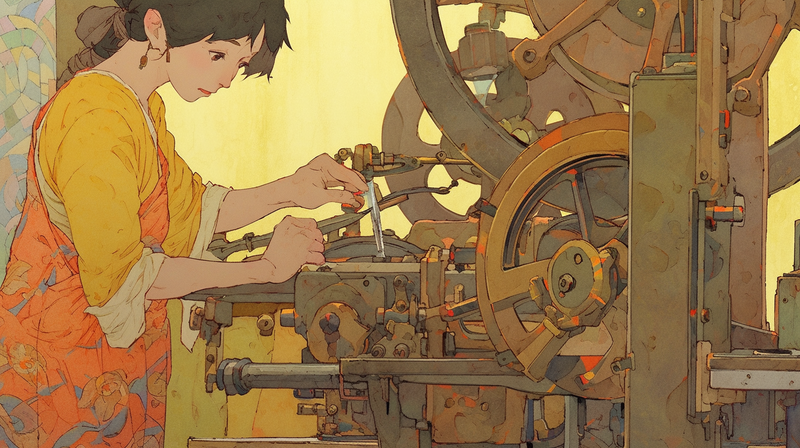提笔忘字
白色魔法
1932年,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在年鉴学院论坛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瓦雷里让听众想象,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微生物,它能攻击现存的所有纸张,并将其破坏殆尽:「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没有解药……它们像啮齿类生物侵入抽屉和柜子一样,将钱包和图书馆里的东西化成粉末;所有人们书写下来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瓦雷里意在强调人类文明依靠书写与记忆来维系、发展,因此才有了文明的绵延坚韧,可他似乎也暗示着,由于纸张的脆弱,文明也总处在危机之中。 瓦雷里并非纸张研究者或印刷爱好者,他大概并不知道现代纸张与古代纸张的差别,严格来说,「纸张病毒」的幻想并不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纸」。在公元三千多年前的古代埃及地区,...
南京面之味
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在1936年的《独生子》中提到了一道名为「支那面」的料理。电影里,一位寡妇来到东京探望分离十三年之久的儿子良助,良助带着母亲游览东京,却没钱请母亲吃高级料理,最后拿出身上所有的钱,请母亲在路边摊吃了一碗「支那面」,乡下的母亲从未见过这道菜,在良助的再三劝说下才最终下口。良助和他的母亲野野太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正是这道儿子羞于呈上、母亲不敢下咽的异域菜品,从路边的廉价食物,一跃成为现代日本最重要的文化形象之一。 即便使用「支那面」这样带有侮辱意味的称呼,日本厨师与研究者也从未否认过拉面的中国起源。日本料理史学家小菅桂子(Kosuge Keiko)曾将拉面的历史追溯到江户时代:...
感觉结构或游戏中的社会
在《MOBA游戏批判——从「游戏乌托邦」到「游戏梦工厂」的文化变奏》、《MMORPG网络游戏批判——关于游戏币以及游戏乌托邦的历史考察》、《逃杀游戏批判——赤裸生命、至高权力以及「游戏集中营」的社会想象力》、《从「王者荣耀」到「绝地求生」:「大逃杀」游戏与内卷社会的伦理学》等等名字长得发指的文章中,邓剑与车致新等人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部分游戏类型展开了分析。 MOBA:这是一种以竞争为核心机制的游戏类型。该类游戏流行的社会文化原因在于,竞争已成为当下时代的重要社会意识。MOBA的时间性赋予网络游戏以完整的商品形式,...
针尖下的世界
1885年,九岁的小约瑟夫·梅斯特被送到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面前。男孩在三天前被疯狗咬了,身上伤痕累累并患上了狂犬病,生命只剩最后几天。在和男孩度过了一个下午后,巴斯特听取了两位医学院院士的建议,将仍在实验中的疫苗注射给了孩子。整个治疗过程旷日持久,巴斯德间隔性地注射疫苗给孩子,终于在三个月后治愈了他。小梅斯特后来在巴斯德研究所担任门房,一直到1940年,德军逼迫他打开巴斯德地下墓室的大门时,他宁死不从,愤然自杀。 巴斯德与梅斯特的故事中充满了命运与偶然,却并非疫苗史真正的序章。向前回溯一百余年,天花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上肆虐,致死人数有六千万之多,死亡率则接近三成。在疫苗尚未诞生的时期,...
有时候你应该做点什么事情
有时候你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这句话里有一种二十多岁的气味,一种二十多岁的不确定性。某一刻开始,对时间无比敏感又非常无感。整理家务、翻读小说、埋头工作、医院看病、玩玩游戏或者其他各种可能的活动随机拼凑起来就能消耗我的一天。说不上是生命中多珍贵的时光,但确实一直在延宕某些时刻的到来。 我十几岁时说不出这句话,但我说过类似的话。八年或者九年之前,潘达住我隔壁宿舍,首都来的天才少年,莫名地陷在青春期的忧郁里。那时候我还在练习阅读和写作,可以说刚刚入门,抓住了一些文字的感觉。那种感觉让人着迷,我相信我会在未来许多年里继续寻找它。因此我对潘达说:你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原本句子不是这样,更接近「你应该找点事做」...
在贝德福那边
1885年,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绅士J·B·沃德(J.B.Ward)出版了一本23页的小册子,题名《比尔文件》(The Beale Papers)。册子一共包含了三份密码以及一份关于密码的故事,作者称,1822年初,一位名叫托马斯·J·比尔(Thomas J. Beale)顾客来到林奇堡的华盛顿旅馆,给旅馆主人留下了一个上锁的盒子。几个月后,旅馆主人收到比尔的来信,要求将这盒子保管十年,并称其中包含着难以理解的密文,...
作为非自然状态的拜占庭将军问题
1982年,莱斯利·兰波特(Leslie Lamport)在同名文章中提出了所谓「拜占庭将军问题」(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该文摘要如下: 可靠的计算机系统必须处理发生故障的部件,这些部件向系统的不同部分提供相互冲突的信息。可将这一情况抽象表示为一群拜占庭军队的将军(a group of generals of the Byzantine army)及其部队在敌人的城市周围扎营。将军们的唯一沟通方式是信使,且必须就一个共同作战计划达成一致。然而,将军中的一位或多位可能是叛徒,会迷惑其他人。...
数码垃圾:电子产品的自然史
引言:电子产品的自然史 每一种真正新颖的自然之配置——从根本上说,技术正是这样一种配置——都对应一种新的「图像」。——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卷宗K) 机器和既非机器亦非人类——我称之为「非人」(unhuman)——的领域,与人们一起建立了被称为自然的人造物之集合。这些行为体(actants)不能被当成普通的资源、地面、矩阵、物体、材料、工具或冻结的劳动;它们比这更令人不安。——唐娜・哈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