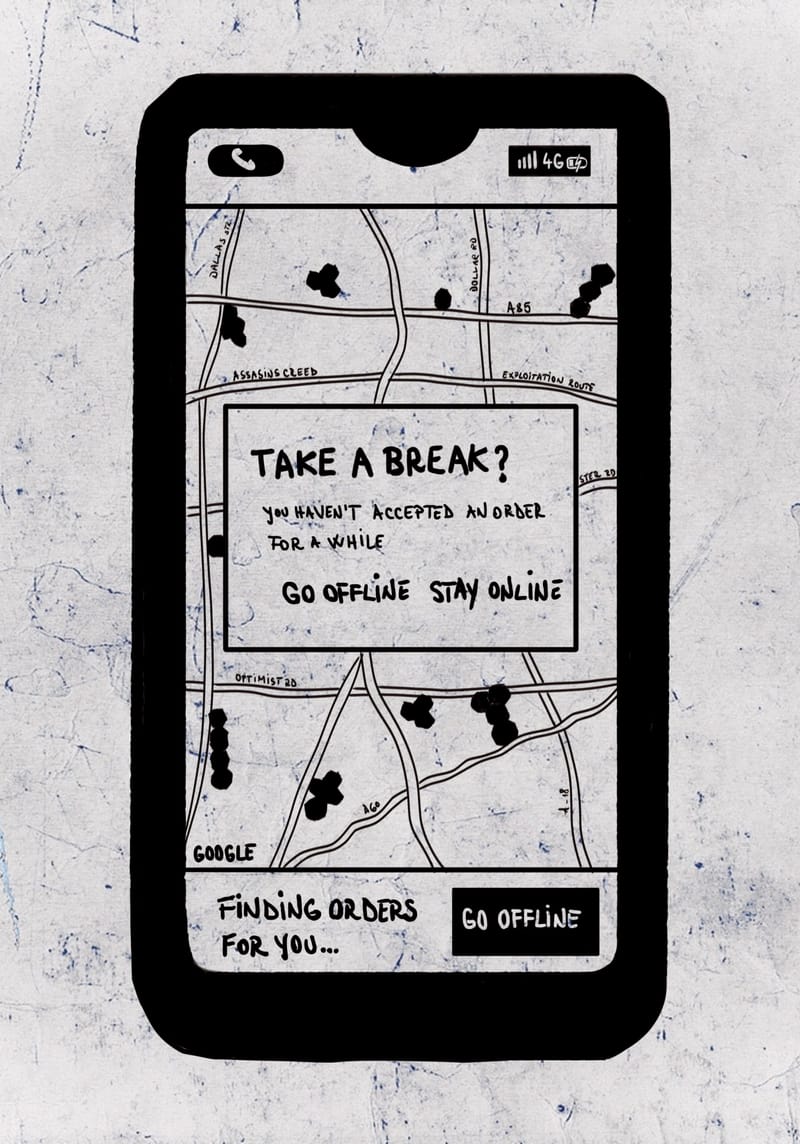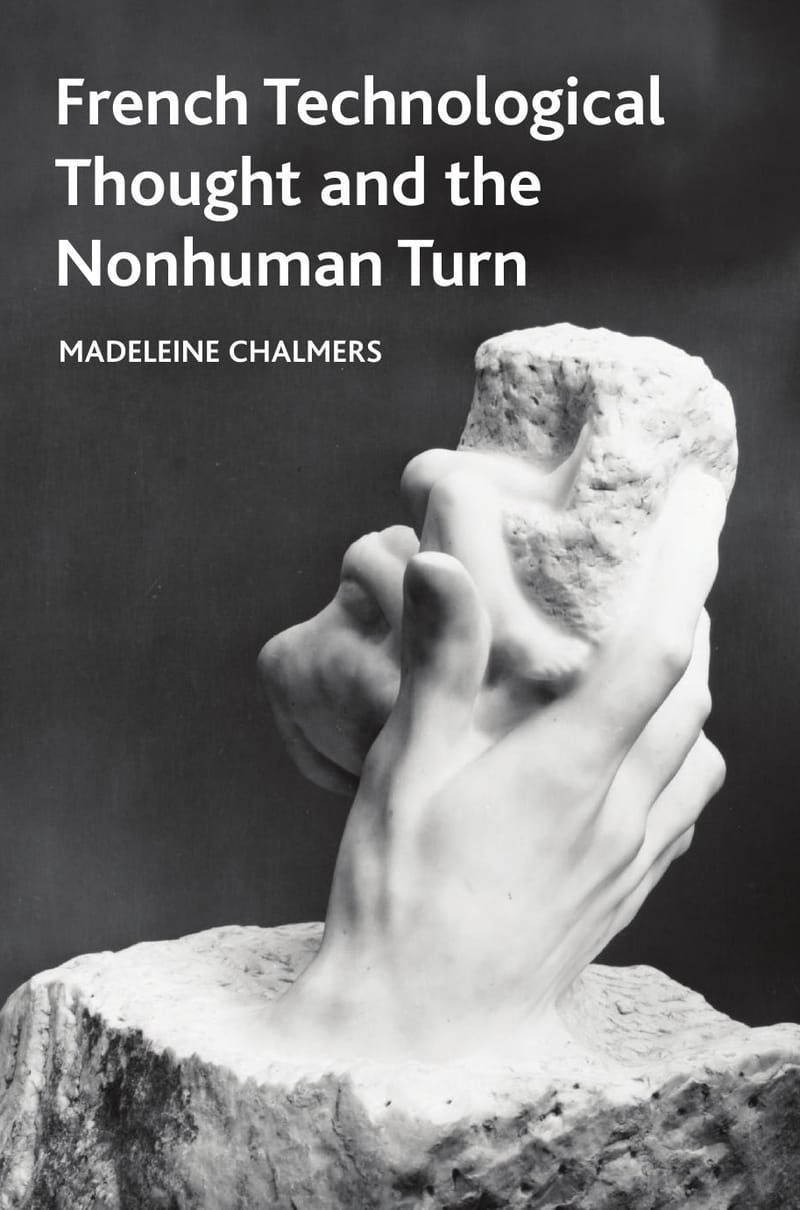公式表达科学,如果把公式输入计算机,屏幕上就会出现科学的世界观:相互交错、重叠的线状网络。其中,部分位置的线路聚集,形成凸起。这些网络中的波谷被称为「物质」,而形成它们的线路则被称为「能量」。要是把这幅图像「动画化」(拍成电影),人们就能观察到,线状网络中的凸起是如何出现,在不同位置变得越发复杂,随后再次变平,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部电影也有个「大团圆」结局:线状网络无定形地向四面八方延展,或者说「热寂」。在众多波谷中,某个低谷可被识别为「我们的太阳」。若是仔细观察这个低谷,人们就会看见许许多多的小凸起:生物质包络着地球。若是注意这些溅射,人们就会在那微不足道且转瞬即逝的涟漪中显现。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将认识到,我们自身是相互交错的力场中的临时凸起,如是,整个传统人类学就失去了意义。就此而言,我们只是各种丛结的关系(线路),并无任何核心(任何「精神」「我」「自我」,或是任何一种足以提供自我「认同」的东西)。若是解开了构成我们的关系丛结,我们将一无所有。换言之,「我」就是一个抽象的点,是具体关系的交汇点,也是具体关系的起点。自然,我们可以「认同」体内的关系丛结:既可以作为一个重物(电磁场和引力场的交错节点),也可以作为一个有机体(遗传场和生态场的交错节点),还可能作为一种「心理」(集体心理场的交错节点),抑或是作为一个「人」(社会场和主体间场的交错节点)。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面具」。「自我认同」是过去的概念,如今,更好的形容是「面具识别」,或许不只一个面具,而是几个可互换、可叠加的面具的识别。
因此,「面具」一词恢复了其存在的本意:一个人只有戴着特定的面具(去跳舞),部落中的其他成员才能识别出面具,并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最初只有少数的面具,它们属于萨满、猎人和同性恋者。后来,面具变得越来越多。今天,面具可以一个叠一个。例如,一个人能以银行经理的身份跳舞,其下又戴着艺术鉴赏家、桥牌手和父亲的面具。人可以一层又一层地剥离面具,随后发现内里空空如也(宛若洋葱)。用存在主义的话说:「我」就是他人口中的「你」。
如果某人将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场域)看作一个面具租赁机构,那他/她也将意识到,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网络,在此之中,面具捕获了物理、生物、心理(及其他)形态的诸丛结,并将其凝结成「人」(Personen)。那么,问题就在于面具的制作方式,以及如何将面具应用到社会网络中的诸关系流中。在此,面具的设计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亚马逊部落中,这相当明显:巫师的面具设计是如何产生的?又是以何种方式将面具应用到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使得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将之识别为巫师?可在所谓「后工业」社会中,或是在一个与其一般复杂的社会中,这一过程就不那么明显了。然而,要明确表达这些问题却再简单不过,这就足以将大部分政治范畴搅浑了。
亚马逊的印第安人恐怕给不出什么有用的回答。他们会把面具的设计归于超人的力量(像是某位豹形祖先),再借某种神圣传统来解释其应用。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可信度并不亚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可它却与我们相隔阂。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犹太—基督教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预设了「我」的核心,它爬进现有的面具并藏匿其中,这使理解面具设计比理解豹形祖先还难。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从主体间关系的场域退后一步,试着从外部看面具——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面具,「我们」便不存在,也就无从识别面具。(曾有人称之为「苦恼意识的辩证法」(Dialektik des unglücklichen Bewußtseins)。)
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这么说:作为勺子的面具,浸入关系之粥,以便创造出人,可不知何故,它们自己也从粥中冒了出来:它们本身就是主体间的形式。(银行经理的面具并没有从某种志业或职业的天堂上堕落到社会中,可志业与职业确是面具的后果。)因此,面具的设计问题是一个主体间的问题。这意味着,只在一般性的「对话」中,我才成为我之所是。由此,我不仅是面具的佩戴者,也是他人面具的设计者。因此,「我」之自我「实现」,不仅在戴着面具跳舞之时,也在与他人相伴并为他人设计面具之时。这个「我」不仅是某人的「你」,也是「你」之为「你」。然而,只在戴着面具时,我才能设计面具。对于面具设计问题,这答案并不令人满意,最多算是序曲,引出后续的问题。正是(也只有)这一提问的过程,才将我们与印度人(包括那些在我们身边跳舞或从电视屏幕中获得面具的人)区分开来。设计意味着许多,也包括命运。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在试着把握命运,并一同为之塑形。
翻译自 Flusser 的论文集 Shape of Thing。自用,未定稿,或有翻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