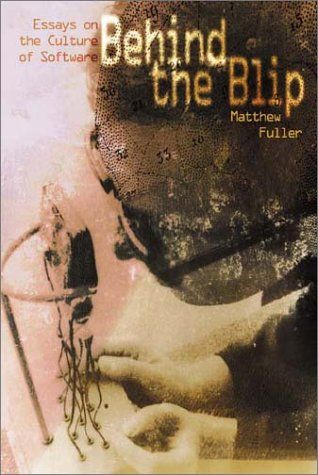工作史前史
1806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抱怨到:「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在密尔所处的十九世纪英国,工人不服从生产的问题不止困扰着哲学家,也让工厂主和商人感到头痛,一位针织品商人就曾大倒苦水:「我发现人们对于任何规律性的安排有着极度的厌恶……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出入,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能按习惯的方式行事……这使得他们痛恨整个系统,我不得不将其打破。」
时隔两世纪,今天的劳动者对此类抱怨已经见怪不怪,大概只会感慨「摸鱼」是人类的天性,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从古至今就未曾改变过。可会心一笑后,细细品味之下,一丝异样却又浮上心头:十九世纪的工人和我们一样都喜欢偷懒,可两个世纪的生产力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偷懒之后仍可养活自己,甚至可以赋闲在家啃老为生,十九世纪的工人若是偷懒或是不服从安排或许就会挨饿,他/她们又为什么要拒绝规律性的安排甚至一切拒工业工作?答案并不复杂,因为对十九世纪早期的人来说,工厂中的工作并非「真正的工作」。
生活在世界上,人们需要许许多多的常识来支撑自身的判断,然而,不同时代和文化未必共享着同样的常识:今天的人们将企业和工厂的工作看作理所当然,可回到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这种新兴的工作形态却未必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在中国,人们几乎是一步从农耕时代跨入了工业时代,因此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工作就意味着在工厂或在某种科层系统中进行日常劳动,除此之外的生产方式便是传统的农耕生活(无论是作为自耕农还是佃农)。可在欧洲,前工业化时代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职业行会和独立匠人,是它们而非工厂定义了「工作」最初的形态。
对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人来说,工作不是两点一线、养家糊口,或是作为社会或国家的螺丝钉,真正的工作总是意味着,一个人在实现上帝赋予自己的「天职」(Beruf)。抛开宗教色彩,「天职」代表的工作观就是所有匠人都会自然生发的观念:重要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是自身的技艺是否在精进,而不是工作本身能够带来多少利润。许许多多拥有此种意识的匠人联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经济组织「行会」。与工厂完全不同,行会不仅承载着工作的分配,更是工人们社交与日常生活的处所。这种重视过程而非结果,劳作与日常浑然一体的状态,正是欧洲的「工作」理想。
然而,十八世纪以来,以分工和机械化为核心的新兴工厂工作完全背离了传统的理想。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盛赞工厂将一根扣针的生产分为十八个步骤并因此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从未想到,在劳动过程甚至劳动内容被牢牢限定后,人们无法在工作中展现创意、个性与天资,工作的产品不再属于他/她自己,工作本身也不再与他/她生命的其他部分水乳交融。眼下,重要的是将事情做完并且获得酬劳,工作因此变得索然无味甚至惹人生恨。正因此,十八、九世纪之交的许多人宁愿成为贫民也不愿(或难以)进入新的工厂系统之中,他们不愿失去传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面对如此之多的贫民和不断扩大的劳动力缺口,社会改革家们感到不安,他/她们希望找到一种办法来将不顺从的贫民变成富有生产力的工人,因此,一种新的道德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伦理」——诞生了。对于此种「工作伦理」,现代人并不陌生:人类必须通过工作来维持生计,说得更简单些,要么工作,要么死亡。可回到十九世纪,它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定义。在教会统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他/她存续的意义不需要证明,无论是通过工作还是依赖他人的救济、养育或施舍。工业时代的人则变成了「工作的人」,他/她的意义需要通过自己去证明,他/她的生存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保障。
与新道德相伴的总是新法律。1834年,臭名昭著的新《济贫法》颁布。1601年的初版《济贫法》规定:凡年老者可在家中接受救济;贫困儿童可在他人家中寄养,成年后可去做学徒。可在新《济贫法》中,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习艺所中从事苦役的贫民」,而习艺所则是一个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强制劳动场所,贫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就一定不会前往。对于这种安排,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解释得十分清楚:「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换言之,只要「不工作」的下场足够悲惨,人们就不得不去工作,不得不成为工业时代的一部分。
工作意味着正常,不工作则是不正常,必须想尽办法将不正常的人转变为正常的人,让他/她们符合新的道德。卡莱尔预想到了这一过程的不完美甚至残酷,可他也兴奋地提到,这种「次优」的方案一次性解决了社会的诸多问题:平民的温饱、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问题只在于如何赶走或驱动那些不工作的人,他/她们不止影响了自己,也拖累了努力工作的人,他/她们是社会中的害虫,也是改革者希望赶走的「老鼠」。在此,现代意义上的工作出现了:不是主动展开的天职,而是被动迎接的任务;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系统的安排;不是为生活而工作,而是为生存而工作。人们不得不工作,只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社会中的异端,而是具有尊严的人类。
欲望的引擎
十九世纪早期的道德改革者们认定,一种全新的、围绕工作结果(而非过程)构建出的伦理将解决个人、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却尚未思考工作伦理的未来:如果生产力真的不断发展,那么越来越少的劳动量就足以支撑个人和家庭的温饱,如此发展下去的结果是所有人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换言之,工作将逐渐消失,用于约束人进行长时间工作的工作伦理也将不复存在。「工作和工作伦理将消灭其自身」,这一推论是如此顺利成章,仅仅几十年后,新一代学者们几乎都在著作中允诺了「无工作」或「少工作」的光明未来。
「工作的消亡」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是十九、二十世纪对未来的美好祝福: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共产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即为了生计而劳动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人们会继续劳动,但是为了自我发展而劳动,某种意义上,这算得上是马克思对传统欧洲工匠生活方式的怀旧,社会在更高的生产力下恢复了原有的荣光;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更直接地预言,到二十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发达,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每周工作时间会缩短至15小时,不到八小时工作制的40%。然而,现实却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们仍在勤劳的工作,工作时间并未缩短甚至越来越长。
今天的人们知道,所有这些预言,哪怕不是刻意为之的谎话,也是过于美好的幻想。马克思与凯恩斯等理论家算对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却并未理解「增长」的真正意义:「增长」从来没有特定的目的,哪怕有,也绝不会阻碍进一步的增长。当卡莱尔等改革者希望让贫民用持续的劳动来证明自身存在时,他/她们从未想到,总有一天国家、政府和社会也需要通过不断的进步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一种无法戒除的瘾:没有人希望增长的列车停滞,尽管人们并不完全明白增长意味着什么又将带来什么,可哪怕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只要增长就好」,现代社会仿佛一个大型企业,带领所有「员工」不断前进,迈向应许的未来。
对无限增长的渴望塑造了现代工作的新面貌:科技的发展本可以大大降低人们的工作时长,可持续的增长必然要求持续投入劳动力,甚至创造那些原本不需要的劳动力岗位,用来将经济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发达。然而,对大部分劳动者来说,生存或温饱仍旧越来越容易实现,工厂主与企业家并未天真地相信纯粹的工作伦理足以约束所有工人的行动,他/她们急需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推动人们工作。幸运的是,解决方案是如此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再相信工作能够让他/她们达成道德的圆满,那就将彼岸变得更加现实,将工作的最终目的变成「不工作」,让所有人为了不工作而工作。
眼下的工作是为了日后的消闲,眼下的苦难是为了日后的舒畅,眼下的屈从是为了日后的支配。延迟满足的模式短暂支配了二十世纪前半夜的工作与工业: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劳动者都抛弃了道德的外衣,人们不再讨论工作的道德与责任,而是每一张具体的钞票与置换它所需的劳动。在被称之为「美国梦」的奇迹还能实现的时期,工作仍有些许超越的意义:积累足够的资本,用巨大的量来达成质变,从而彻底改变人生的轨迹。可当分配逐渐固化后,工薪阶层能够积累(甚至能够想象)的金钱都不再足以改变任何根本的因素,为什么而工作的问题重新浮上水面。
人们毫不意外的发现,两次世界大战后,在阶层上升通道逐渐关闭的时期,五光十色的消费品出现了。小汽车、洗衣机、油烟机、洗碗机——与战前相比,各类机械在功能进化之前,首先拥有了各式各样的外壳,并且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耐用品越来越像快消品,一切行业都变得越来越像时尚业。经济学家常常解释称这是因为战后有大量的财富需要消化,因此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发展,却从未考虑过大量的「消费」行为本身意味着人们已经放弃积累财富,也放弃了通过足量的财富来改变阶级与命运。从改变人生到占有最新款的洗衣机,工作的目的如此快速而自然地堕落了。
如何将不想工作的人拉入工作之中?现代社会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不断生产欲望的机器,用占有商品的欲望而非工作本身的道德价值来吸引工作者。工作为了收入,收入为了消费,消费为了欲望,而欲望永不停歇,永远无法满足,这就是支撑现代工作和现代生产的终极公式。某种意义上,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是增长和发展的必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低,越来越少的工人就足以完成同样的生产。个体对经济最大的助力不再是成为工厂的螺丝钉,而是成为工厂产品的消费者,承接整个经济系统一刻不停的生产结晶。
当代的工作与个人温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逐渐脱钩,甚至难以影响个人的命运。工作彻底地货币化了,从数百年前的值得投注一生的天职,变成了彼此之间没有差异的获取金钱的手段。工作越是缺乏内在价值,人们就越是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意义和自我的定义,而不得不求助于消费。今天的人们崇拜的不再是工程师或文学家,而是能够占有更多、更好的消费品的人,无论是一辆玛莎拉蒂,还是限定款的变形金刚模型。当代工作变成了欲望机器的一部分,通过提供差异化的报酬,它在保障个人消费能力的同时,迫使人继续努力追求更好和更多的东西。人们不得不工作,只有购买、占有足够的财富和物品,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失败者,而是具有尊严的人类。
成为现代人
当代社会努力将所有人的梦想从「更好的人生」转变为「更多的人生」。更多未必意味着拥有更多东西,而只是占有更多选择。这种占有与选择的哲学试图解决当代工作意义的缺失。传统上的工作可以定义自我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整个人生的方向,一位木匠需要钻研的东西与一位铁匠截然不同,但两种职业都有自己可以抵达的意义彼岸,两者都可以自豪地承认自己正在从事值得投注终身的工作。今天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其薪资水平所界定,除去少部分科学、文化、创意等产业的人士外,大部分人不再骄傲地用职业定义自身:重要的不是作为产品经理或程序员的我,而是我的年薪有七位数甚至更多。
这并非纯粹的拜金主义,对大多数人来说,金钱本身的意义并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金钱所能代表的选择,或者更简单的说,金钱象征着自由。今天的人们相信,自我不是被工作,而是被收入所能带来的自由选择所定义。在或大或小的岔路口上,选择越是丰富,人生也越是多彩:「我」被我所购买和能购买的东西所定义,「我」被一种无限的选择的过程所定义。选择并不意味着放弃道德或品味,相反,选择意味着能够接纳更多元的道德和品味。因此,一些人开放而包容,能够理解、穿梭于不同的事物之中,另一些人则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选择」的缺乏被看作真正的贫困,一种关乎自我与心灵的贫困。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前现代的生命之间总是存在着质的区别:农民的人生根本上不同于木匠的人生,两者由截然不同的东西组成,也注定迈向不同的目标。当代的人生则更接近积木,每一次选择都是一块组件,所有人共享着同样的条块,可并非所有人都能选择所有的条块,也总有人会选中「错误」的选项,人生之间的差距变成了「量」的差距,区别在于有的人选择更多,这意味着他/她能搭建出的形态更加丰富,最后形成的建筑也更加可靠、美观。在积木式的个人意识形态背后,人们感到托克维尔所说的现代社会特有的愤懑,一种「我本可以但却并未」的愤懑,以及需要不断自我完善与自我成长的欲望。
现代国家从个人处借鉴了工作伦理,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无限增长的要求,当代个人则将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转化回个体层面:个体之间的根本差别被取消了,人们试图用越来越多的选项完善自身,也在此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企业」。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所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塑造的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他/她们主要关注市场交换以及在交换中强化个人的利益;在当代,也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时期,典型的形象是「作为企业的个人」,人们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企业家,注定要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
当传统的匠人大喊「我是一位木匠」时,今天的人们只能回应说「我是一个企业」。当代的自我成长并不会彻底改变阶级或命运,它总是在已有的人生积木上修修补补,添加更多样的条块或更丰富的色彩,因为一家企业不可能变成企业之外的东西,它只能变成一个更成功的大型企业,或是因各种失败的选择而陷入破产的境地。为了尽可能正确地选择,人们努力从生命中剔除不可控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规划、规制与规范。自我控制变成了(无论是物理性的健身还是心理性的时间管理与情绪管理)当代最重要的学问,八小时的工作伦理也变成了一种无垠的生活伦理。
我是一个企业,我是一个项目,今天的「自我」是一个必须不断加以维护的工程:我必须不断优化自身,甚至优化得比其他所有人都快,不然就会被淘汰。这种自我管理与自我维护的精神重新混合了工作与非工作界限:过去,人们只需要在通过努力完成工作证明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今天,在一天中的所有时刻,我们都需要为了证明、优化自己而拼尽全力,用更当代的话说,下班时间正是个人成长的时间。正是在上班与下班的反复循环中,新自由主义的自我(Neo-liberal Self)发现人生是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意义空洞:值得追求的不再是「我是什么」或甚至「我拥有什么」,而是「我还能拥有更多」的进步意识。
如同现代史上的每一种主导性人格模式,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并不恒久,甚至比过往的每一种人格都更容易破碎。二十世纪末以来,许多国家逐渐发现,基于工作与消费的二元区分、追求持续竞争与自我优化的人格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崩溃。在美国,出现了归巢族一代(boomerang kids generation),也即大学毕业后回到父母身边的反常一代。在英国,不就业、不升学也不进修的尼特族(NEET)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在拉美,失学与失业的「双失青年」一直是政府的心头之痛。在欧陆,法国的袋鼠族和德国的赖巢族掀起了关于啃老的讨论。在日本,单身寄生者与低欲望一代又构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景。
然而,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强大恰恰源于极端的脆弱。作为「新自由主义自我」的镜像,尼特族完美地呈现了放弃选择与放弃努力的结果,对正在努力拼搏的人来说,尼特族的境遇既是一种威胁:如果拒绝投入、拒绝选择,「我」也可能变成尼特族一样的人,一个缺乏选择的贫困者与无法自主的失败者;也是一种安慰:这家失败的企业并不因为任何结构性的或不可避免的因素而陷入如此境地,它的失败源于自己进行了错误的选择或是无法抑制的懒惰。尼特族越是失败,「正常人」就越会拼命的工作与发展并在努力之中感到宽慰。通过赋予「失败」的生命一种独特的结构性价值,这个精妙绝伦的系统掩盖了自身的失灵,照亮了成功者的人生。
哥布林人生
如果要为现代「失败者」谱写一部历史,新冠之后的几年将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从中文世界的「躺平」(放弃选择)与「摆烂」(故意选择更差的选项)到英文世界的「哥布林模式」(Goblin Mode),如此大规模的放弃成功(甚至刻意追求「失败」)的情况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比起语义复杂的「躺平」与「摆烂」,英文中的「哥布林模式」得到了更清晰的定义:拒绝社会期望、抛开自我形象,以不修边幅、享乐主义的方式生活。在牛津词典将「哥布林模式」选为2022年的年度词汇后,各路媒体陆续发表文章讨论人们为何会选择进入洞穴之中,过上哥布林式的人生。
少部分讨论提及社会竞争的加剧、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多的讨论则在关注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的影响:无论是在隔离期间,还是在隔离结束后的患病期间,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冠状肺炎提供了一种大规模的「去社交」状态,短暂地消解了原本的社会规范。对于这种放弃宏大追求、回归基本需要的「异常」状态,个体非但不急于逃离,甚至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松弛。因此,许多人即使在隔离结束后或是疾病康复之后,仍旧将「哥布林模式」看作一种新的生活选择,并主动进入其中,换言之,在英文语境下,「哥布林模式」是一种中性的新生活状态,其中并不包含价值褒贬。
从新冠开始的讨论倾向于将「躺平」「摆烂」或「哥布林模式」看作一种应激反应,即个体在公共事件中习得了某些新的心理结构,或不得不用这种结构应对短期事件带来的压力与改变。然而,在对现代工作、消费与生活的历史进行追溯后,我们意识到,与其说「躺平」「摆烂」与「哥布林模式」是对新冠的应激反应,不如说是整个现代历史结成的硕果。如果说尼特族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反面,那当代的哥布林则是主动拒绝与其共舞:拒绝选择,拒绝将自我看作一个企业或是工程,拒绝增长、发展与完善,拒绝思考长远的未来,拒绝成功也拒绝失败。
自我原本是一个充斥着欲望的无限增长的主体,现在却被最小化成了一系列感官的组合,欲望被最小化,视野和时间被急剧缩短,一种「为了自我的自我」诞生了。如果说愿意不断约束并发展的自我是「人类」,那么享乐主义的(乃至斯多嘎式的)自我就是永远比人类矮小却也更快乐的「哥布林」。可洞穴生活的前提是存在洞穴外的世界:哥布林无法也不能忘记自己「必须」走到洞穴之外,因为他/她从心底拒绝认可眼下的生活。于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躺平」「摆烂」与「哥布林模式」总意味着一种对抗:用自我的心理结构(以及连带的行动或拒绝行动)对抗外在的意识形态。
所有这些现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正当、无限的发展、自我的完善——早已深入骨髓,于是对外部世界的对抗最终变成了一场面向自我的战争:对抗自己从小习得的所有人生法则,对抗自己所掌握的所有意识形态知识,对抗过去与未来面临的或可能面临的每一种可能。没有人会主动寻求痛苦,尤其是彻底否定自己所有生活信条与未来希望的痛苦,因此,「躺平」「摆烂」或「哥布林模式」从来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一种无法选择或无力选择之后的备选项。人们越是不得不释怀与放下,越是躺得平直,越是大声宣称这一切,身体中就越会涌出一腔无从释放的愤懑。
然而,正是在愤懑之中,我们才能找到希望,找到真正超越自我的力量。人们不应该忘记,说自己「选择躺平」恰恰是将「躺平」的责任放回自身,主动为社会和他人免除责任。人们也不应该忘记,真正的释怀恰恰意味着承认作为个体的自己无能为力(甚至相当程度上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进程)。正如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说:「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
只有将自我的生命与宏观的结构、历史相关联,人们才能更好的理解自身的境遇,理解迈向未来的方式。即便自身并不处于特定的困境之中,我们也能理解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在同样的结构问题下,他/她们或许拥有更少的资源,更差的位置,对他/她们来说,此刻的人生或许并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只存在糟糕解法的解答题。也只有理解了与私人困扰所关联的整个时代和历史,人们才能发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可能只是历史上的过眼云烟:现代意义上的「工作」出现不过两百年;上学、升学、就业的人生模式由来不过一百年;必须在社会中与他人竞争并胜出的观念更是近五十年才逐渐流行。
清除了观念上的阻碍,我们才能设想更多的可能,甚至那些原本不敢想象的乌托邦。是否可以让工作与收入解耦,迈向一个拥有全民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世界?是否可以拓展工作的界限,让家庭中的杂务、照料、沟通也变成一种值得尊重的劳动?是否可以让工作重新具有意义,或者更努力地从事那些自己能够找到意义(尽管收入微薄)的工作?人类无法通过想象改变命运,可生活的境遇总是一种「遭遇」,是历史和当下、结构和个人、他人与自我的碰撞,因此,改变命运将会撞击到的「自我」,改变对自我的认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改变了我们对境遇的体验。
或许,越是在退缩时,我们才越应放大思考与想象:努力理解社会结构、历史演变与他人命运的紧密关联,勇敢探索生命进程、日常体验与远近未来的多元意义。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并不意味着要获得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成功」,无论这种成功被定义为无限的富有、持续的努力还是不断的成长。历史是如此漫长悠久,人性是如此柔韧可塑,人们可以跑、走、站、躺,也可以生活在洞内或洞外。在一个密布选择的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真正关乎自我:是否要理解生活本身的复杂,并活得自在、清明。而在所有关于自我的话题终结后,还有一个选择值得追问:是否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是否可以学会为他人而活,为自己之外的事物而活?
本文另有版本刊发于《时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