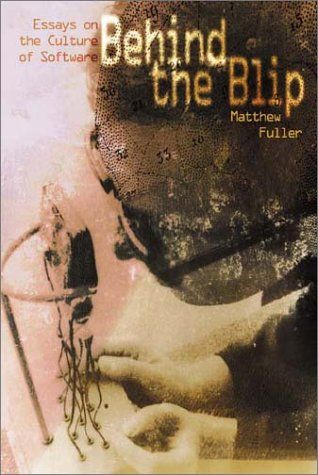软件批评的进路
2003 年出版的 Behind the Blip 一书收录了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写就的七篇文章,整体上可看作富勒后续提出的「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y)的先声。富勒现任职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通常被看作媒介理论家,抛开去年在学生许煜(共同指导老师包括斯蒂格勒和拉什)的推动下出版《媒介生态学》中译本,在中文学界极少得到关注。富勒的受冷大致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缺乏有力的引介者(在许煜之前似乎没能有一个相对熟悉其研究脉络的中文区的学生);其二是研究难以在现有的中文学科系统中安置(算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系统或变体,然而文化研究本身在中文学界建制化程度就较差);其三也离不开富勒本身的「野路子」(媒介艺术家出身转向学术研究)带来的理解困难。
与七八十年代的未来学或技术批评不同,包括富勒与加洛伟(Alexander Galloway)在内新一代媒介研究者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是接近艺术实践,不仅是评论、参与各种媒介艺术,甚至本身就是艺术家;其二是接近技术实践,不仅是在传统技术哲学或技术批评的基础上发展其研究,同时也以相当工程师化地视角思考技术的存在。两项特征在加洛伟处或许还能算是背景色(毕竟他师从詹明信与哈特,对当代批评理论相当熟悉),在富勒处就只能说是根本性的要素了。审视富勒的文章,尤其是其早期文章中的引用部分,尽管也有引用如福柯、海德格尔、鲍德里亚等现代理论家,可是其出处大都是导引类书籍或读本与转引。并不具备实质上的对话能力;真正得到一手引用的书目则大都偏向实践,或是技术与艺术项目(如 Alan Cooper 的界面设计指南),或是相对通俗的针对特定议题的技术批评(例如 Steven Johnson 的 Interface Culture)。
富勒所引用的材料已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 Behind the Blip 一书的写作进路:在同名的篇目《在「哔」声后:软件作为文化(通向或离开「软件批评」的方法)》——Bheind the Blip: Software as Culture (Some Routes Into “Software Criticism”, More Ways Out)——中,富勒试图追问「软件批评」的可能。作为前提,富勒试图清理出此前不同层面的软件研究脉络,即软件批评、HCI研究、程序员自述与批评理论等几种形态,并尝试将不同脉络整合到自己希望构建的软件研究系谱中。整体上看,富勒所希望迈向的软件批评(亦即后来发展出的软件研究)仍是早期软件批评与批评理论的混合,然而HCI研究与程序员自述的确也在不同层面上——一方面是人机交互中内在的个人主义假设与封闭的设计情境,另一方面是程序员建构出的对数学美的追求及作为其发展的对社会控制数学的追求——为其研究提供了启发或是靶子。
回到软件批评与批评理论两方面。富勒列出的早期软件批评研究清单中既包括民族志或人类学性质较强的实证作品(偏向STS),例如 Jeannette Hofmann 对文字处理器的分析[1],或是 Donald MacKenzie对导弹引导系统设计中的浮点运算之政治意涵的分析;也包括推进方式较为理论化的研究,如 Michael Heim 的 Electric Language 或基特勒(Kittler)的各类研究。可以说,至少在富勒本人看来,软件批评是一个相当开放的领域,其发展的困境一方面源于问题意识尚不够精准(似乎大多在STS或媒介研究的脉络中进行),另一方面也源于理论的稀缺,为此就需要引入批评理论。
可是为何此前的批评理论并未关注到软件?富勒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软件作为工具的神话(性质)阻碍了批评理论的介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般性的技术或媒介批评,往往是基于一个类别或一类对象,而并不基于该类别的具体实例展开(例如可能在整体上研究电子媒介而不关注软件,或者整体上讨论软件与硬件,而不区分系统、应用、界面、窗口等不同层面),这就使得结构层次复杂且不同实例之间异大于同的软件难以得到专门研究。
自然,同一情况反过来看也可以认为,由于前研究中疏漏过多,软件批评或软件研究的确是一个相当具有潜力的领域。尤其是软件中最重要的两个性质,首先是软件所具有的特殊时间尺度,即一种无时间性(Timelessness)本身就带来了相当独特的实在论性质(可参考许煜后续的讨论),亦可以于更广阔的哲学脉络相连;其次则是由于整个计算机系统的过度复杂性使得软件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发生在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中,这种特殊的运作模式又带来了两项优势——其一,由于层面极多,不同学者可以进行不同的跨层次分析,如此就可能避免在层级化的跨学科术语迷宫和僵尸会议中迷失(如电影研究)[2];其二,由于软件批评始终是与业界、技术相连的,因此也避免诸多文化理论的命运,也就是避免太快进入「接受」分析或是纯粹的思想批评,向更生产化的分析敞开,可以将批评转化为对软件中生产实践及其再配置的关注。
清理脉络之后,富勒转入对软件批评的建构性讨论,大致上包括批判软件(Critical Software)、社会软件(Social Software)与思辨软件(Speculative Software)三种形态。其中批评软件是指融入了批评理论的问题意识的软件,具体来说,既可以利用软件本身所呈现的证据来构建/说明对象、信道、陈述、序列等多方面的安排,使其真理条件得以显现(既某种结构解蔽工作,可参考对 Word 的分析);软件MOD则顾名思义,是指制作软件MOD(伪装成正常软件)以解释用户的底层构造、程序处理数据的方式和界面的转换、编码过程(可参考 Web Stalker 与 Natural Selection)[3]。社会软件则是指能自我揭示其输入输出流及影响,或作为用户和程序员之间持续的社会性的结果而直接诞生、改变和发展的软件,其目标是逃离专家系统(专家们的内部跨学科),将软件真正地社会化,更细致地进入机器、数字与社会,认识并找到将被排除在专家文化外的智识联合起来的办法。
相较之下,思辨软件既与批判软件或社会软件有所区别,又延续了两者的问题意识,即试图考察软件系统与人的互动关系的替代性可能:「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创造这个系统,但这个系统也在创造我们。我们建立了这个系统,我们生活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也被改变了。」[4]与系统—个体循环互构的思路不同,思辨软件是解释编码之可能的软件,也是创造不同数据、机器、工作之联结转化的软件。它试图发掘那些「哔」声(Blip)背后的事件:「这些软件中的事件,这些数据受制于和制造的过程和制度,提供了一个闪光点,在这个闪光点上,这些相互关系、合作和冲突可以被挑选出来,并分析它们的控制和生产、干扰和发明的多种能力效价。」[5]必须意识到,正是由于软件无法脱离「运行/进程」(Process)而存在,一种以思辨软件为载体的「行动即思考」或「行动即批评」才可能成立。因为正是这种对「运行/进程」的戏拟构造出了对其「正常状态」的最为严厉的批评:思辨软件拒绝相信无辜的故事/哔声,而是通过歪曲与误读,带领用户在哔声之间漫步[6]。
作为艺术/学术的软件批评
全书第二章开始,富勒陆续展开了六个案例分析,其共同点在于,个案均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到了特定的媒介艺术实践中,差异则在于其介入形式的不同(作为评论、分析或说明)。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个案研究的理论推进仍有相当差距,部分篇目算是颇有创见,亦有部分篇目仅能算作尚未发展成篇的「笔记」(Notes),理论上并不融贯,也并未与富勒本人所勾勒的整体框架有充分的关联。尽管如此,对不同案例的简要介绍仍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只有在对具体的艺术品及其评论、分析或说明的二阶分析中,富勒论述方法上的优劣才能被展现;另一方面,富勒在不同文章中使用的语体与材料性质都相去甚远,充分的个案讨论有助于帮助理解富勒所谓的软件研究(至少是这一领域的早期形态)的不同形态及可能。
回到文本,全书第二篇《剖开外立面:将 Matta-Clark 的撬棍带入计算机》(Visceral Facades: Taking Matta-Clark’s Crowbar to Software)重点分析了艺术家 Matta-Clark 的作品。Matta-Clark 是一位美国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家,其标志性作品包括1974年的「断裂 Splitting」(将一栋房子从中间切开,并用撬棍将一半翘起五度)、1975年的「锥形截面 Conical Intersect」(在一栋房子中打出一个圆锥形的巨大空洞)、1976年的「下水道 Substrait」(下水道中的漫游影像)及1973年的「真产权:假产业 Reality Properties: Fake Estates」(买下各种房地产交易中被遗忘的边角,例如某人车道上一英尺宽的地带,一平方英尺的人行道,极小部分的路缘石和排水沟)。


富勒关注 Matta-Clark 乃是因为这种对建筑的「剖析」或许可以挪用到软件中。在一般的分析中,软件似乎并未嵌入在任何实质性的构造(Architecture)中,「作为一个在合成空间中实现的几何体,它可以是任何空间,任何事物,可无论如何,它都像是被干洗过并从时间中剥离出来」[7]。正是为了穿透这种表面的稳定性,在软件运行所依赖的(也是受污染的)物质与社会与平稳运作的电子之间提供对话机会,富勒希望将 Matta-Clark 的撬棍引入软件中,在软件的表面打出孔洞与裂隙,利用故障(faults)、扰乱惯例(disturb)并开拓软件之特异性(idiosyncrasies)以暴露出软件之实质运作,重新思考「用户」与软件之间的关系。
可是这种暴露要如何实现?基特勒所谓的「媒介考古学」自然是一种方式,更广义上的批评理论对软件生产、运作之社会条件的考察也有其效果,然而富勒所采取的方式却迥异于从批评理论或媒介研究中生发出的研究。在《变异的方式》(A Means of Mutation: Notes on I/O/D 4: The Web Stalker)与《打破信息法则》(Break the Law of Infomation: Notes on Search Engines and Natural Selection)两文中,富勒写下了两个自己参与的艺术作品的注记。The Web Stalker是 I/O/D[8]团体于1997年发布的艺术项目,彼时正是浏览器大战(IE与网景)期间,The Web Stalker 的主要目标正是要在此环境(商业公司相互竞争,不同的产品之间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下创造一种替代性的网络浏览的可能,或更进一步,创造一种「变异」的可能。
The Web Stalker 内置了许多不同的模块,除去「正常浏览」被渲染后如平面设计稿一般的网页外,也可以直接查看网页的源代码,观察网页的加载状态与正在加载的元素,或是用线和圆表达网页间链接的地图(Map)[9],用户可以选择将不同的模块自由摆置在屏幕上。富勒相信这种替代性的浏览方式能够帮助用户深入理解网页的超文本性质,并且成功展现了从网络内在的物质性(作为数据流的HTML)中找寻再构造/重解释之可能[10]。
用富勒的话说,软件研究「应当将事物拖入游戏(putting things into play)」并「让事情发生(making something happen)」。在1996年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中,富勒与哈伍德(Graham Harwood)基于雅虎修改出了一个搜索引擎,当用户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种族主义或极右翼关键词时,引擎会将结果替换为一些写好的页面(并非屏蔽,而是替换)。通过模拟搜索引擎的正常运作,「自然选择」以一种戏谑的方式破坏了种族主义再现的可靠性。
The Web Stalker 与「自然选择」的共同性在于对软件的模仿,或者说,一种将行动与理论自动结合的构造:不论富勒如何从多方面解释 The Web Stalker 的能量——作为一种独特的既非艺术也非反艺术的「不只是艺术」(not-just-art),或是在开发方式[11]的可能——整个研究/作品的关键仍在于打开软件的「自然」,揭露其运作;类似的,「自然选择」看似意在抨击种族主义或极右翼,可是其核心仍是通过对搜索引擎之递归过程(关联性强或点击量高就会靠前,而越是靠前就越容易有高点击与关联,由此一小群技术专家设定的早期模型偏好可以相当大程度影响所有后续的结果[12])的破坏,达成对搜索、链接、界面等多种不证自明的要素的质疑。
杂交、综合与变异
试图在富勒的探索中找到「解蔽」的面向并不困难。然而,富勒方法的真正要义在于,由于破除遮蔽的道具是必须进行交互的「软件」(而不是某种理论),这就意味着,破除遮蔽的过程同时也就构成了新的经验(不再是作为「用户」的经验,而是类似网络街头知识(street-knowledge)的经验)的塑造过程,这也就构成了软件研究的行动面向:通过向这个专家的、商业的、经济的系统中加入各种微小的因子,使「软件」的意味发生改变——不仅是基特勒意义上的概念,即向硬件/真实的回归;也是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结合,一种朝向生产的综合(synthesis)与变异(mutation)。
在《界面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Interface)中,富勒延续了对「综合」与「变异」的讨论,并将之放在「界面」之中进行讨论。在该文中,富勒分析的重要对象是 Harun Farocki 的影像艺术作品「我想我正看着囚犯」(I Thought I Was Seeing Convicts)。在作品中,Farocki 截取了监狱摄像头画面,并将其与部分可交互的界面的影像并置(例如将实际开/关的门和监狱的门控系统并置,或是将在操场上的散步的犯人与表示这些犯人所处位置的定位系统并置)。

在对这一艺术作品与更广的界面研究的分析中,富勒区分出了三种界面:其一是作为普遍调控的界面,也即弥散在系统中的界面(如狱警并不直接控制囚犯,通过各种技术与纪律,他/她将囚犯调制进整个监狱的运作系统中);其二是作为索引地图的界面(如定位系统对操场的映射);其三则是作为关联结构或摆置空间的界面(如电子游戏将异质性的按钮、画面规则整合/摆置到同一套界面中,使不同要素在界面内部组合出一定的结构)。这种精确的区分[13](而非仅强调界面的「包裹/呈现」机制)意味着,富勒所要展开的并非一种简单的界面批判(通过智能面包机烤面包的学徒们似乎失去了和面包的真实联系,也无法做出好吃的面包),而是一种对重构界面的期待[14]:界面可能是牢笼,也可能通过其开放与重组带来「文艺复兴」,「正是通过它与什么结合,它到哪里去,它使什么发生,我们将知道它本身是否比通常的平庸更有价值。」[15]
富勒对「杂交」的渴望在《深长的灵魂来电》(The Long, Dark Phone-In of The Soul)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在此,富勒所分析的是「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也即一种极其初步的「人工智能」,文章处理的问题也并不复杂:无非是讨论人如何在面对非人智能(无论如何称呼)时的代理/能动(Agency)焦虑(不仅是对抗性的焦虑或被替代的焦虑,同时也包括一种不自觉的简化,即将自己缩减成软件/机器/数据库可以理解的特定要素的组合)。自然,正如富勒所说,面对这一状况,「一种反应是,从这种棘手的危险中退后一步,重新建立关系」[16]。相对的,另一种选择就是进入危险的关系,在关系中寻找重新调整的可能。
恰恰是在对这种重新调整的讨论中,富勒找到了两种模式(相当程度上,两次机械降神):神经网络与病毒。其中神经网络代表的是某种相互关联的系统内的「蝴蝶效应」,即通过微小的要素改变影响整个系统构造的可能;病毒则代表了那些根植于软件内部的形式逻辑却对软件本身早成了破坏的要素(需注意,是否遵从软件本身的逻辑正是「病毒」与「灰尘」的差异)。神经网络与病毒的结合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解代理/能动的模式:「病毒有感染策略,而神经网络的构造则明确地对新输入开放。
「正是这种微小的、有害的亲密性和开放性的结合,暗示了发展代理/能动的方式,使其既能参与事物的公共性和相互交错的关系之中,又能通过增加新的代理/能动种类,为其提供额外的缠绕性(tangledness)。」[17]神经网络与病毒结合的隐喻构造出了一种向错误开放的系统,这一系统不会产生免疫反应,或者说,这一系统唯一的免疫策略就是将所有病毒纳入其基因序列中,由此不断改变其构造。富勒没有追问这一系统在概念上是否可能,他所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可能:为了让智能代理更好地发展,有必要引入那些糟糕的东西(错误、愚蠢、混乱),用一点点的变异可能去导向错误而非服从。
正是这种对软件变异的渴望,一种似乎内在于软件之软(Softness)的冲动,带领富勒作出了全书最精彩的案例分析《看起来你在写一封信》(It Looks Like You’re Writing A Letter: Microsoft Word)。这篇文章是对富勒另一艺术作品(A Song for Occupations)的解说,该作品将 Word 的界面拆开成了不同的组件,试图「展开」 Word 复杂的结构及其与写作的关系。然而这一分析不仅关涉解蔽或是召回杂交所需要的各种「剩余物/垃圾」,同样也呈现出了以 Word 为界面组织起来的各种关系:
既有用户与软件的关系(「『当用户学习新系统时,语言将用户安装在系统中。』正是在这一点上,程序通过界面与用户进入组成」),也有设计师/程序员与软件的关系(「在计算机的原始概念基础结构中所规定的人类有机体的心理测量学、心理物理学、行为学设计参数的痕迹已经被留在了Word中,凭借的是将所有这些可怕的物质数量反刍到屏幕上所需要的纯粹痛苦的集中行为」);既有软件与生产/工作的关系(「Word对信息和交流没有直接的『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对信息和交流的促进作用……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选择正确的模板和勾选必要的成千上万个变量框,每一个可能的文件都将为生产做好准备」),也有软件与世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Word的激进性在于它绝对拒绝『Dasein』,即工匠、蹦极运动员和苹果牛顿的用户所经历的工具和行为的瞬间存在和融合」)。
作为全书中唯一一篇未采用MOD方法的研究(抛开作为导引的《在「哔」声后》),《看起来你在写一封信》完整地展现了软件研究的另一种可能(似乎可以看成一种更普通的,更接近文化研究的可能,然而它所具有的实际能量并不弱于偏向艺术实践的研究),即通过对软件的细致分析,展开所有被勾连其中的要素。正是通过对软件内在的自然的杂合的说明,富勒已不再需要通过MOD软件的「行动性」来展现变异之可能。软件从未像它们伪装的那样纯净,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忘记这一点,还是在「哔」声之前,带入更多的错误与混乱:「至少,我们还需要一些时刻,那些我们所知将成真的东西消失的时刻,那些我们对软件的确定性湮灭的时刻。是否可以开发出一种软件,它与语言一起抛出实现的时刻——对用户来说,一起抛出的还有设备,一些从其自身之中变得陌生的设备。」[18]
此处指 Writers, Texts, and Writing Acts: Gendered User Images in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一文,收录于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
此处是将计算机理解为一种多层次的「集合物」。Richard Feynman 指出有13层,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层级被卷入。对层级的挖掘不仅意味着对特定层级本身的理解,也打破了层级之间完美联合的幻象,带来了未来重新重组时的机会。 ↩︎
所谓的结构解蔽方法非常类似传统媒介研究的进路,只是更加技术化一些。真正将软件研究与其他领域区分开的是富勒与加洛伟等人对软件艺术的关注(根植于德国当代传统),这才导向了软件MOD作为研究方法的独特思路。 ↩︎
引文出自 Ellen Ullman 所著 Close to the Machine。 ↩︎
Behind the Blip,第30页。关于「哔」声是什么,富勒也给出了相当完整的解释:「这些『哔』是什么?它们是对生活过程进行的解释和归纳操作。它们是联想、逃避、痛苦、默许和喜悦等动态的统计残留物。它们不仅仅是一个事件的符号,而是事件的组成部分。银行余额中的数字,网络浏览器中出现的链接,都是具体的安排,是决定在一个特定的分析或使用系统的层次中潜在运动的相对程度的形式。它们有一个隐含的政治。它们的美学可以被描述为它们潜在的组合性或孤立性能力的范围,以及它对捕捉、发明、审问或飞行的允许,以及它们被放置后的,或和平或强制的节奏的结果。」 ↩︎
富勒总结了思辨软件三项工作特点,但我个人认为这一总结算不上精妙,仅仅是对破解「哔」声的一种拓展:「首先,它能够反思性地对自身和作为软件的条件进行操作——去它不应该去的地方,去观察哔声的背后;使它所连接的每一个小事件的动态、结构、制度和驱动力可见。其次,是让这些哔声和塑造和产生它们的东西,受到它们之间非自然形式的连接。使现成的数据、类别和主体的排序失去控制而痉挛。第三,就是要使这前两个阶段的后果服从于发明的浩劫(用新的创造替代旧的建制)。」 ↩︎
Behind the Blip,第43页。 ↩︎
团体最初包括 Matthew Fuller, Colin Green 与 Simon Pope 三人,The Web Stalker 已经是 I/O/D 项目的第四代。 ↩︎
用更现代的观念来说,这是一种较为初级的、不面向开发者的「开发者试图」。 ↩︎
由于文体是注记(Notes),富勒行文相当散乱,文中散布着大量有趣的细节,例如 The Web Stalker 为<IOD4>标签做了专门解析,而在其他浏览器看来,这一标签其实是没有特殊意义的。 ↩︎
这款软件由富勒等几个程序菜鸟用Lingo语言(完全不适合写此类程序,主要长处是绘图)写成,免费发放,不像普通「免费软件」满足于模仿商用软件。 ↩︎
现在的搜索引擎逻辑已和富勒描述的有所区别。在富勒所讨论的阶段,主流商用搜索引擎(如雅虎)仍有部分「黄页」的性质,今天的搜索引擎则看起来更为「中立」,其间变化仍需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 ↩︎
富勒也提到,三种界面仅仅是界面的三种面向。在不同的情形下,三种界面可能彼此重叠甚至彼此包裹。这一结论似乎比界面本身的类型学更容易理解。 ↩︎
富勒相当细致地描述了界面的脆弱以及内在与这种脆弱/易感性的可能:「即使执行它们的装置被设计制造出来,并数以百万计地分发,它们所体现的执行任务也可能改变或消失。这些设备将被删除或重新组合、部分使用、杂交。确保这种杂交化的功能开放性,才是软件界面设计的首要任务。」Behind the Blip,第115页。 ↩︎
Behind the Blip,第117页。 ↩︎
Behind the Blip,第123页。 ↩︎
Behind the Blip,第132页。 ↩︎
Behind the Blip,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