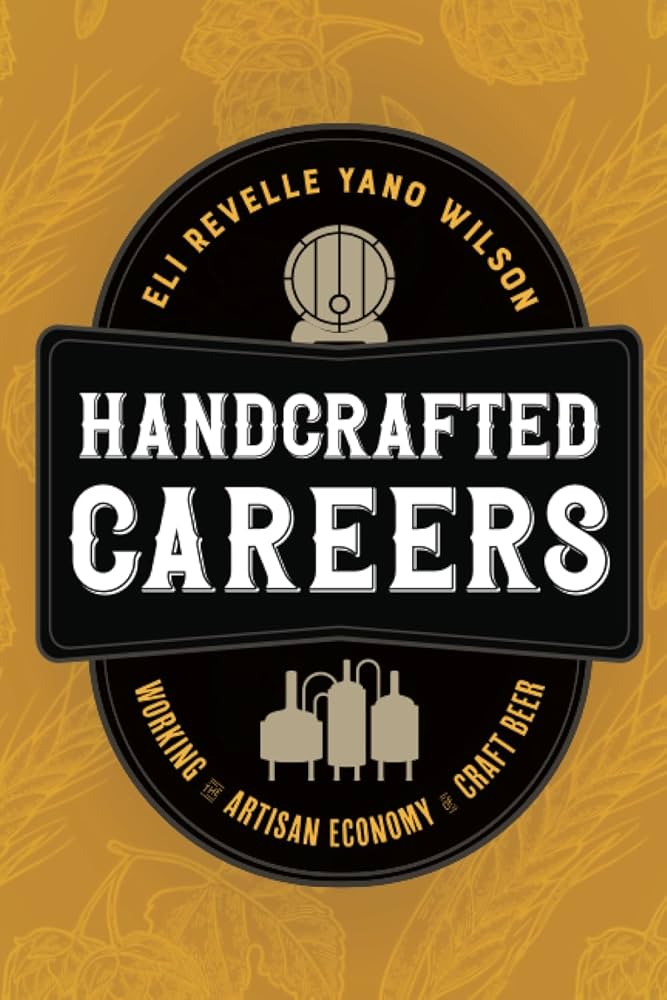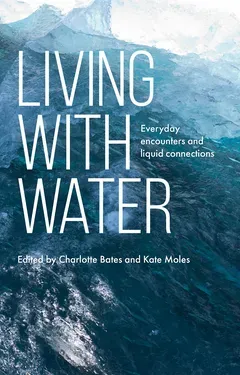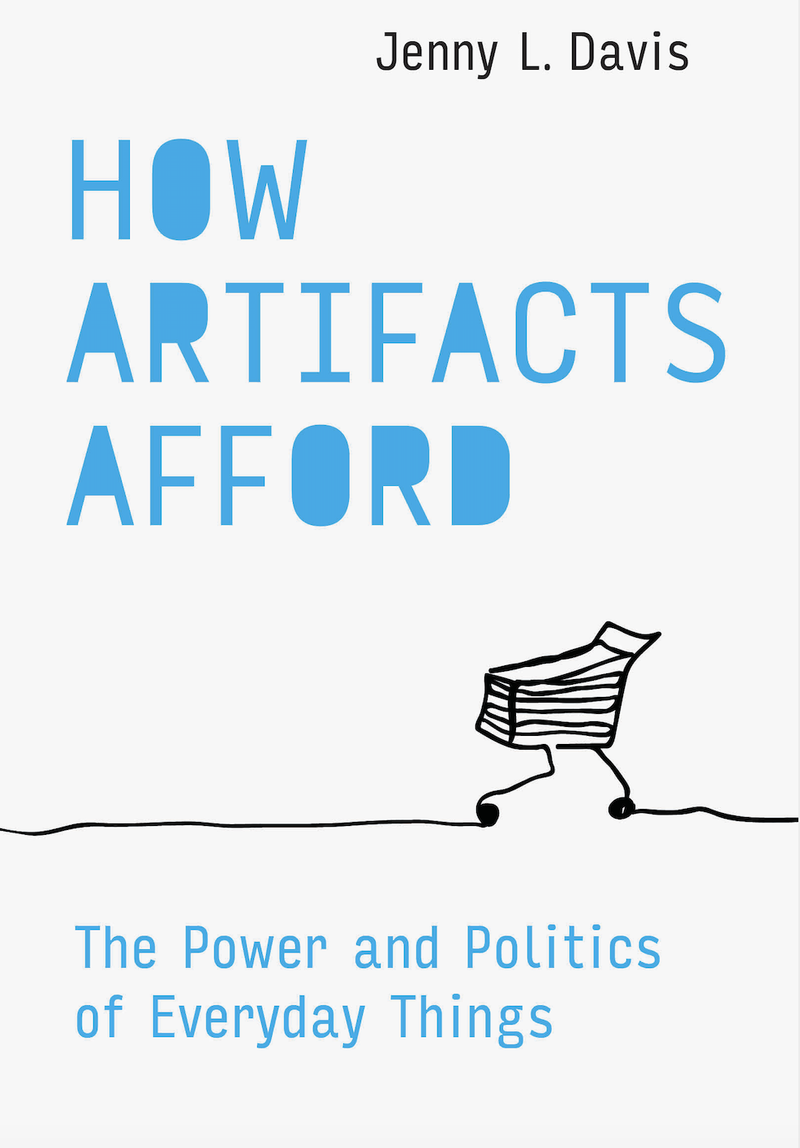人物的比照:两个家庭的形象塑造
《理智与情感》甫一开篇,奥斯汀便以一种人物简介式的处理方式,将埃丽诺一家四个女人的性格一一道来:「达什伍德太太性情急躁,做事总是冒冒失失。」「埃丽诺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虽然年仅十九岁,却能为母亲出谋划策。」「玛丽安各方面的才干都堪与埃丽诺相媲美。她聪慧善感,只是做什么事情都心急火燎的。」「三妹玛格丽特是个快活厚道的小姑娘……已经染上了不少玛丽安的浪漫气质。」[1]
借用小说的标题,在埃丽诺一家中,母亲、玛丽安与玛格丽特显然属于「情感」,而埃丽诺则被孤独地归类于「理智」一方。尽管奥斯汀并未解释这样的家庭中如何能生长出埃丽诺这个「异类」,但埃丽诺与三位家人之间的差异显然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异化:在许多情况下,埃丽诺必须帮助甚至替代母亲作出有关家庭生活的重大抉择,而这种抉择便赋予了她一种近似「家长」的身份,使得她在人物关系结构上也与母亲、玛丽安与玛格丽特构成了不同形式的「对子」。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也具有与埃丽诺相近的性格,区别在于「伊丽莎白观察力比姐姐(简)来得敏锐,脾性也不像姐姐那么柔顺,凡事自有主见,不会因为人家待她好而随意改变。」不仅如此,如果将两部小说中核心家庭的成员进行对比,我们将发现,除去多出的简、玛丽与父亲三个角色,其他人物的设置几乎完全一致:伊丽莎白与简的性格差异不大,母亲较为冲动甚至有些滑稽,玛丽安与莉迪亚一样情感充沛乃至不够检点,小妹则跟稍小的姐姐(玛丽安、莉迪亚)性格接近,只是仍旧处于成长状态之中。
伊丽莎白与埃丽诺共享着的家庭背景解释了她们身上诸多信念的来源。在《傲慢与偏见》中,母亲与妹妹们在社交场合中制造的诸多尴尬直接导致了伊丽莎白对她们的不满,更进一步使得伊丽莎白认为,问题出在她们未加节制的情感表达上[2]。在这一层面上,两部小说仍然共享着「理智」与「情感」的二元主题,推崇一种以理智控制情感的德性。这种德性在《理智与情感》中集中体现在埃丽诺与布兰登上校两位人物身上,不过他们的性格极为类似,在小说中发展出了相当程度的友谊,甚至可以说是惺惺相惜。然而《傲慢与偏见》中新引入的父亲、玛丽与简三个家庭成员却拓宽了作品对「理智」的展现形式。:父亲的理智是超然的,同时也是缺乏责任感的,正是这种超然的理智使得父亲鄙视母亲与这个家庭中除了简与伊丽莎白之外的成员,更使得他放弃了对女儿们有效的引导,差点铸成恶果;三妹玛丽的理智不仅不够健全,缺少了父亲对事实的洞察,此外更破坏了情感的表达, 使她似乎无时无刻不想着展现自我,总是以批判的目光对待家人,成了一个缺乏爱的能力的可悲角色;简的理智显然不如父亲与玛丽那样膨胀,仍会保持对家人、朋友的关心与呵护,然而她过度的圣洁与对人性的信任又使得她差点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概而论之,尽管支撑起故事情节的是一出关于达西品行的反转剧目,然而《傲慢与偏见》实际上延续并发展了《理智与情感》的主题。奥斯汀运用了完全一致的手法,通过塑造主人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张力,在主人公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不同感情经历中进行比较,使得简单的家庭成员的增加得以推进主题的深化,在保留了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冲突的同时将视角进一步拓展到了理智本身的运用上。这种视角的拓展集中地体现为故事中象征「情感」的家庭成员(母亲与莉迪亚)重要性的下降与象征「理智」的人物(简、父亲、玛丽)的重要性上升。正是基于对不同家庭成员的性格与情感经历的反思,埃丽诺与伊丽莎白最终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作出了相应的抉择,这些抉择或有一时的好坏之分,但在奥斯汀笔下最终都导向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自然的条件:缺席在场的父母兄弟
在较为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由于认为男性一般更富于理智,在家庭中负责计划、规制全家人的行动的应当是父亲或兄长这样的男性角色,倘若不存在这样的角色,则应当由母亲(长辈)来承担「理性」。然而在《理智与情感》中,由于母亲不过是一个年岁更高的玛丽安,她并不能承担其抉择的重任,于是身为长女的埃丽诺便成为了实质上的一家之主[3]。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傲慢与偏见》中。尽管那位「乖觉诙谐,好挖苦人」「不苟言笑,变化莫测」的父亲[4]充分解释了伊丽莎白性格中理智、幽默等等成分的来源,但他的超然却使得他实际上成为了这个家庭中的缺席者,仅仅在寻找莉迪亚与同意伊丽莎白的婚事两件事情上有所贡献。不仅如此,两部小说中的父母都无法有力的引导女儿们的成长,而且由于并不存在男性继承人,两部小说中的家产也都并不属于女儿们。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两个故事中的父母与兄长都在实质上处于缺席状态,但这种「缺席」本身却始终在场,贯穿着故事的每一步发展。正是父母兄弟的缺席使得女儿们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构成了故事发展的基础,而属于非直系亲属的财产继承权则进一步将女儿们抛入了相当糟糕的婚姻环境中,抽离了一种完全「纯真」的爱情的条件,使得婚姻中的经济考虑几乎成了一种必然。
不过这一状况的悖谬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失去了继承权,女儿们恰恰逃过了那些注视着财产的男人们,在她们的爱情中,财产的考虑变成了单方面的,男性不会再将目光放在她们的财产上,而是聚焦于她们内在与外在的美丽。如布鲁姆在《爱的设计》中所说,《傲慢与偏见》中,失去财产继承权的伊丽莎白得以褪去习俗(财产)的修饰,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得伊丽莎白拥有了一种被动的自由,建立在自由上的则是可以与男性对抗的平等,还有在选择中的盲目、冲动、理智与审慎。
在女儿们具有财产继承权之时,这种自由的权力属于男性,他们可以在财产或者真爱之间选择(就像威洛比所作的那样),而这种选择证明了他们自身,也证明了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是一桩严肃的事业,而非草率的抉择(如伊丽莎白与埃丽诺的母亲所做的那样)。正是财产的消失使得伊丽莎白可以较为容易地检验达西对她的爱,因此当达西第一次向她倾诉衷肠时,当达西提起他不会在意财产与她那些低贱的亲戚时,伊丽莎白拒绝了他,不仅是因为偏见,更是因为伊丽莎白无法忍受自己与对方在这段感情中的地位并不对等,自己仿佛接受施舍一般接受了对方「下嫁」的爱。
然而在事情的另一面,当伊丽莎白了解了达西真实的人格后,她感到感激与器重。而当达西逐渐变得温和、谦虚之后,她更加确认了,达西对她的爱是相当纯粹的心灵之爱[5],只关乎她个人,而不关乎其他状况。相当程度上,这种关注甚至超越了伊丽莎白的肉体:尽管达西也爱伊丽莎白的外表,但是他起初并不认为伊丽莎白美丽,而是此后才从「眼睛」这一具有象征的器官中逐渐发现了伊丽莎白的美丽所在。
如何理解伊丽莎白对于达西的复杂情感?奥斯汀给出的答案是将那些复杂的成分都当作爱情的基础或是养料,并且承认爱情并非简单的动物般的相互吸引,而必须是彼此尊重、理解的心灵的结合:「不过,世上还有所谓的一见钟情,甚至双方未曾交谈三言两语就相互倾心的情况,与这种爱情比起来,如果说由感激和器重而产生的爱情显得不近人情事理的话,那我们也就无法替伊丽莎白辩护。」[6]虽然奥斯汀表面上说要无法替伊丽莎白「辩护」,但她的故事却已经充分表明了她的态度:威克姆与莉迪亚的一见钟情差点成为一桩悲剧,而玛丽安与威洛比的一见钟情也毫无疑问是个错误。
这种状况表明,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其实存在着两种深浅不一的「自然」。在故事的表面,奥斯汀强调人应当以理智约束「自然」的情感表达,应当考虑各方面因素以决定自己的爱情归属,自然在此处应当被习俗所约束;可在故事的里层,奥斯汀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反,在那里,奥斯汀笔下的人物几乎拥有了一种浪漫派一般的习性,执意地相信着一种本真的纯洁的爱,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这种爱需要同时与那些理智的习俗的考虑所兼容,附着这种「纯真的爱」上的浪漫气息便又多了一层。
言辞的转变:间接语体与隐含作者
奥斯汀在爱情与现实之间起舞的尝试显然获得了成功,几乎没有人怀疑埃丽诺与伊丽莎白在情感与理智之间找到了某个恰当的平衡点,各自收获了一桩可以在达成自我实现的婚姻。然而奥斯汀个人的情感经历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平衡仅仅发生在故事之内;在写作的层面上,奥斯汀始终将爱情放在首位,不断尝试在爱情之中注入温和的现实考虑,而非将爱情建立在理智之上。
这种表达意图与表达方式之间的割裂集中体现在两部小说对于自由间接语体与焦点人物的使用上。在描写搬家后爱德华第一次拜访埃丽诺一家时,奥斯汀写道:「在那个当口,爱德华是普天之下因为不是威洛比而能被宽恕的唯一的来者,也是能够赢得玛丽安嫣然一笑的唯一的来者,只见她擦干眼泪,冲他微笑着。一时间,由于为姐姐感到高兴,竟把自己的失望抛到了脑后。」[7]在这一段描述中,「一时间」之前的状态都是常规的第三人称叙述,而之后的叙述则是通过间接语体直接描写了玛丽安的感受(第一人称视角)。从写作技术的角度看,间接语体的使用有助于表达人物的情感状态,并且塑造连续的阅读感受,而这显然是奥斯汀的一大特征。
问题正在于,奥斯汀在小说中往往还使用了焦点人物的手法,即通过将叙事的视角限定在女主人公的视野之内,借此来构造悬念、掌控故事节奏等。焦点人物的使用容易形成一种伪第三人称的叙事效果,使得读者无法区分故事中的叙事者与焦点人物,而在《理智与情感》中,这一状况甚至发展到可以将原文中大部分的「她」与「埃丽诺」替换为「我」而几乎不影响故事的逻辑[8]。当读者被焦点人物的手法迷惑,自然地以为叙事者实际上就是埃丽诺后,读者又会在除埃丽诺之外的人物身上时不时发现如上文那样自由间接语体的应用,并且它们往往是在借对应人物之口说有利于埃丽诺(叙述者)的话。两方面作用下,一种极其微妙的自恋般的效果产生了。
在《傲慢与偏见》中,由于有意识地将焦点放在了一些次要人物之上,并且收敛了除了伊丽莎白之外角色的间接语体的使用,《理智与情感》中不时出现的「自恋感」消失了。可是奥斯汀并未完全解决故事中人物声音混杂的问题,反而还因为更加直接的「说教」将作者本人的声音暴露在了故事之中。当奥斯汀写下「那我们也就无法替伊丽莎白辩护」[9]这句话时,她同时也就承认了,这个故事并不是被一个客观的上帝所叙述的,而是存在着一个有情感倾向的叙述者,并且考虑到焦点人物的手法,这一叙述者很可能就是埃丽诺或伊丽莎白的现实化身。
如此一来,不仅叙述者与女主角的关系遭到了怀疑,整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被瓦解了。尽管奥斯汀从未表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她同时也不能指出这些故事是虚假的。倘若奥斯汀真如评论家们所说,是一个道德家与一个幽默家,那么她道德家的一面必然会告诉她,一个故事的道德效果要求读者相信故事(至少在情感上)的真实性。倘若敏锐的读者在某个瞬间感知到,即便仅仅是微弱地感知到了,故事的女主人公或许就是那个叙述者,那么那些他人的直抒胸臆与被第三人称写定的情感表达[10]就将被看作一种「想象」,而并不能证明她的理智,更不能证实这种理智所带来的美好结局。
即便不考虑奥斯汀无意在叙事的声音间撕出的裂痕,我们只需进行最为简单的比对即可发现,这两部小说都并未能有力地表达婚后家庭生活的场面,奥斯汀用于证明埃丽诺与伊丽莎白选择之正确的不过是「(生活在)众多美德与诸般幸福之中」[11]这样的只言片语,仿佛一个充满理智的婚姻选择就已经足以带来幸福的家庭生活。这种状况表明,在这两个故事中,家庭是作为一种待脱离的状态而存在的,故事的主人公急于脱离的很可能不仅是自己那个不甚满意的原生家庭,更可能始终不会进入自己父母需要面对的那种家庭生活之中,而仿佛可以只生活在自己与伴侣相敬如宾的爱情里。这一状况不仅暗合着我们此前分析的两个故事爱情观的浪漫主义底色,更与作者本人的经历紧密契合。
在这一层面上,奥斯汀小说中混杂的叙事者的声音或许就已不是写作者的问题,而是过往人生经历给她本人留下的印迹。尽管她不停扭转着这个故事的结局,让那些理智的人们都找到了恰当的归宿,但他们却始终无法安静下来,而是不断轻声叫嚷着,勾勒着那场未完成的罗曼史。
奥斯丁,孙致礼译. 理智与情感[M]. 上海三联书店, 2014.p8 ↩︎
可参奥斯丁,孙致礼译. 傲慢与偏见[M]. 译林出版社, 2010.p83 ↩︎
母亲在找房子时特别考虑埃丽诺是否会同意便体现了这一点。可参奥斯丁,孙致礼译. 理智与情感[M]. 上海三联书店, 2014.p23 ↩︎
奥斯丁,孙致礼译. 傲慢与偏见[M]. 译林出版社, 2010.p5 ↩︎
阿兰·布鲁姆, 胡辛凯译. 爱的设计[M]. 华夏出版社, 2017.p223 ↩︎
奥斯丁,孙致礼译. 傲慢与偏见[M]. 译林出版社, 2010.p219 ↩︎
奥斯丁,孙致礼译. 理智与情感[M]. 上海三联书店, 2014.p82. ↩︎
通常的第三人称叙述在这样替换后会出现「透视」的状况,即人物看到自己不应当看见的事物或活动。 ↩︎
奥斯丁,孙致礼译. 傲慢与偏见[M]. 译林出版社, 2010.p219 ↩︎
如故事接近结尾处「他(爱德华)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不仅出自情人的狂喜,而且不管从情理和实际来说,他也的确如此」这一段表述在叙事者可能是埃丽诺的情况下便不得不损失许多情感上的力量。 ↩︎
奥斯丁,孙致礼译. 理智与情感[M]. 上海三联书店, 2014.p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