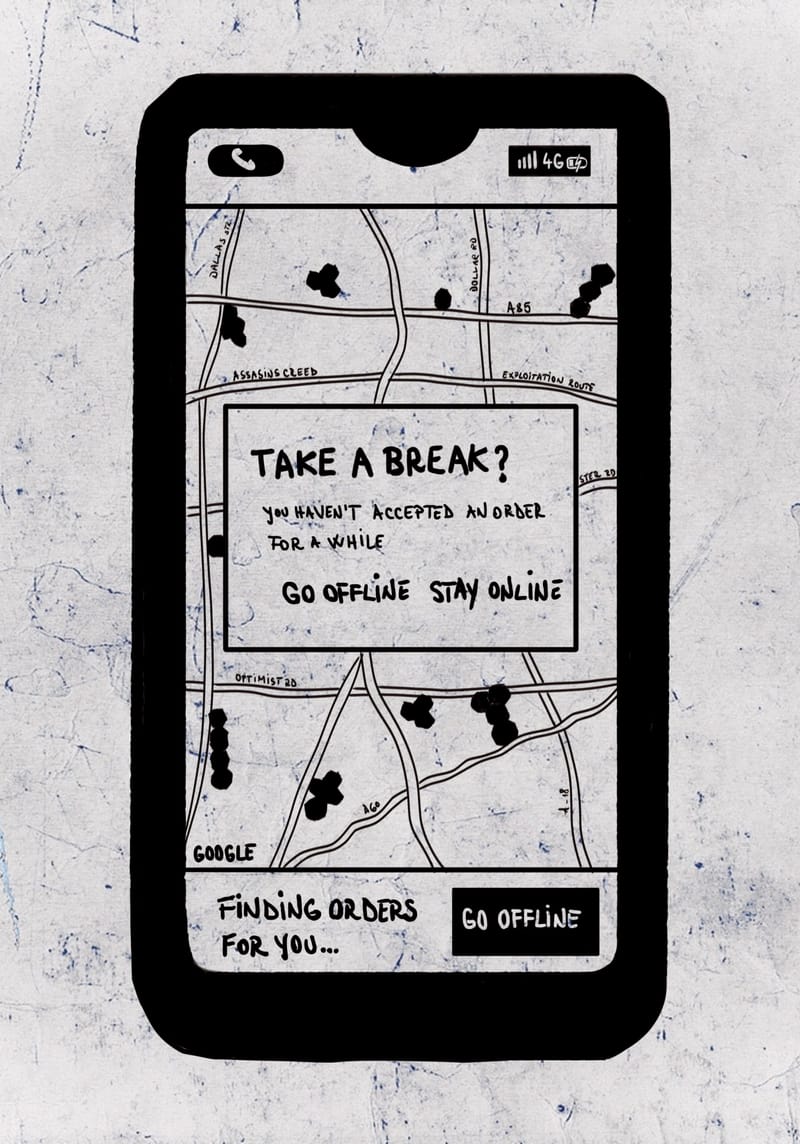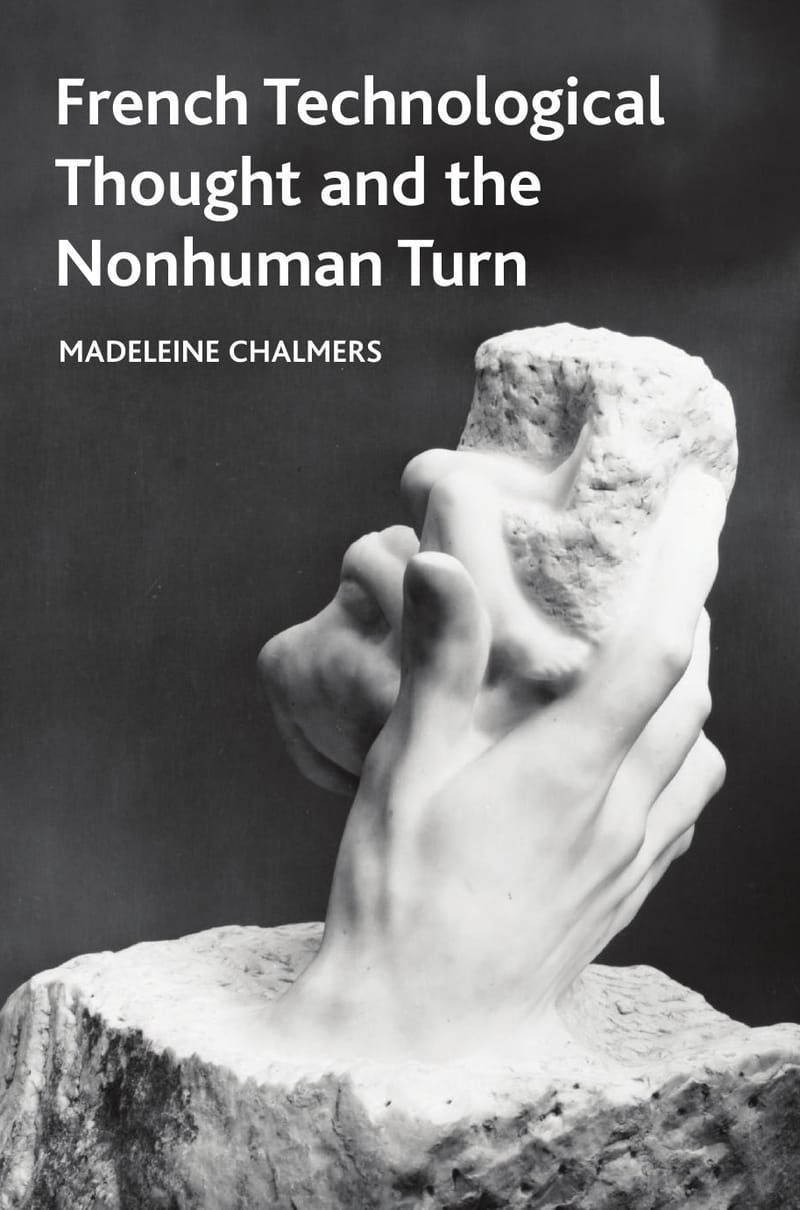通过将「线索与谜团」(clue-puzzle)定位在牛津或真的乡村宅邸中,侦探俱乐部及其同行赋予了「线索与谜团」重要性,在此之外,他们也非常喜欢思考这种形式的意义。在威尔斯(Wells)之后,与1929年雷吉斯·梅萨克(Régis Messac)的著作奇怪地并列,塞耶斯在其著名的文集介绍(Sayers,1928)中为「线索与谜团」赋予了古老的意义,以消除任何现代的不真实感——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圣经、伏尔泰都被援引以为其正名,如果不是作为该形式的来源。其他的评论家则用现代术语解释了「线索与谜团」意义。切斯特顿希望赋予其世俗化的宗教角色(Chesterton,1902),刘易斯认为这种神秘性弥补了「宗教的衰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C. Day Lewis,1942:xx),奥登则在颇具影响的《罪恶的牧师之家》(The Guilty Vicarage)疑问中赞扬「线索与谜团」。奥登断言,这种形式反映了基督教世界将谋杀像蛇一样带入伊甸园,并通过「来自外部的天才的神奇干预,通过提供有罪的知识来消除罪恶」,将罪恶感转移到单一可识别的凶手身上,使其成为替罪羊(W. H. Auden [1948]1988:24)。这个论点结合了基督教的慰藉和时尚的人类学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只要不应用于任何实际的故事,就可以成立。实际故事的开头与伊甸园不通,它充满了紧张感,后续则由可确认的凶手产生了无法接受的不忠、不可宽恕的罪行。虽然奥登的方法与切斯特顿和克里斯蒂小说中发现的「简单的邪恶」——满足于罪恶就在此世,且可以被驱逐——相吻合,但它并不能解释反复追求某些罪孽迹象的痴迷本质。
一种当代方法是弗洛伊德式的阅读,以一种完全不通的、肯定与迷恋有关的方式来解释内疚。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解读坡(1933),这个带有神秘污点、线索和混乱记号的夜间谋杀故事可以被解读为代表儿童对父母性活动的幻想,这似乎并不令人惊讶。杰拉尔丁·佩德森-克拉格(Geraldine Pederson-Krag,1949)推进了这个想法,用「原初场景」(primal scene)的术语阐述了利奥波德·贝拉克(Leopold Bellak)早期的建议,即暴力满足了本我,而侦探的行为代表了超我的审查秩序(1945: 403-4)。查尔斯·赖克罗夫特(Charles Rycroft,1968)在他的书《想象力与现实》(Imagination and Reality)中发展了这种性化的弗洛伊德式的阅读方式。这种解释非常有力,在原始场景理论中,知情但无辜的侦探和儿童的观察之眼之间有着清晰的关系,但很少有文学评论家愿意让犯罪小说被这种强烈的简化解释所控制。一般而言,人们更容易接受「线索与谜团」与心理学——比波洛所声称提供的心理学更严谨——之间的联系。齐泽克关于侦探作为分析家的描述(Zizek,1990;1992)似乎最容易被接受,尽管理查德·拉斯金(Richard Raskin)的分析可能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将完整的弗洛伊德观点和其他进路(包括更广泛的精神病学方法)结合起来,我们稍后再讨论。
一种本质上更加保守的解释方法是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因为它有意识地忽视了内容。在从技术美学角度评价犯罪小说方面,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是最著名的倡导者,他坚持认为犯罪小说本质上是一个类似民间传说的故事,尽管它具有「更高的复杂性」(1961:16)。由此,他将犯罪小说从政治现实中剥离出来,放弃了它可能具有的令人不安或激动的内容。巴赞与大多数读者的意见相左,但他并未感到烦恼:它的形式主义信念是他陷入一个奇怪的境地,即坚持认为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像《六座拿破仑半身像》(The Six Napoleons)这样的「纯侦查」作品比著名的冒险故事《花斑带探案》(The Speckled Band)好得多——这一判断表明,基于技术评估而非内容评估的进路有局限性。托多罗夫(Todorov,1977)用更严格的结构主义方法,将侦探小说这一子类型解读为双重叙事:一个由叙述者完成,另一个被谋杀者隐藏并由侦探破解。托多罗夫的方法原则上与内容无关,但它是拆解故事的有力工具,对内容乃至意识形态分析都有价值。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主要以子类型为基础并进行描述,该进路影响了格雷拉(Grella)与帕内克(Panek),前者将「线索与谜团」形式理解为一种人们想做就做的无害的民间故事([1976]1988),后者则跟随弗莱,认为整个活动具有游戏性、缺乏冲突,并坚持观众必须仅仅欣赏这些怪异而诱人的实践(1979: 18-19)。约翰·卡韦尔蒂(John Cawelti)也将他的结构分析与弗莱相连,将犯罪小说主要视为「一种仪式戏剧」(1976:90),但他一直留心语境、观众以及他们在文化上(如果是不再政治上)对他们所享受的模式做了什么。
如果这些作者倾向于将犯罪小说基本看作一种无涉价值观与社会政治意含的文化现象,那么对「线索与谜团」的崛起和力量的另一些解释则与语境更密切相关。人们通常认为,「线索与谜团」子类型消解了战后的焦虑。一些分析家认为,这种小说的作用在于忽略当时的冲突——普里斯特曼将之视为「一种田园诗」(Priestman,1990, 第九章标题);其他人则认为该子类型将压力转化为可管理的形式——范·达因(Van Dine)的编辑马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在此看到了「一个悲剧十年的焦虑与痛苦」(Tuska,1971:20)。对犯罪小说的「线索与谜团」形式中的替代机制最彻底的研究,来源于理查德·拉斯金(Richard Raskin,1992)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它在四个层面上吸引了读者的注意:首先是「游戏性」(Ludic),作者与读者的游戏,读者享受这种竞技;其次是「愿望实现功能」,涉及读者与凶手、侦探和被害者的认同——受虐狂在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出现;再次,拉斯金描述了更加难以捉摸的「缓解紧张功能」,通过惩罚恶棍,以及更令人不安地,通过容易受伤的被害者如愿以偿地死亡,小说成功转移了焦虑——齐泽克在它对侦探作为分析家的讨论中有更深入的探索。最后,广义地说,拉斯金提到了「定向功能」,涉及社会神话或更现实地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问题:阶级、种族、性别等等,以及犯罪小说——如此具有说服力的——潜在政治,这些模式已被社会政治倾向的评论家如奈特(Knight,1980)、波特(Porter,1981)和曼德尔(Mandel 1984)讨论过。
拉斯金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男性假设,而女性主义犯罪小说作家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认同和紧张缓解机制——这将在第八章中讨论——但是将拉斯金的类别用于主要的犯罪小说文本,仍可以发掘出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他有力地指出,这种形式之所以成功,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好的谜题,而且因为这些好的谜题能够同时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对深刻且困扰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编码。
基于美国的私家侦探形式在上述两方面都与「线索和谜题」小说家有所不同,不论后者来自英国还是美国。
翻译自:Stephen Knight. Crime Fiction, 1800-2000: Detection, Death, Diversity. pp. 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