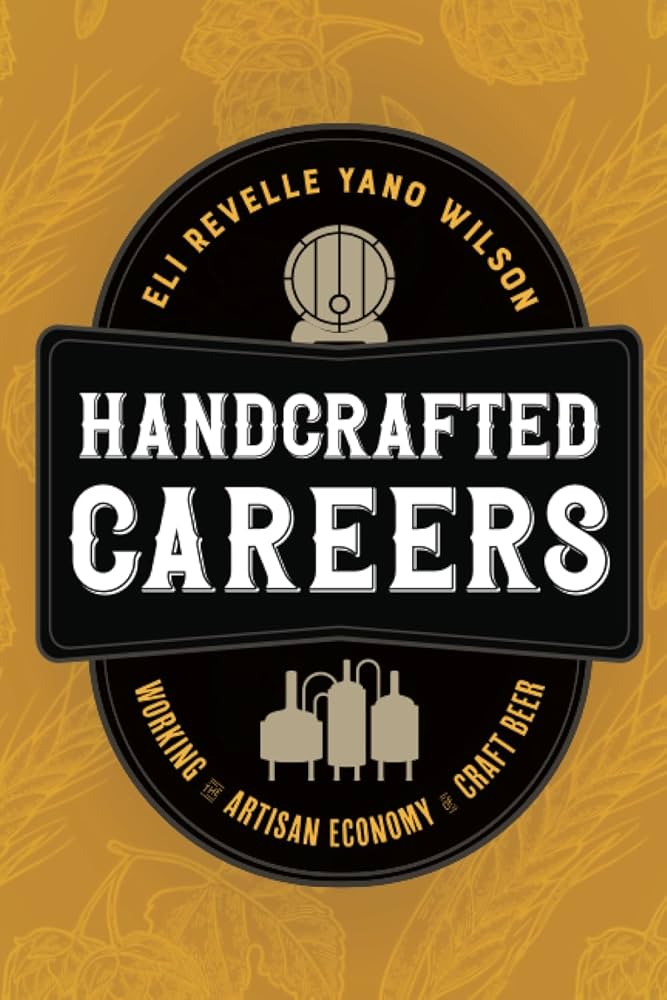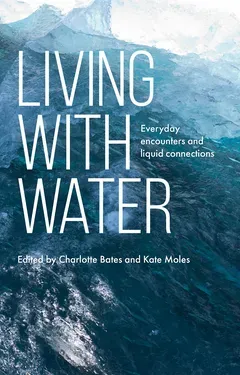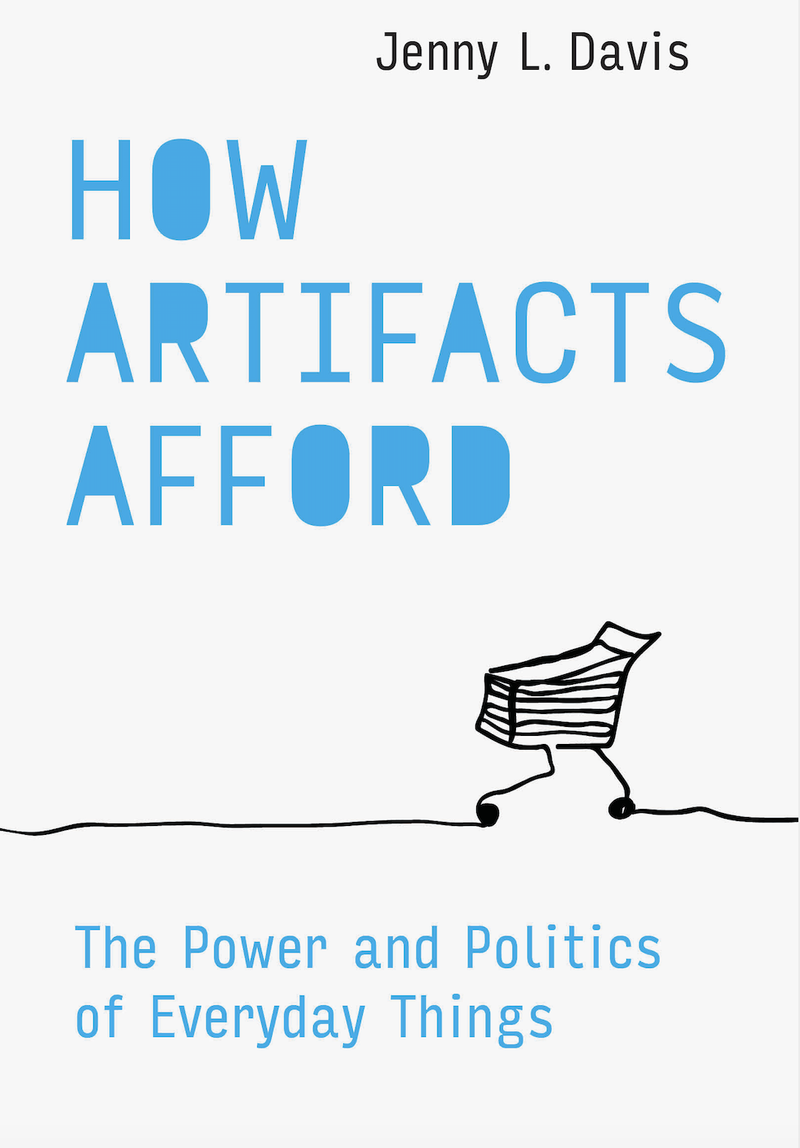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与《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中[1],东浩纪对AVG游戏[2]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相当有效的分析,并将这一结构统合在「游戏性写实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下。概括来说,所谓「游戏性写实主义」是一种与「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相对立的创作理念,后者为近代以来的文学所广泛使用,认为文本需要模仿或者至少部分地模拟「现实」,折射、反映出「现实」;而前者则直接刺破了虚幻的「现实」,希望建立起(或者说选择)一种全新的栖居之可能。
在东浩纪「症候式」阅读[3]的方法下,2000年代的AVG游戏以其整体上出奇一致的叙事结构与策略,反映出了「御宅族」世代的心灵问题:懦弱的他们既为无能自豪,害怕也无法成为「父亲」,同时又是如此渴望「父亲」的权力,于是便将这种矛盾的欲望倾注到AVG游戏(美少女游戏)中,构成了游戏中「可选择多个分支的滥情」与「分支内的纯情幻想」之间的结构矛盾。在东浩纪看来,这种叙事结构的矛盾可以更进一步地反映出社会的「后现代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集中体现为「大叙事」的崩溃,与多元的「小叙事」的兴起。
所谓的「游戏性写实主义」正是尝试借助游戏描述这一状况,而支撑其这一理论的关键有二:其一是「大叙事」与现实之关联;其二是「小叙事」与选择之关联。概括来说,在近代以来的所有宏大叙事中,最为基础性的叙事便是认定存在着一个「现实」,而「御宅族」们沉浸在游戏中的状况恰恰暗示着这一叙事的崩溃;相对的,多元的「小叙事」在形式上就首先对应了游戏中产生的一个个小世界,且AVG游戏中对选择、分支的强调更是在游戏内部就生产出了复数的世界/历史,而无论是在游戏之间选择,还是在游戏内部进行选择,对于选择的强调显然也与外部世界的人们的心灵状况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形如同构。
然而东浩纪的理论核心却存在着的相当暧昧的部分:一方面,他认定大的叙事崩溃了,生活形如AVG的结构那样,是在一个个世界/历史之间选择的过程;然而另一方面,预设了存在着一个「游戏外的生活」本身就假定了「真实世界」的存在,并且构成了某种「大叙事」。这种矛盾进一步地体现在东浩纪态度微妙的变化之上:从《动物化的后现代》到《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尽管仍旧自称御宅,但早就结婚生子的东浩纪对待御宅们的态度已不再如原来那般温柔,更不再尝试避免论题的政治化[4],反而是直指「萌的本事,止于无能」,彻底将问题暴露到了社会空气中。
正如东浩纪尝试以后现代社会的心灵状况解释游戏内部的结构性矛盾那样,对其理论之暧昧的最佳解释便是他的父亲身份与御宅族的固有属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视角转变带来的理论生长同时也就暗示着,推进其理论的最佳方式便是尝试转换焦点,拓展其分析范畴,在此过程中检查理论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不妨就以与AVG游戏相去最远的大型开放世界游戏[5]为例。在将东浩纪的理论运用到开放世界游戏上时,一个最明确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无法分清到底是御宅们对着二次元美少女释放情欲显得像动物,还是沉迷在砍杀、升级的心流之中更去人格化。如果按照东浩纪的设想,「动物化」是后现代社会的一项特征,那么AVG游戏与开放世界游戏似乎就指向了两种「动物化」(甚至可能是两种「后现代」下的模式),前者可以概括为「性」的本能(成为「父亲」的愿望),后者则可视为某种「摩擦」成瘾的症候[6]。
不同的「动物化」模式显然与不同游戏形式本身的游玩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AVG游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事件化」的模式,即通过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段事件化,赋予其决定命运的魔力,以便赋予选择以游戏性(game play)。这种模式的极致代表便是东浩纪提及的「世界系」:越过民族、国家等范畴,将男女主人公(往往是高中生)的生活与人类世界的存亡直接关联在一起。在此意义上,AVG游戏对待事件的方式是严肃的,尽管玩家无法定义事件,可一旦一些片段从文字中跳脱出来,形成了事件,提出了选项,玩家就有理由相信,到了自己介入的时刻。
对于游戏而言,控制/介入是一组重要的关键词。对客体或事件的控制/介入是建立起主体性并进一步确认此在的必要步骤,玩家如果要选择某一游戏(即选择某一世界)便必须要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一定的主体性,换言之即是保证一定的控制能力。而正如东浩纪所分析的那样,在《Air》《寒蝉鸣泣之时》与《Ever 17》这类具有症候性的AVG游戏中,作者便是通过使玩家无法介入其中(不提供事件/选项甚至只提供虚假的选项),来实现对御宅之「无能」的一种强烈的同时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讽刺。
在此意义上,开放世界游戏可以说是完全站在了AVG的反面。开放世界是一种对世界完整模拟的尝试,可以放在东浩纪所说的「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范畴下进行理解,其主要结构并不依赖于明确的事件维持,而仅仅需要玩家通过控制人物与世界进行「摩擦」(互动),只要人物仍在走动,能够与他人交谈,则就还存在着一种类物质的「摩擦」过程,个人也就能够建立起主体甚至投射出某个身体。可是在AVG游戏中并不存在着「摩擦」意义上的快感(点击鼠标控制文本显然不能构成有效的摩擦/互动),玩家主体性的确立(某种意义上也是游戏性的确立)要求结构本身能够提供某种游戏要素,不若便只能将AVG降格为「小说」。
不妨认为,AVG将游戏性集中在了命运的多重性与未知性上,其典型的游戏体验恰如博尔赫斯所描绘的那样:玩家身处一个小径交错的花园,通过在不同的小径之间穿梭,以游戏外的视角(第三视点)审视与综合游戏内的路径,从而获得关于花园的总体性认识。然而花园中必须存在着一个上帝(上帝视点),用于保障结局的有限性与过程的有限性,不若则玩家无法确认整体的花园图景之意义,花园将被无数身影填满,故事无从诉说,也就无人会进入这个意义的荒原。
与意义之荒原对应的恰恰是开放世界的整体图景。尽管大多数开放世界游戏仍会存在着一条主要线索,用以赋予世界与玩家意义,但开放世界游戏的核心却并不在此,而是在于摩擦/行动本身,也即某种意义上的「身体性」。进一步的,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与开放世界或是车枪球等强调身体要素的游戏相比,AVG游戏似乎是一种「被诅咒」的游戏类型,其本身确切地不支持无结局(即便在故事意义上烂尾了,游戏文本也必然有文本收束意义上的「结局」),因为事件/选择与结局对其来说存在着本体论式的意义。
事实上,即便是传统上认为最重视剧情的RPG游戏都存在着事件/选择与结局之外的游戏性。只要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战斗系统、采集系统、收集系统,剧情于RPG来说便永远不可能有如在AVG中那般重要,因为角色扮演(亦即角色主体的确立)仍可通过与世界「摩擦」来实现,事件/选择与结局便永远不构成游戏的本质,而只是一种赋予意义的便利工具。
这种对比进一步地指向了,AVG游戏或许是众多可以无结局的游戏类型中较为异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AVG游戏的模式是以有限的事件/选择对应有限的结局,而开放世界则是以无限的事件/选择对应无限的结局[7]。更简单地说,AVG游戏是目前所有游戏类型中,唯一结构是封闭的、线性的。对于AVG模拟出的世界来说,结构宛如蛛巢,文本在其中穿梭,重点并不在于线路,而在于节点(事件化的部分,变成选择的部分)——即便是一个完全没有选项的AVG游戏也必须在结构上保有分叉性,或者说越是想要去除选项,便越需要在叙事上呈现出复杂的线性结构。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AVG游戏并非是通过文本在进行叙事,其核心的叙事手段是一种复合的线性结构(有时也包含某种映射),而这种结构也就使得,在对世界的模拟上,AVG始终呈现出的是一种宏观的视角(这充分解释了「世界系」中的日常生活与人类命运之间不和谐),因为必须存在着某种宏大之物(第四视角)带领角色/玩家(第三视角)兜兜转转,以保证角色/玩家的抉择不会导致世界的崩塌。相对的,开放世界或者说以机制为中心的游戏聚焦于一种物理性的摩擦上,其本质在于模拟人与世界之间一种互动过程,而并不开放一种宏观的互动网络。
进一步对照AVG与开放世界中的叙事模式,我们似乎能够发现某种悖论。在游戏性意义上相当单一且只拥有有限选择的AVG游戏往往拥有复杂的结构与主题,并以结构框定故事的意义,将之收束成一个封闭的文本;而在游戏机制上非常复杂的开放世界游戏则往往借一个英雄史诗性的故事赋予行动意义,再将其发散成一个可以不断行走以生产摩擦的世界,形成一个开放的文本。对于开放世界游戏而言,一个典型的问题便是叙事-机制的冲突(Ludonarrative),也即机制生产出的微小但持续地「摩擦」可能影响了整体的故事叙事,进一步消解了故事与世界的意义。
不妨将叙事-机制的困境同样理解为某种后现代状况的隐喻[8],无限的选择带来的是无限的自由,然而自由建构的问题却在于需要个体自主担负起整个此在的意义(「自我叙事」),最终导致了确定性的缺失甚至更进一步的情感缺失。如果延续东浩纪的论述,将个人在不同故事间的选择理解成在不同小世界之间的抉择,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所谓的后现代状况下,个人的情感维系最终是关涉到整个世界(此在)的,而开放世界所固有的随机性则会动摇整个世界的意义基础。例如当人们在讨论《上古卷轴》或者《辐射》的世界时,实际出现的总是那些被编剧(上帝)精细设计出的故事(剧情、任务甚至任务的奖励),而并非程序随机生成的随机任务或是野怪。另一极端的例证则是早期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无人深空》,其中各式妖魔鬼怪正是随机性之意义深渊的绝佳隐喻[9]。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AVG游戏与开放世界共同面临着的某种状况。如果延续东浩纪的理论,我们则可以进一步指出,AVG游戏与开放世界实际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以应对这一状况:AVG游戏并不试图重新描绘或是控制「现实」,而只是再造一个隐喻的结构以投射自我的欲望;相对的,开放世界则仍旧秉持着某种近代以来的自然主义观点,其根本在于身体性的「摩擦」,而欲望与主体性等等则均挥洒在这一摩擦的过程当中。概言之,AVG游戏之症候反映出的是「控制的虚幻」,而开放世界则一直意在达成「虚幻的控制」,两者折射出的都是某种「无能」的状况,但其症候性表达却有所区别。
倘若尝试进行一番外部视察,则毋庸置疑,无论是日本的御宅族抑或是喜爱开放世界的游戏爱好者们,其现实生活即便不具有(在东浩纪所述的「小叙事」与「选择」意义上的)后现代特征,至少也处于某种现代与后现代的界限之上。因此在游戏中再造一个自我或是陷入游戏的世界中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其本质与瑜伽、健身、任务管理等等现代迷思一样,都是现代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试图控制自我以达成某种确定性的方式。这种自我控制在叙事学上也可以表述为东浩纪所说的从「故事中心」到「角色中心」的转变(不难理解这一转变与从「大叙事」到「小叙事」之间的同构关系),其关键似乎在于,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能面对「真实的」他者,而是直接与世界体系中的一些功能性角色直接互动,这也就导致了个体对于他者的抽象性理解(即「你不是你,而是一个送外卖的」[10])。
可是世界终究需要是某种此在,不若则切身生活其中的个体将无法找寻栖居之所。因此在面对不断强化的分工体系下的抽象他人时,个体不得不进行一种结构性的假想,即一边通过功能符号设想他人的生活[11],另一边尝试将结构收束成一个自己能够理解的故事(「外卖小哥的工作也很辛苦啊,我还是给他一个好评吧」),以表示自己仍旧能够对世界有所了解甚至控制。在这一视野下,无论是AVG游戏还是开放世界,其构造都转化成了一种充满孤独感的「自我叙事」。尽管玩家往往乐于在网络上沟通、交流关于游戏的种种经验,但恰恰是这种交流反映出来了这一叙事内部的不完整[12]。
是要肯定虚设的世界还是试图寻找一种平衡?这一问题本身并没有答案,因为虚设的世界从来都离不开所谓「现实」的背景,更离不开物质的身体。然而虚设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一种全新的真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东浩纪想书写的新日本文学史还是目前尚未出现的存在着思想脉络的游戏史,游玩的欢乐与游戏背后暗藏着的孤独都成为了其中必不可少的插画。
在作业提交时,本文已经发布在机核,文章名同上。(不是抄袭啦。) ↩︎
Adventure Game,广义上是指所有以文字叙述为核心的游戏,狭义则是指「美少女游戏」(girl game)。 ↩︎
书中将这一方法称为「环境分析式的解读」,但其意在通过文本的裂隙勾连内外发现「病症」的方式与症候式阅读方法完全一致。 ↩︎
已有不少批评者指出,东浩纪的分析刻意避免了政治哲学化,尝试进行一种纯粹的文化分析,然而《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一书显然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政治化倾向。 ↩︎
为了强化差异,我们此处限定是3D的开放世界。 ↩︎
从东浩纪擅长的精神分析学的视角看,很难不认为这种「摩擦」成瘾也是一种性欲或是成为「父亲」的愿望的变相体现。 ↩︎
在此我们假定「是否击杀面前的怪兽」或是「是否向右走一步」这样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最基础的事件/选择。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并不认为人们已经普遍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状况。后现代仍是属于少部分人的,更多的人仍身处现代甚至前现代状况之中。这一整体图景导致的道德困境可参考《现在,在海拉尔 ——<荒野之息>中的后现代主题》一文。 ↩︎
一个反例或许是Roguelike游戏。尽管Roguelike游戏已经将随机本身转化成了一种乐趣,但是这类游戏是典型的以结构进行叙事的作品,其故事本身就是「随机」或者说「数值」,也正因此故事才不会为「随机」所影响。不过另一方面,在Roguelike游戏中如果真的是完全随机出现数值,玩家恐怕也很难接受,设计者对数值范围的限定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叙事(所谓「数值设计」)了。 ↩︎
这种认知显然非常近似于游戏世界中主角对NPC的认知。可参见《现在,在海拉尔》中的相关讨论。 ↩︎
这一过程与东浩纪所说的「数据库模式」非常相似,与语言学、常人方法学中的日常沟通的「索引性表达」也非常相似,不过是将语言中的索引转化成了某种绘画的或者现实的符号。 ↩︎
有关游戏之外的沟通这一点,可以尝试在东浩纪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初步的观察:开放世界游戏恰恰是内向的,因为欲望都可以在其中释放,太快地实现了「控制」与父亲的角色;但在AVG中,由于特定的结构叙事,玩家/主角永远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因此必须向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