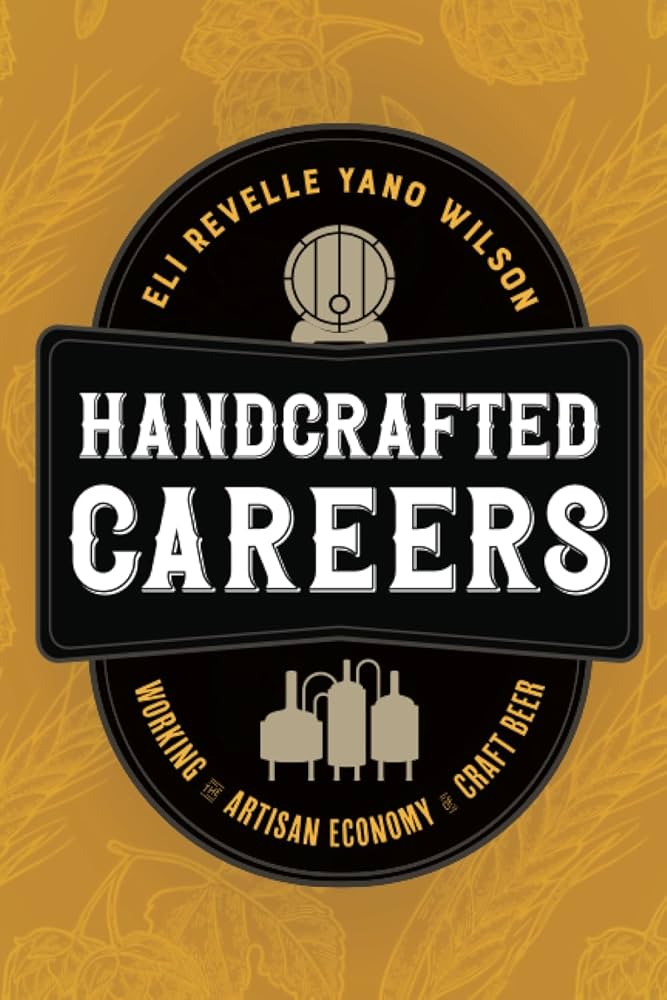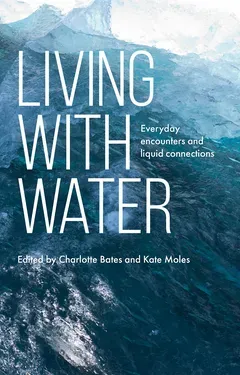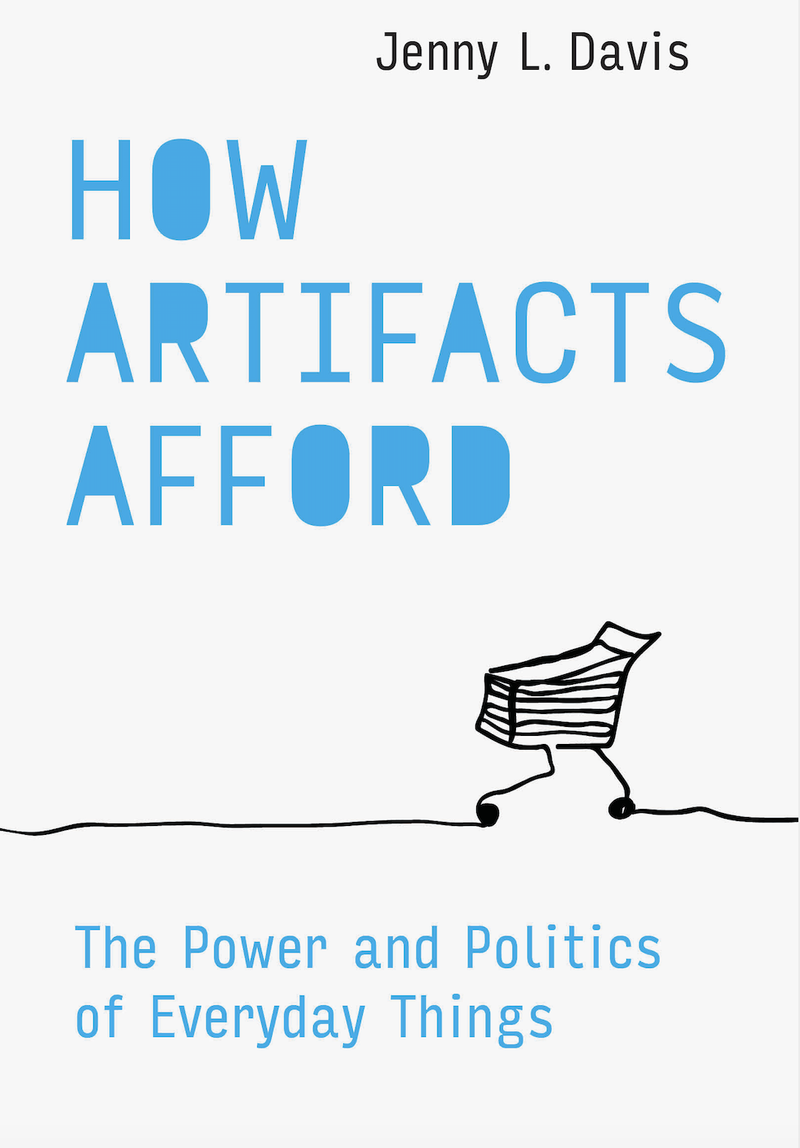一、引论
有关两晋南北朝间名教与自然的讨论,近代以来较为有名的有二:其一是鲁迅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二则是陈寅恪于《金明馆丛稿》中所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等文章。此二种文章立足之处虽大相径庭,日后发展出的研究更是面貌殊异(鲁氏文章所开辟的是当代所谓「文学史」研究,其重心在文不在史,而陈氏文章则属历史学一脉),可究其所关心之根本问题,却是殊途同归。
究其原因,论者之文章自不会背离其身世,鲁氏与陈氏所处之时代正如魏晋:分裂、变革、融合乃是时代之主题,新旧、内外、华夷之间如何作出取舍,世人又如何于此乱世间留得一份独立、自由之可能乃是时代向论者所提出的问题。于是不难理解两人同时将目光聚焦与两晋南北朝之间,且一并关注着魏晋诸子与名教及自然之关系。而今日重审这一研究主题(尤其陈氏论述),自然也与当前时代的命运(或至少与论者自身之抉择)息息相关。归根结底,史既从史出,亦从己出,此乃理解陈氏论述之根本。
是以为引。
二、名教:士大夫之统治逻辑
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末尾,陈氏指出,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身上似乎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尊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欲解此语,不妨再查此文前后,陈氏在评《世说新语》中「王子敬病笃」一则时说:「然则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1]
尽管此则故事所证乃沈氏的天师道信仰,「此义」却包含了陈氏对于中古文化史的洞见。不难理解,于陈氏而言,两晋南北朝士大夫之周孔行事与老庄自然之间冲突,其形成原因必离不开「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与时代风潮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也在更广大的层面上指向了中古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根本脉络。
自然,在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厘定讨论的基本范畴,即审视陈氏论述中的士大夫所指何人何群,名教、自然又分别为何物,其意涵是否存在着变迁,与士大夫之间又有着何种的「互动」关系。
查陈氏《金明馆丛稿》两册,不难发现,其中所用「士大夫」之根本属性有二,其一是文化属性,即须为文人;其二则是政治属性,则须为官或至少存在着为官的可能。结合秦汉之间尤其东汉以来对官员的选拔体系(征辟制度)与教育系统来看,附着于士大夫身份上的文化与政治属性进一步转化成了某种家族属性,即士大夫须为名族出身(至少与名族之间存在着姻亲等关系)。于是,仅从字面理解,便可大致察觉名族与名教之关系密切,如陈氏所论,遵守名教即服膺儒教,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即所谓孝友、礼法等。而按老子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又云「始制有名。 」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所谓名教,按照魏晋时人解释便是「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换言之,所谓名教之下所体现的是一套基于周孔之学,由家庭延伸倒君臣、家国之间的统治逻辑;而自然则是对于这样一种统治逻辑的反对、抵抗或放弃。
这一统治逻辑集中体现在有晋一代的君臣之间。《晋书·礼志中》略云:「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武帝亦尊汉、魏之典,既除丧葬,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撤宴。太宰司马孚等奏敕御府易服,内者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抱朴子·外篇·讥惑篇》又云:「吾闻晋之宣、景、文、武四帝,居亲丧皆毁瘠逾制……于时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为法……」两则材料所体现的便是晋代皇室自宣帝至武帝都重孝、礼,以至「居亲丧皆毁瘠逾制」,超过了丧礼之规定,以体现自己对孝、礼的尊重。
在这种体系之中,孝乃是一种道德标准,礼则是一种行为规范。晋室君主对名教(孝礼)的重视必然会延展至臣子之中:逻辑上看,一方面,臣子自然需要应和君主之需;另一方面,也正是那些重名教之人才可成为「臣子」。不过也正如陈氏所论,实际上无论君臣,名教其实都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司马氏既以《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杀嵇康,也可以三大孝之名义让王祥、何曾、荀顗等人致位魏末晋初之三公[2];同样,于臣一面,王祥等世家可以名教位极人臣,嵇康、阮籍等人亦可以反名教宣告对于晋政权的不认可。其间名教与君臣的关系绝非单向的关系,而是牵涉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层面上诸多势力的互动。
三、自然:反名教的身份政治
有关两晋之间「自然」的讨论,自然无从脱离「清谈」。但清谈本身并非一成不变,陈氏认为在两晋之间,清谈之含义与风气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
暂且略去此一转折的原因不论,陈氏所言清谈与士大夫进出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便是指本文此前所述名教与君臣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即士人于魏、晋之间的身份立场抉择。不妨以竹林七贤为例来讨论此一话题:如陈氏所云,嵇康乃七贤中主张自然最激烈之领袖,《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嵇喜撰《嵇康传》云:「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於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但嵇康本人似乎却并不认为这一主张之绝对正确,在留给儿子的《家诫》中嵇康所言却丝毫没有自然痕迹,反而尽是其从不遵守的世俗教训:「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
嵇康所呈现出的这种冲突恰恰暗示了其追求自然的「政治属性」,即以非名教追求自然而反晋室。而此一意图又与嵇康之身家密切相关:「康娶魏武曾孙女,本与曹氏有连……而因姻戚之关系,以致影响其政治立场则一也。」与曹氏的姻亲关系既是在情理层面提供了不与司马氏合流之理由,更暗示着魏晋之间的自然与名教之争延续了东汉以来寒族与世族之间的对抗逻辑。
出身贫寒的曹魏素有节俭之风,《三国志·魏志·崔琰传》云:「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即是一例。但以节俭反对世族门阀之浪费不过曹氏与世族对立之侧面,出身官宦的曹氏若欲在汉末称帝,其必得打破与汉代统治紧密相关的世族的名教观念,而这一企图之最佳体现便是曹氏的求才三令:「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简言之,曹氏求才三令所说大意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也常负不仁不孝之污名,其意实在说明秦汉以来儒家世族安身立命之根基不过虚妄,并借此获得寒族人士乃至部分世族人士之支持。
由此不难理解,曹氏之倡导自然(尤见于其诗作与政令之中),乃是基于家世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差异,发起的对于名教的抵抗;自然本身的形态是模糊的,其定义即是名教之背反,因而自然与名教之间绝不可弥合。但此种自然终究难以维系,曹操死后,缺乏有力统治者的曹魏很快迎来了世族的反扑,如陈氏所言,众多过去服膺于曹魏之下的世族开始转而支持司马氏之势力,是以最终完成世族对于寒族的反扑。
在此一历史背景之下重观陈氏所述竹林七子之不同境遇,便最终可得一妥当之解释:七子于自然与名教之间所作之抉择,等同于在曹氏与司马氏之间所作之抉择。七子之中嵇康、阮籍、刘玲、阮咸四人始终持不加合作之态度,故而与曹氏有姻亲的嵇康遭杀,阮籍虽尝「禄仕」却依旧保持其放荡不羁之行为,故也为司马氏所杀;刘玲、阮咸虽未遭大难,却也「至少对于司马氏之创业非积极赞助者」。而向秀、山涛、王戎三人则选择与司马氏合作,其中向秀因自然与名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完全「改图失节,弃老庄之自然,尊周孔之名教」,而山涛与王戎两人,前者为司马氏姻亲,后者乃王祥同族,于是便得以存在更多的解释空间。依陈氏所论,诸如山王二人者「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之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宗旨反覆出处变易之弱点,若由此说,则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其最著者也。」
简言之,山涛与王戎两人之世家身份赋予了他们缓解自然与名教之张力的可能。但其侍晋室之政治抉择必然使得他们于调和自然、名教之时有所偏倚,于是彼时众多世家大族皆有信仰的天师道信仰被重新引入了自然概念之中并加以强调,自然之旨便成了「养生遂性」[3]乃至求仙问道以延寿续命。自然之中的曹魏属性既被清除,其与名教之间的冲突亦不再成为一种必然,于是如《后汉记》所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此处名教已然是自然的另一种体现,于是有关自然与名教之关系的清谈也最终失去了其仅存的政治意涵(及与士人身家命运的切身相关),乃是彻底转变成了玄理之论与士人身份的象征。士人也终得以「行事尊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而不显自相矛盾。
四、再造:新自然及华夷之辨
清谈之去政治化并未带来这一思想形式的生命力,反而使其在面临外来冲击之时丧失了抵御能力,如陈氏所述: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夫清谈既与实际生活无关,自难维持发展,而有渐次衰歇之势,何况东晋、刘宋之际天竺佛教大乘玄义先后经道安、慧远之整理,鸠摩罗什师弟之介绍,开震旦思想史从来未有之胜境,实於纷乱之世界,烦闷之心情具指迷救苦之功用,宜乎当时士大夫对於此新学说警服欢迎之不暇。回顾旧日之清谈,实为无味之鸡肋,已陈之刍狗,遂捐弃之而不惜也。 」
而这一思想史的动向更近乎成为了政治史的隐喻:沉迷于清谈之中的士大夫既已放弃了原本清谈中所可能包含的政治讨论,便也无从认清佛与道、胡与华夏之间的关联形式,最终使整个国家在外来冲击之下四分五裂。自然,如本文开篇所述,这一问题绝非士大夫之「庸碌」可解释的;事实上,正如陈氏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所述:「然则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而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中,陈氏又「尝考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家世夙奉天师道者,对於周孔世法,本无冲突之处,故无赞同或反对之问题。」
结合两番论述,不难看出,陈氏认为,大量的天师道信徒都是「家世夙奉」者,因此难以放弃其天师道信仰;而天师道信仰与儒家名教并不冲突(经寇谦之等人改造后反而十分契合),故一直相安无事。可是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意见上的分裂:诸如范缜等希望排佛而保持家传之道法者为一;如梁武帝弃舍其家世相传之天师道,而皈依佛法者为一;如南朝孔稚珪等持调停道佛二家之态度,即不尽弃家世遗传之天师道,但亦兼採外来之释迦教义为一。此种对于佛教态度的分裂所带来的即陈氏所考证的「政治之剧变多出于天师道之阴谋」:如河北清河崔氏乃天师道世家,且对天师道之教义「具有创辟胜解」并借此巩固了自己世家大族之地位,由是则「一方结合寇谦之,『除去三张伪法,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一方利用拓跋涛毁灭佛教」。
佛道之间的冲突向政治领域的延展既是情理之中,却又暗藏着华夷之辨的核心。崔浩之推动北魏前期之汉化以达成对佛教的抑制即可说明:于崔浩而言,华夷之辨不在种族之差,而在文化之异。因此只要拓跋一族愿意接受汉化,崔氏便足以认定其为华夏并借北方世族集团之力辅助北魏,并在北魏推动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以利用拓跋一族对抗有诸多「汉人」信仰的佛教。一言以概之,拓跋一族虽身为他族,但心向华夏,学习华夏之文化,于是是为华夏一族;而佛教徒虽身为「汉人」,却因信仰夷狄之教,最终「堕落」为夷狄。
自然,依此后的历史论,崔浩最终尝试推动的排佛尽管屡次重现,但毫无疑问是失败了。不过历史同样没有垂青如梁武帝等舍道求佛者,而是最终选择了三教合一(或佛道调和)之态势。暂不论这一态势最终的成因,就陈氏的论述看,此一态势中至少蕴含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即佛道之间何以调和。于儒教言,如陈氏所述:「外服儒风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期间并无所冲突。」但基于天师道之道教与外传之佛教绝非同一体系可以容纳,至浅而论,两教所进行的宗教仪式及所信奉的神仙体系、教义即大相径庭,融合再造实为难事。
依陈氏论,在调和佛道方面,「孤明先发」者乃是陶渊明。陈氏以为,陶渊明之家族乃是天师道世家并与崔浩一般排斥佛教[4],但其贡献并不来自于对天师道一脉道教的发展,而是化解了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统一,使得自然与名教重新对立,却又并不以自然作为一种身份政治的工具[5],其反名教「仅限於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非积极地对抗名教[6]。不仅如此,从「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等句中不难看出,陶氏实际上叛离了诸多天师道的义理。在陶氏的论述中,自然不再是天师道中可以被操纵的「旧自然」,而更多携带了「运化」之意味的一种「新自然」,故「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此种新自然的理念同样根植于老庄之道,但对于天师道之道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颠覆:道教于此失去了其强烈的宗教色彩,转而变成了某种与现实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思辨系统,因此与周孔之教更显协和之意。而这种宗教色彩的退却也最终使得佛道得以调和,由此陈氏认为,陶氏之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採(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其「孤明先发」则实乃绝唱,「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概而论之,陶氏之思想既为两晋南北朝之周孔之教、老庄之道并举开辟了一个新的基础,也为华夷之间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范本。结合陈氏所处之世看,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他给予陶渊明如此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