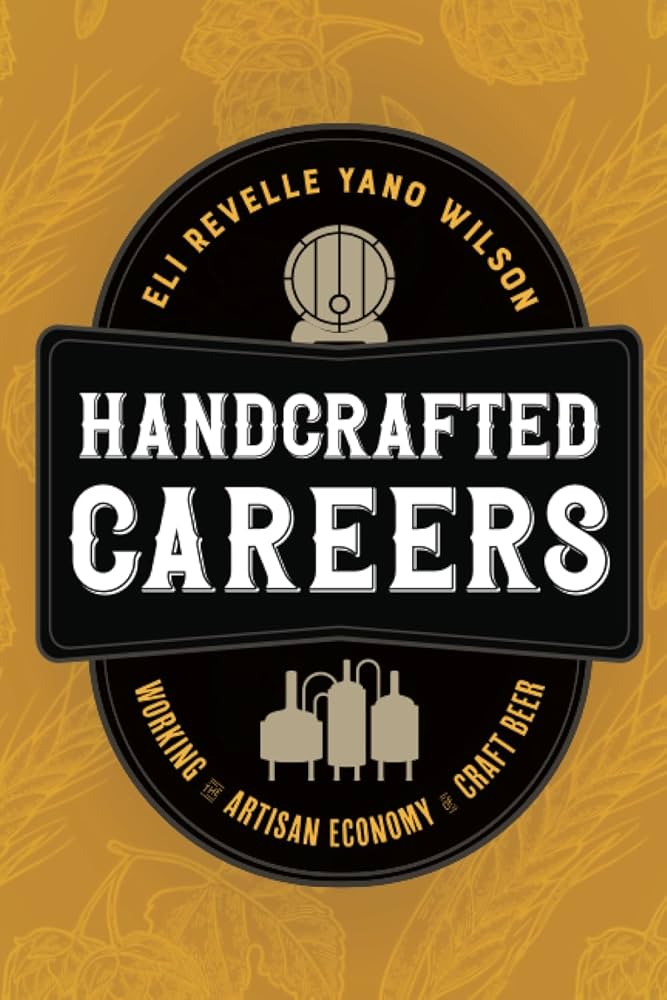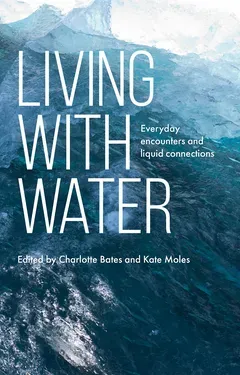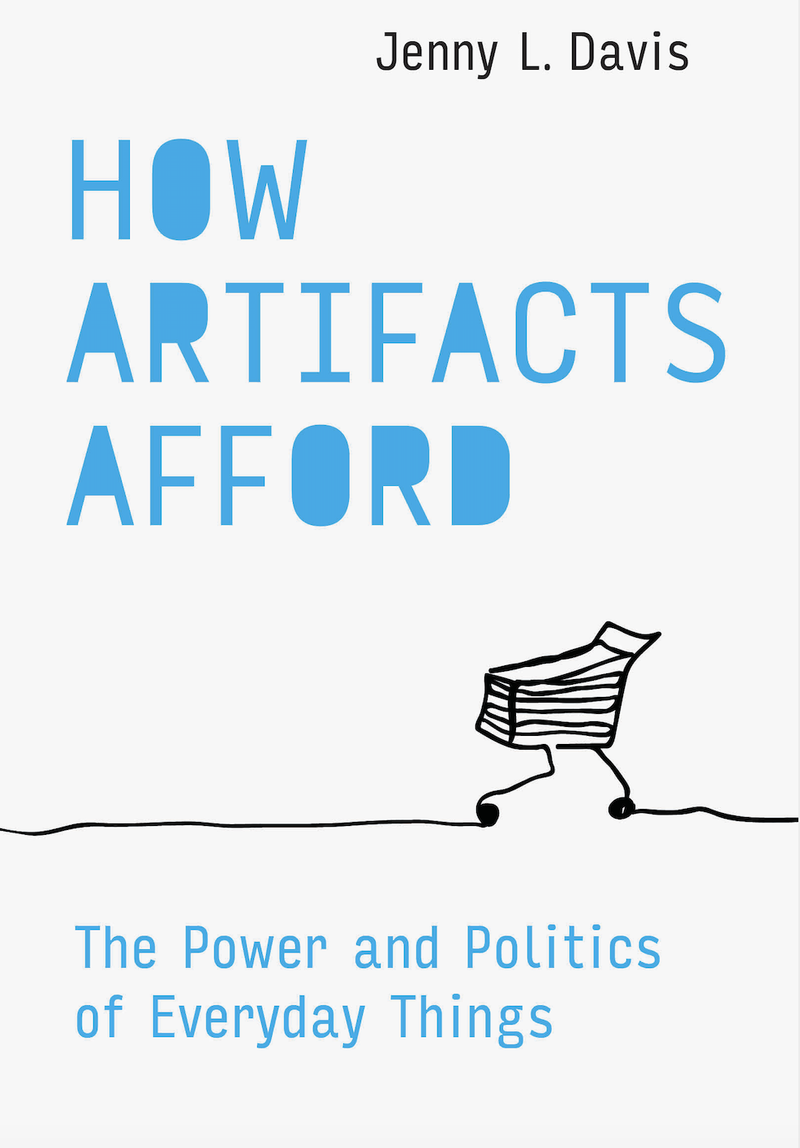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提出,社会学要努力让那些私人的、当下的和公共的、历史的发生关联。我们可以把这种努力理解为对下列三种(或两种)关系的处理: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微观的个人世界和宏观的社会环境;二是历史与当前,即当下的社会结构和历时性的演变;三是公共与私人,或者说社会和政治,即一般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显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或者社会学学生所面对的状况与米尔斯大不相同,无论是宏观的世界环境还是更具体的国家、学科环境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只需要借助这本书去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学术状况,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米尔斯式的研究,或者说怎么样在当下的时代中发挥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意味着必须要成为米尔斯式的人吗?这意味着必须要反对那些米尔斯反对的具体人物吗?例如宏大的帕森斯或抽象经验的拉扎斯菲尔德。
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为了指出米尔斯方法更多的当代可能,我们需要从米尔斯本人的视角出发,更准确的说,要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视角出发,首先考察米尔斯本人是如何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写作中,贯彻了他所说的方法论。很快我们会发现,《社会学的想象力》这部作品本身就是其观念的证明,米尔斯的确尝试将个人生活/生命与更广阔的图景勾连起来,将个人困境、职业困境与整个学科的问题联系起来,而这部作品正是他最重要的尝试。
米尔斯的双面人生
顺风顺水的天才
虽然米尔斯在作品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按照Oakes和Vidich传记中的写法,米尔斯自己一直有要当上社会学大人物、大思想家的雄心壮志,整个学术生涯也堪称顺风顺水,
顶刊发表:早在博士之前,米尔斯就在ASR上发表了题为《逻辑、语言与文化》(Logic, Language and Culture,1939)的文章。博士生早期,他又先后在AJS和ASR上发表了《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后果》(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1940)和《情景行动与动机的词汇》(Situated Action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1940)两篇文章。
顺利求职:不止发表一帆风顺,米尔斯的求职之路也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在一封信件中米尔斯提到,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是主动向他抛去了橄榄枝,希望他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他也是当时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助理教授。
广受认可:进入哥大后没花多长时间,米尔斯出版的三部曲:1948年的《权力新贵》、1951年的《白领》和1956年的《权力精英》很快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项,在多个高校担任访问学者,也作为特别顾问在二战期间为国会工作。
稍加计算就能发现这一切多么惊人:米尔斯在AJS和ASR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才24岁,进入哥大时也才27岁,直到三部曲完成(中间他还写了另外的许多作品)时,米尔斯也才刚刚四十。他几乎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完成了其他学者穷尽一生才能完成的成就。毋庸置疑,这是一位顺风顺水,一路有贵人相助的天才。
学术世界的混蛋
然而,天才米尔斯也相当傲慢,或者说,过于不理解他人的平庸。从读博期间起,一直到生命末期,他一直和周边所有的「傻瓜」(按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更难听)们关系不太好。甚至常常主动挑起战事,用学术上的分歧主导学术社交关系。
米尔斯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博,在评审小组开会评判他的博士学位之前,他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抨击系主任吉兰(John Gillan)的文章,并且将它发表在了AJS上,题为《社会病理学家的职业意识形态》(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
好在他最终还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被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请到了哥大。在最初的一段时间,米尔斯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工作,但因为痛恨那里的研究方法、思路和氛围,他无法完成他的工作,并因此被解雇。此外,米尔斯也一直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攻击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研究,这导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逐渐变得孤立无援。
不止在哥大内部,几乎在整个美国社会学届,米尔斯都和那些曾经欣赏并帮助他的人闹翻了(为数不多的例外是默顿)。四十年代末,米尔斯陆续前往几所学校担任访问学者,其中就包括芝加哥大学。在个人回忆中,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提到米尔斯绝对是个天才。
但这种欣赏同样无法获得等价的回报,米尔斯在给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的信件中提到:自己和休斯以及奥格本(William Ogburn)等人的会面根本就是一场灾难:「我就是不能把这些人当回事。我担心我的态度会显示出来,所以我已经停止了行为」,他认为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异常无聊,自己不如回到纽约。
尤其要注意,从青年开始,米尔斯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争论公共化或是学术化,每次这类事情发生都能决定性地破坏米尔斯和一个人或一群人之间的关系。种种行为叠加起来,就构成了米尔斯在六十年代前给人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象:既是一个学术的天才,也是一个学术世界中的混蛋。
在想象之时
早期文本
Brewer在2004年的论文中详细梳理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前置文本,我们不作过多说明,只在此简单列举:
1943年,在抨击系主任的《社会病理学家的职业意识形态》(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一文中,米尔斯指出,吉兰等人代表了一种社会管理(social administration)的传统,它把社会问题看作社会形式未正常作用的结果,而非某种本身有问题的社会结构的「正常产物」,或者看作是个别受害者的个人缺陷,而不是结构问题。换言之,米尔斯要求区分结构与个人的影响。
1944年,在新杂志 Politics 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The Social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一文,其中提到:社会学家有帮助无权无势者参与公共问题的公共责任。
1953年,米尔斯在《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发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风格》(Two Styl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一文,在其中提到了「宏观」和「分子」两种风格,也就是后面他会着力批判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
1954年,米尔斯在《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发表了《IBM+研究+人文主义=社会学》(IBM Plus Researching Plus Humanism = Sociology)。这是一本通俗刊物。米尔斯在其中抨击了两种学者:一种是渴望获得IBM标志的科学家;一种是从事无关紧要的思索的大理论家。在此之外,米尔斯提出了第三种尚未命名的类型:公共参与,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和离石区是,关注个人生命和社会结构间的联系。
个人境遇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社会学的想象力》整个文本完成之前,米尔斯已经逐步构造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所有的理论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几乎都是他真实生活中的「敌人」或「对手」)。事实上,米尔斯早在1944年年底就在书信中提到,自己需要写一本书专门表达自己对社会学的看法,但这本书却迟迟未能动笔。
这部分源于米尔斯在四十年代时的主要兴趣仍集中于经验性的更实质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米尔斯的私人生活还没有提供充分的动力帮助他完成这份文本。具体来说,我们至少可以发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写作时期的两个关键背景:其一是离开美国;其二是米尔斯面临的严重抨击。
不难想象,类似米尔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数社会学家决裂只是时间问题。1956年,米尔斯出版的《权力精英》并未像之前的作品一样广受好评。在给科塞 (Lewis A. Coser)的信中,米尔斯非常难过地指出,美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对《权力精英》发表的各种意见让他倍受打击。
对于这种抨击,米尔斯的第一反应就是骂回去:他很快写了一篇回应文章(Comment on Criticism)发表在《异议》杂志上,其中认为批评家们对他作品的批评只是在打击他本人,这些「研究领域的政治家」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肯说。
心灰意冷之际,恰好米尔斯被授予富布赖特奖学金,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哥本哈根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借助这一机会,米尔斯离开了生养自己的美国。隔着重洋,米尔斯开始有一些空隙设想自己对美国社会学能作出的更实质性的贡献。他一边开始构思后来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平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姊妹文本,米尔斯在访问期间留下了一份名为《致托瓦里奇的信》(Letters to Tovarich)的手稿,其中是米尔斯试图向一位虚构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解释他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学家的各种情况。显然,这两份文本之间的关系,正好反映了米尔斯所构想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王子复仇
在留欧期间,受职业上的挫折所激励,米尔斯如此高强度的进行写作,经常一天连续写上十多个小时,最终导致和妻子在写作期间分居并最后离婚。在将要完成作品的1957年4月,在给科塞的信件中,米尔斯提到自己即将「回归」(to return)社会学届,并对自己和社会学的未来寄予厚望。
「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我认为是关键的一年。突然有必要做一个大的总结。」米尔斯将自己即将完成的作品和社会学的未来紧密关联在一起(有信件表明米尔斯最初希望将这本书叫做《社会研究》),并逐渐在此过程中放弃了残余的礼貌,开始直指帕森斯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名字。
对米尔斯来说,这是一次社会学世界中的王子复仇记:「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与美国社会学界的这些人做斗争;我忽略了他们,只在做我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一直在幕后搞鬼,现在我宣告开战。我要用我的《社会研究》一书来揭露他们本质上的破产。」
这最为清晰地表明,《社会学的想象力》牢固地镶嵌在米尔斯的生命中,和此前的《权力新贵》《白领》《权力精英》一样,是他用学术的方式理解私人生命历程(或者更准确的说,私人生命困境)的又一次尝试。
想象力的接受史
《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之时在英国和美国都掀起了一阵波浪。尽管两国此时的主流社会学都具有强烈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米尔斯所说的社会管理的特征,主流社会学家给予的也大都是批评意见,但由于脱离了和米尔斯的私人恩怨,英国的评论大多比较温和:
- 古尔德(Julius Gould)将米尔斯称为「特浓咖啡般的激进派」,认为他的观点只对四分之一的人有吸引力;
- 弗莱彻(Ronald Fletcher)认为米尔斯有某种救世主精神,想要将学科拯救出来,但他同样认为米尔斯的评论太过极端,方法论上的建议也并不扎实。
- 温奇(Peter Winch)在195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的理念》(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中认为米尔斯的意见在哲学上非常有力。
相较之下,《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美国的接受要困难许多,如《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和《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就根本没有刊登相关书评,而已有的评论之态度,也与评论者(或所在的派系)同米尔斯的私人关系紧密相关:
- 哥伦比亚大学:米尔斯始终保持忠实的莫顿对此不置可否;拉扎斯菲尔德直接称这本书是「先进的骗术,而不是知识」;曾在哥大就读的李普赛特则认为这本书「对社会学来说非常不重要」。
- 芝加哥大学:布鲁默读过这本书的手稿,但并未发表意见;正如米尔斯忽略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也将米尔斯逐出社会范围,休斯直接称米尔斯的作品是政治哲学而非社会学。
- 其他:由于在冷战问题上和米尔斯观点截然相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直接称这部作品是「庸俗社会学」,米尔斯本人则是「历史的垃圾桶的看守者」。
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仍以李普赛特为例。在与Neil Smelser一起为英国读者撰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社会学的文章中,李普塞特认为米尔斯有意「将自己与社会学兄弟会割裂开来」,使他和他的书「对社会学来说非常不重要」。米尔斯逝世后没多久,这篇文章的美国版本省去了这个脚注,Smelser还特意解释称这一脚注是由李普塞特单独写就,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到1976年,李普塞特本人的说法也发生了变化,他说米尔斯是「在该领域的杰出人物中独树一帜」,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则「对社会学社会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元方法论作品
尽管米尔斯一直在私人生活中与他心目中的愚人们发生冲突,甚至将各种对他的批评都看作狗屎;尽管《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米尔斯在世之时并未收到积极评价,甚至被逐出美国社会学的圣殿,但在米尔斯逝世后,他作品的私人背景很快与作品本身的力量相分离。
在今天的主流评价中,《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学经典中的一员,在主流社会学传统中位居核心。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思路理解这一作品:它不仅是社会学承诺的先知,也是一本自写作之时就践行了其本身的「元方法论作品」,是米尔斯理解私人生活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尝试,是社会学想象力本身的元实践。
正是米尔斯本人无心控制也无力控制的私人生命进程,种种得意、批评、兴奋、苦恼与愤懑,才造就了它的特别。也正是米尔斯本人无从控制也无法控制的社会公共进程,将作品中的私人性逐渐剥离,将一部属于流亡者的复仇宣言,转变为对未来社会学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