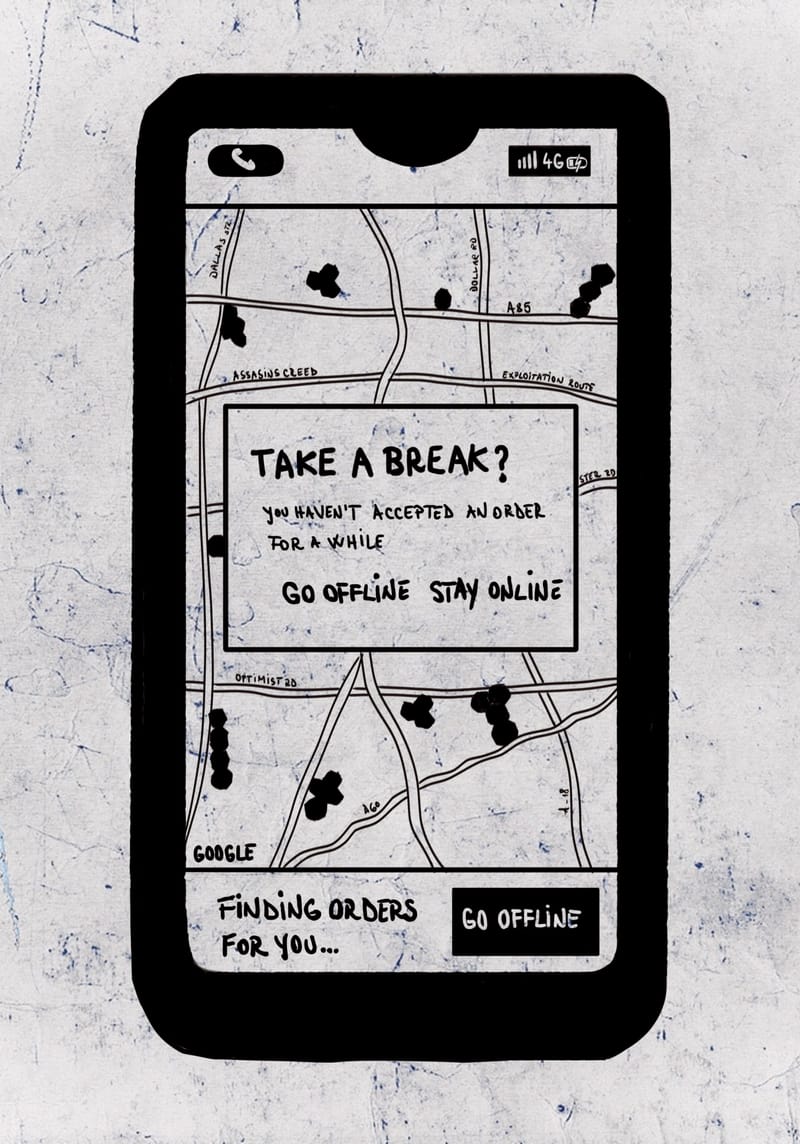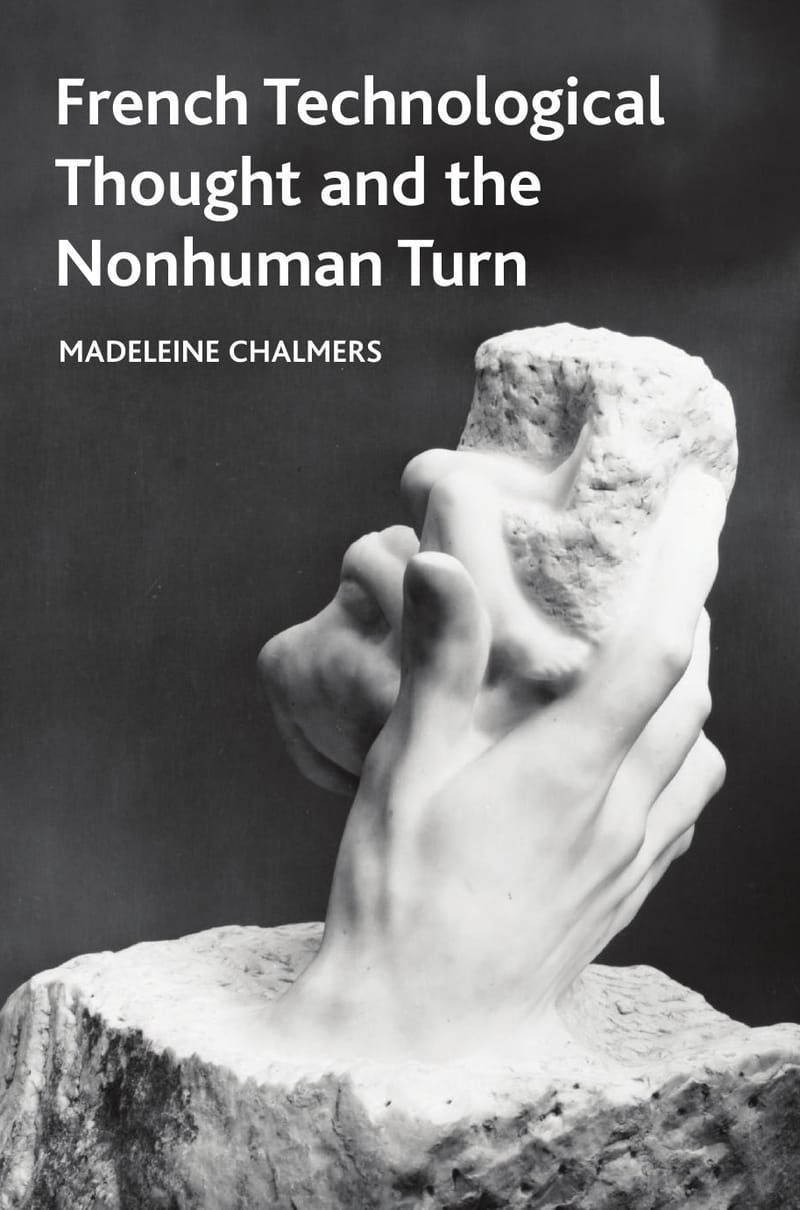翻译自 de la Fuente, Eduardo (2016) Frames, handles and landscapes: Georg Simmel and the aesthetic ecology of things ,原文收录于 Pyyhtinen 编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Georg Simmel 。自用,应有不少翻译错误。
「形式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已偃旗息鼓,前者对视觉、文学和声音对象的内在机制感兴趣,后者则从意识形态、话语和社会的棱镜中观看艺术。正如我在别处所说 (de la Fuente 2007; 2010a; 2010b; 2015),近来的研究重又强调了艺术的「行动性」(agencies)与「示能」(affordances)[1](Gell 1998; Acord and DeNora 2008)、审美实践的物质性(Mukerji 1983)、艺术形式所引发的激情的诸种类(Hennion 2005; Benzecry 2011),甚至不大情愿地承认,对美学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可以从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心理学家那里学到一些东西(Tanner 2004)。如果必须在美学思考的这些趋势中提出一个普遍的特征,那就是渴望「复活」我们所谓的「语境」[2]。语境本身已经成为我们不能想当然或以某种先验的方式假设的东西。我希望从最近的地理学文献中借来位置(place)与空间(space)之间动态且具关系性的特征,我们需要一种能重新唤醒或复活「死去的语境」的思维。(Thrift and Dewsbury 2000)作为一个活着的有机体,语境不仅仅是主体的「活的经验」——这种探究思路强化了物质和感觉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假设。再度激活的语境概念应该是关系的与动态的,同等关注可能性与限制,同样留意「生命」与「形式」。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格奥尔格·齐美尔的思想世界及其关注范围。齐美尔是一位社会学家、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美学家、艺术史学家和日常生活理论家。在此,我希望在齐美尔的思想与生态取向的作者们之间建立对话,后者——诸如乔治·贝特森(Gregory Bateson 1973)、J.J.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 1966; 1979)与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 1993; 2000)——均试图超越语境简化论。于我,这是一次对话而非一致的行动。我将特别说明,在对「画框」「壶柄」和「风景哲学」等主题的思考中,齐美尔 (Simmel 1965a; 1994; 2007) 如何显示出对事物的美学生态学的深刻理解。(关于「美学生态学」的概念,可参 Murphy 2014)如下陈述揭示了齐美尔思想中的生态逻辑:「每一件事物都只是能量和物质不断流动的过渡点,只有从此前的事物中才能得到理解,只有作为整个自然过程的一个要素才具有意义。」(Simmel 1994, 11)我并不是说齐美尔占据了我在此处考虑的生态学美学之先机(尽管他确实直接影响了罗伯特·帕克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方法);「贝特森式」或「英戈尔德式」的阅读也不应取代现有的——如新康德主义或活力论(Vitalist)——对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的解释。 (Frisby 1991; Lash 2005) 我的主张是,齐美尔享有生态思想家们的洞见,即美学感知[3]既不能还原为感知主体的内部机制,也不能还原为外部环境的特性,而是应还原为两者复杂的相互作用。
不过在讨论齐美尔或生态学各自的美学方法之前,我们需要谈谈,为什么审美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些方法值得仔细研究。在一篇题为《被装饰的世界和感觉的纹理》(Ornamented Worlds and Textures of Feeling)的文章中,文化心理学家简·瓦尔斯纳(Jan Valsiner 2008,67)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语境……充斥着高度重复的视觉和听觉模式」。瓦尔斯纳使用了与贝特森和吉布森非常相似的语言,认为「所有生物和环境的遭遇都可以视为模式协调的过程。」(Valsiner 2008, 67)尽管他没有使用「示能」这个术语,但瓦尔斯纳(2008,67)认为,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遭遇采用了「形体(body)模式的遮蔽(camouflage)[4]……基于形体展现的紧密配合……为行走、吮吸、游泳或爬行的表面纹理」等形式。他对装饰现象抱有特别的兴趣,装饰现象似乎早于「为美而美」(beauty for its own – aesthetic-sake)的概念,因此也暗示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创造装饰图案的社会原因」。(Valsiner 2008, 69)模式的语法显而易见,因为它们扩大或淡化了感知场域的内部特征;这反过来控制了观看者或使用者内部情感紧张的增长和升级。在此,「朴素」(plain)和「花哨」(fancy)是相对的,极简主义与「西班牙式的巴洛克风格」(Churriguresco)同样如此。它们与模式生成的整体场域相关。由此出发,瓦尔斯纳进一步假设关于装饰和图案的一般规律:「一个被装饰的世界让体验者驻留『在场域内』——不让他逃脱,同时并不特别要求他对这些图案给予关注或采取目标导向的行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保持社会行动者「在场域内」是我们所说的物的美学生态的核心运作机制之一。
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
在与生态思想传统的关联中定位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这一想法背离了齐美尔的主导形象:一个形式主义者、强调美学自主性的康德主义者或19世纪末「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理念的辩护者。可以说,这些对齐美尔作品的部分解读阻碍了社会学、文化研究和美学批评等领域对他的接受。即使在齐美尔思想的支持者中,也无需走太远就能找到这种主题。因此,《伦勃朗》的翻译者们觉得有义务承认,「从当前许多分析的观点看来,齐美尔坚持美学领域的自主性,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社会、文化或生平背景,这似乎是无可救药地倒退甚至反动。」(Scott and Staubmann, 2005, xvii)同样,美国社会学中齐美尔美学作品的早期拥护者提出,「艺术是独立于生活的现实的论点说明,齐美尔属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法英两国的『为艺术而艺术』学派」。 (David 1973, 324)有趣的是,同一个评论者指出,对齐美尔来说,「世界是由多种相互冲突的组织中心构成的」,不同生命单元经常「试图围绕自己的原则组织同样的材料」。(Davis 1973, 325) 因此,人们在康德哲学中发现的诸领域(艺术、道德和科学)和人的能力(审美、伦理和理性)的分离在齐美尔处并不那么明显。戴维斯(Davis 1973,325)认为,在齐美尔的美学著作中,「世界……看起来更像莱布尼茨的自我实现的单子的世界,甚或是一种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而非康德式的。」 (Davis 1973, 325) 万物有灵论的敏感性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尽管齐美尔对现代性和所有文化的潜在「悲剧」有所保留,他也从未完全认同韦伯式的祛魅理论。
《社会学美学》一文充分展示了戴维斯所说的万物有灵论或泛神论的面向。这篇文章讨论了从美学角度看待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
即使是最低级的、本质上丑陋的现象也可以融入色彩和形式、感觉和经验的语境中,这为它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意义。即便是最普通的、其孤立外表毫无新意且令人反感的产品,当我们深刻地、充满爱意地卷入其中,我们同样能够将它想象为所有事物的最终统一的光线与图像,美与意义正是由此而生……如果我们把美学欣赏的可能性延伸到极点,我们将发现事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世界观变成了美学泛神论。(Simmel 1968, 69)
因此,齐美尔 (1968, 9)并没有把自治作为美学现象的主导原则,而是在论证相反的问题,强调美感来源于所有事物的统一:「从每一点中,整个美,整个世界的意义都将绽放而出。」(Simmel 1968, 69) 此外,根据他的观点,各种非艺术的东西,包括机器、有组织的生产和政治制度,都可以被美学地感知。任何涉及对比、可比性和价值转化能力——即「从枯燥中激发灵感,从原材料中提炼塑造」——都会产生美学理解。统一美学现象的是「我们的感觉与差异联系在一起,这些差异的价值不亚于我们的触觉或温度感知。」 (Simmel 1968, 70)美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可以指向上、下或侧面(例如,它可以指引我们去欣赏某物的「最高」「最低」或最「可比」的情况),但是,最终需要「将世界分为光明和黑暗」,这样才能产生审美刺激和价值。(Simmel 1968, 70)缺少有意义的对比,世界上的所有元素都将「无形式地相互流动」,而「原始的和低级的形式」将不能作为「精致的、明亮的和崇高的事物的支撑和背景」。 (Simmel 1968, 70)
吉布森的美学知觉生态学
正如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在与美感可能被发掘处的关系中,生态学方法是彻底的泛神论。生态学方法也认同齐美尔论文中的观点,即没有对比,世界将是无形式的,并且这种对比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因此,与齐美尔关于光明、黑暗、崇高和世俗的讨论相呼应,吉布森(1979, 130)提出了一个命题:「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陆地动物来说,地面和天空是所有次要结构所依赖的基本结构……我们都已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环境的子结构中。」
世界,作为无止境的美学转换和操控的基础,是生态学方法的中心主题——只有后者将语境称为「环境」,将其中存在的可能性称为「示能」。这一术语应归于吉布森 (1979, 127)的创造,他把「环境的示能」看作「它为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这些示能可以采取「表面」「实质」(substances)「介质」和「物体」[5]等形式,它们包括诸如「地形、遮蔽、水、火、物体、工具、其他动物和人造显现(human display)」等事物。(Gibson 1979, 127) 对吉布森的示能理论来说,表面(surface)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分离了实质与介质(medium)」(例如我房子的墙壁和屋顶通过将我与水分或过多的空气分离来提供舒适)。实质还指导生物体从环境要素中感知到的各种实际行动。物体是平的还是垂直的,凸的还是凹的,刚性/稳定的还是柔性/完全不稳定的,决定了物体是否能「提供支撑」,是「站立式的」还是「下沉式的」,「爬上式的」还是「摔下式」还是「钻入式的」或「撞击式的」(Gibson 1979, 127–8)。
吉布森(1979,137)认识到,随着诸如「工具、器具(utensils)和武器」等物体的开发和「人造显现(manufactured displays)变成图像、图片和文字」,示能的「行为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可即使是技术复杂性和更复杂的媒体也需要环境的支持。发声需要「空气」来传播;没有「光」提供的视知觉,文字与绘画就不再可能;如果没有一系列可被操纵的液体和固体的存在,家具、建筑、公园和桥梁也就不会存在且无法想象。
因此,我们的美感究竟是由环境决定的,还是我们通过观察、感觉和知觉来强加的品质?同大多数生态进路的作家一样,对吉布森来说,这是个荒谬的问题。他认为示能「指向两个方面,环境和观察者……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一个人与世界的互补关系的认知不会分离」(Gibson 1979, 139)。这一论点不仅使主客二元论成为问题,也令人质疑如下观念:美学交流的主要作用是满足心理的或象征性的需求,这种需求已经存在于一个按照自己意愿操纵外部现实的主体中。
贝特森《迈向心智生态学》中的艺术与美学模式
我们习惯于将审美现象视为一种话语的或再现性的结构,以至于我们经常忘记,若没有知觉的唤醒,审美体验是不可能的。在《迈向心智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贝特森发展了心智生态学的主题,它既不是话语的也不是再现性的,贝特森 (1973, 102) 写到:「他们说『每幅图片都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一概括适用于大多数艺术……但我想避免分析『故事』。」作为替代,作者提出了如下方案:
我关心什么是艺术对象中最重要的精神信息,而不是它可能「再现」的东西……「风格就是人本身」(Buffon)。风格、材料、构图、节奏、技巧等东西中隐含着什么?……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狮子可以是老鹰或牛头犬,同时传递着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然而,如果它们是木头做的,它们的信息会有多么不同!.……将感知到的物体或人(或超自然物)转化成木头或油漆的编码(code)是一种关于艺术家及其文化的信息源……我感兴趣的是转化的规则,而不是信息本身。(Bateson 1973, 103)
如果一个审美对象所再现的可能不是艺术的决定性维度,那么《迈向心智生态学的步骤》在人类事务中赋予了艺术何种角色?贝特森认为艺术对抗着内置于意识中的「数量极限」(quantitative limit),即「所有有机体必须满足相当少的意识」的基本事实。由于知觉认识的限制,人类有机体求助于习惯和其他无意识反射。但这些只能提供有限的对世界的知觉。因此,艺术在意识方面的功能是揭示「思维的系统性」。(Bateson 1973, 118)这同等适用于对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史前狩猎图和对梵高的椅子的描述,它们通常被分别解释为「交感的狩猎魔法」和对「艺术家」所见事物的洞察。贝特森 (1973, 117) 认为,艺术帮助心灵认识到意识提升的「潜力」存在,它存在于「你和我之中」。 (Bateson 1973, 117) 毒品、酒精、梦,甚至精神分裂症,都可以把我们从意识的选择性或有限性的本质中释放出来;但只有艺术,通过运用技巧、移情和创造性的跳跃——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有意识的或有目的的选择——起到「矫正」的作用。
简论对称性
有趣的是,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强调了美学感知的生态学方法中一个重要主题:即「对称性」和其他模式在人类及自然事务中的作用。他认为「所有美学主题的起源都可以在对称性发现」,并且「在人类能够把一个想法、意义、和谐带入事物之前,他必须首先对称地形成它们。」(Simmel 1968, 71–2) 应当强调,承认对称的重要性不一定等于将其视为审美秩序的唯一或最高形式。事实上,对称性可能具有一系列社会学和政治含义。齐美尔(1968,72)写到,「对称地组织整个社会的趋势……为所有专制政权所共有」,对称也是「理性主义」的美学伴侣。社会中的理性组织有其自身的「美学吸引力」,从「机器的美学吸引」即可得见,「工厂」和「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更大的尺度上重复这种美」。(Simmel 1968, 74) 对称性具有吸引力,因为对称模式「以最少的智力消耗……为观察中的心灵提供了最大的洞察力」。(Simmel 1968, 75)相比之下,不对称图案的吸引力则明显体现在浪漫主义的美的概念、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概念、「伦勃朗和尼采」的世界观及现代插花艺术中,其中花卉「不再被捆成一捆」,要么「单独地」展示,要么「至多是松散地捆在一起」。(Simmel 1968, 75–6)
重要的是思考以下事实:对称和不对称类型的审美秩序不仅仅是由关联规则或相似性连接起来的范式或世界观。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1969,54)在《视觉思维》中所说,「在空间中见到一个物体意味着在语境中看到它」,同时,「在感知中实际遭遇的关系并不简单」。他的意思是,视知觉的心理学经常错误地从联系的「频率」和「相似性」等方面来看待关联性。对知觉的这种思考模式倾向于假设被感知的事物具有多种离散(discrete)的属性,当它们进入新的或不同的环境时,这些属性基本保持不变。阿恩海姆提出,颜色是一种典型的关系现象,其中位置、北京和密度将提供不同类型的知觉关系。简而言之,关联性与一个场域内的事物的「位置和功能」相关,「只有当整体模式的结构表明必要的关系时,相似性才会发挥其统合力」(Arnheim 1969, 54-55)。因此,一种颜色或形状看起来似乎与其他元素相协调,仅仅是因为这两样东西的配对意味着某种完成。阿恩海姆写到,「对称性只是适切性(fittingness)的一种特殊情况,是通过将事物组合成一个组织良好的整体而获得的相互完成。」
美学感知的生态学方法也随之而来。《迈向心智生态学》中的相当一部分即致力于分析对称性在人类学、生物学和控制论中的作用。贝特森(1973, 385)指出,对称性是一种对看似随机的时间做出非随机推论的方法,这在美学领域尤其重要:「从美学的角度看,一只爪子大过另一只的螃蟹的形状不仅仅是不对称的。它先提出了一个对称规则,随后通过提出更复杂的规则组合巧妙地否定了这个规则。」(Bateson 1973, 385–6)借助战后信息论的语言,贝特森解释说,模式是一种处理源自环境的信息「冗余」的方法:
如果接受到的序列中缺少某些项目,接收者能够比随机状况更成功地猜测缺少的部分,则该信息材料包含「冗余」。事实上,如此使用的「冗余」这一术语就是「模式化」(patterning)的同义词。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材料的这种模式化总是有助于接收者区分信号与噪音。(Bateson 1973, 389)
因此,遮蔽(旨在破坏通讯)通过「打破信号中的模式和规律」或「在噪音中引入相似的模式」来达到其目的。(Bateson 1973, 390) 遮蔽消除了阻挡环境中无关事物的能力。遮蔽和噪音的另一端是「逻辑学家的梦想,即人类应该通过明确的数字信号进行交流」。(Bateson 1973, 388)无歧义的编码有助于降低噪音,但却损失了丰富性与表现力。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在有效利用冗余,吊诡的是,阻止冗余会让我们更关注重要的事情。作者的例子是在说「我爱你」时,语气和非语言沟通变得至关重要。冗余的有效使用存在于「人类的肢体交流、面部表情和语调」中,同样也存在于「艺术、音乐、芭蕾、诗歌等事物」对日常模式化的精细运作中。(Bateson 1973, 388)
将对称模式看得比相似性和同质性多得多的结果是,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及其对立面,被视为事物如何被构造(framed)的函数。对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项目来说,这并非没有影响。可以说,在《脸的美学意义》(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Face)一文中,齐美尔所见最接近于对称与不对称——并非对比的范式或世界观,而是沿生态连续统运动的动态的美学整体性。(Simmel 1965b)尽管人体的其余部分主要通过肢体运动展现,其中的某些部分,如手,似乎有其自身的统一性(例如手指协调一致地运动),但仅在脸部,形式与实质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命运只有同时打击其余每一部分,才能打击其中某一部分。」(Simmel 1965b, 276)
在反思元素间的相互依存性及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所能传达的效果时,齐美尔回到了对称的主题。然而,与「社会学美学」中的处理相反,他在此指出,正是因为「脸由彼此相似的两半组成」,脸才能够获得高度的个性和表现力。(Simmel 1965b, 279)脸是一种美学综合,其中「两部分的本质相似性补充和平衡了个体特征的分离性」。(Simmel 1965b, 279)这反过来又让人类「外表」的一个方面——脸的表面——成为了「灵魂的遮盖与揭露」的焦点。(Simmel 1965b, 281)或者,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说,脸是一个控制论回路,旨在解释心智的系统性。
贝特森与齐美尔论框架化
除了框架(frame)的概念外,或许没有任何隐喻能将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带向艺术史与哲学美学(即让所谓的两种文化重新融合)并相互对话。在《迈向心智生态学》中,根据参观旧金山动物园的经历,题为「玩耍与幻想的理论」的章节观察到,水濑和猴子等哺乳动物能够做出表达性行为,该行为能够区分「玩耍」与实际的「战斗」。(Bateson 1973, 179) 贝特森(1973, 179)由此推断,哺乳动物能够进行一种「元交流」以传递关于交流的「信息」。他认为,将事物视为「游戏」而非「战斗」的能力是一个框架化(framing)的过程,当我们区分笑话与实际陈述、隐喻和字面表达以及梦和现实生活时,也会发生类似的状况。贝特森假设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观察到这样的界限。
框架化的生态学理论与齐美尔的版本相去甚远? 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 1991) 在《界线》(The Fine Line)一书中罕见地综合了贝特森与齐美尔,该书主要关注边界以及社会行动者如何议定边界。泽鲁巴维尔指出,框架化是「周围环境、行为或带有心理支架(brackets)」的活动,框架的意义不在于所框架的「内容」,而在于它「以独特的方式转换内容的意义」。框架允许我们从一种「『风格』或体验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进行心理转换」,如「拳击比赛结束的信号铃」所示或演员进入舞台时「立即变成虚构角色」的样子。(Zerubavel 1991, 11) 至于相框,泽鲁巴维尔(1991, 11)说,相框是为了「提醒观者他们无法闻到照片上的花或吃上面的苹果」。
齐美尔本人即从理论上阐述了相框的重要性:
框架的质性(qualities)表明,正是它们帮助和赋予画面以内在统一性……眼睛强化了图片中心与其四周的关系……事实上,两组压条(mouldings)的包围要比一体成型的框体的包围更能封闭框架……正是这一点有利于艺术作品成为与外部世界相对的孤岛……这就是为什么框架无法通过其结构以提供一个空隙或是一座桥梁——通过它们,世界可以进入或离开图片。(Simmel 1994, 12)
鉴于像泽鲁巴维尔(1999)这样的作者支持「认知社会学」(cognitive sociology),我们或许要问:框架完全是认知的吗?就齐美尔而言,我认为不是。为什么?首先,凝视并不完全是一种认知或去身体化的行动,正如齐美尔(1997,12)所说,「凝视就像身体运动一样,更容易从高处移向低处」,且由于图片平面复制了具身体现的诸方面,「图片的一致性将受到离心分布的影响」。其次,框架所展现的示能类型并不完全与其设计分离。齐美尔(1997,12)认为,正是「框架的设计」使得「凝视的连续流动」成为可能,这将延展到框架相当平庸或「偶然」的面向上,例如「框架两侧接合处」;「与内侧相比」,「框架的外侧」被抬高;以及压条,它通过框定框架,给人以任何「装饰」或「剖析」(profiling)就像「溪流在两岸间」流动的感觉。再次,框架材料的质性。齐美尔表示,木材被认为优于布料、大框架在小图片上看起来更好、自然摄影可以离开框架而快乐地存在这些事情都并不奇怪。
因此,在齐美尔的架构中,框架并不是一个空洞的隐喻,每个事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居/在」[6]在这个世界上。相框提醒我们,「当艺术品挂在我们的房间里时」,它不会「扰乱」我们的日常知觉生态;它就像「世上的一座岛屿,等待着你靠近它,或是从一旁经过它、俯瞰它」。(Simmel 1994, 14)相较之下,每当我们「接触一件家具」,它就持续地、即时地「介入我们的生命,因此并没有自在的权利。」(Simmel 1994, 14) 尽管有着工艺、技巧或设计意图,家具却并不具备吉布森 (1966, 235)所说的「特殊的知觉态度——绘画的态度」。家具和绘画都是对「已有表面的修饰」,但只有绘画是「为被观看的明确目的而创作的」。(Gibson 1966, 224)
然而,图片远不止是被框之物
可我们是否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画作或是更广泛的图像?米切尔(2005,31)的《图像何求》(What Do Pictures Want?)认为艺术品「有其自身的智力或目的性」。他承认,没有一个「现代、理性、世俗的人」会轻易承认照片「被当成人」。(Mitchell 2005, 31)然而,当涉及到将某些对象视为有人格(personhood)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破例」。不仅如此,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母亲的照片并未活着,但他们仍不愿意污损或毁坏它」(Mitchell 2005, 31)。米切尔机敏地说,如果我们可以问那些图片能够回答的问题,它们将包括以下几种愿望[7]:
图片想要值很多钱;它们希望被称赞为美丽;它们希望被许多情人崇拜。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想要某种对观看者(beholder)的掌控。简而言之,绘画所渴望的是与观看者交换位置,在所谓的「美杜莎效应」(the Medusa effect)中刺穿或麻痹观看者。(Mitchell 2005, 35–6)
在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审美对象可能想要什么或渴望什么的问题,被重新理解为因果性(causality)或行动性(agency)的概念。其中一位作者假设这些物体的作用是「吸引、强迫、诱捕和取悦观众」。(Gell 1998, 23) 这是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勒(1998, 16)《艺术与行动性》(Art and Agency)一书的论点,该书将行动性定义为「被视为引发因果关系」的人和物。因此,行动性可以「存在于雕刻的图像中,毋宁说汽车」,因为「在实践中,人们将意图和意识归于像汽车或神的图像这样的物体」。(Gell 1988, 17)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案例研究,它挑战了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的框架学(frame-ology)的一些假设与规范。1914年,为抗议同为活动家的埃米琳· 潘克斯特夫人(Mrs Emmeline Pankhurst)在狱中的死亡,女权主义者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攻击了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画作《镜前的维纳斯》(The Rokeby Venus)。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这幅画经受了一系列深重的、多数呈对角线的创伤,这种创伤很可能出现在被谋杀者的尸体上。盖勒思考了玛丽·理查森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如此鄙视这幅画,以至于她认为这幅画是对同伴之死的愤怒的合法对象。他总结道:「理查森疯狂地损毁图像,以使其死亡与潘克斯特的死亡相对应,这创造了一种图像和人的生命相遇并融合在一起的空间。」(Gell 1998, 64)
艺术史家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 1989,425)也讨论了对《镜前的维纳斯》的攻击,他把他作为「圣像破坏」(iconoclasm)或逆向艺术创作(art-making in reverse)的终极案例:「当圣像破坏者们对图像做出暴力反应,强烈而戏剧性地试图打破对他或她的控制时,我们就开始感受到它的潜力」。与字面的框架学的论点相反,可以说,观察者和美学沉思的对象间的情感和精神空间为偶像崇拜(iconophilia)与偶像恐惧(iconophobia)留下了空间。它模糊了真实的情感空间,并借此在世界上产生了可感知的「情动」(affects)。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就像花瓶不想被打碎那样,画作也不想被砍伤。前者想要保持并包含在人类的行动中。
因此从生态方法来看待图片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种方法需要处理一些显而易见的案例,如艺术通过文字的效果和建制性的框架化(如博物馆作为元框架)成为艺术的事实。它同时也需要解释——正如盖勒所说——为何图片空间是一个将人与图像融合在一起并唤醒激情的空间。然而,融合并不等于无界限。齐美尔(1965b, 267)写道,尽管图片中的「画布和颜料」得自现实中的形状和材料,但由这些形状和材料构造的艺术作品构成了一个「理想的空间,它与现实空间的联系不超过音调对气味的触动」。这个类比十分惊人。与绘画作为现实之窗的陈腐比喻相反,齐美尔提醒我们,事物——包括图片、音调和气味——以各种方式居/在于世界之中。这些居/在模式时或重叠,但总的来说,图片与其他空间配置的关系就像音调与气味的关系。
壶柄之思
图片空间中人与物的融合也具有其他的美学相似性,例如日常审美对象中功能与形式的融合。在《壶柄》中,齐美尔写到,关于像「器具」或「花瓶」这样的物体,最有趣的就是我们拥有「同时属于两个世界」的某种东西。(1965b, 267) 换言之,我们需要有能力去解释,为何某些类型的审美对象注定要被「操纵(handled)、填充和清空、递上,以及被放在这里和哪里」。(Simmel 1965b, 267)对齐美尔(1965b, 267)的沉思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那些由于被「握在手里而被吸引到实际生命运动中」的物体。
如此看来,尽管在目的与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齐美尔作品中对美学自主性的所有讨论都可以被统一。的确,可以说齐美尔的类比思维模式是专为处理事物间的不协调的连接而设计的(de la Fuente 2008)。借此,齐美尔把壶柄与与瓶/壶之间的统一比作「人的手臂,它作为与躯干相同的组织过程的一部分而生长,也调节了整个存在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Simmel 1965b, 269)。《壶柄》指出,壶柄与物体间的关系象征着手在实际、美学和精神生活中的总的作用。正因为具有创造和掌握(grasp)事物的能力,手可以说是「灵魂的工具」,是「生命过程」中存在的能量如何被统一和操纵以达到更高目的的象征。(Simmel 1965b, 269)
回到齐美尔与生态美学思想的重叠处,《壶柄》中借助了大量植物隐喻和(如上所述的)有机隐喻。作者有时似乎依赖一种隐性的理解,即人造物与自然物具有相似的属性。一个拿着碗的人反映了手是如何构成一个「调和的桥梁」,创造、拿住或掌握在其中均有可能,并且将「灵魂的冲动传递到碗中,到其操纵中」——在讨论这一反映如何可能时,齐美尔选择了如下的类比:在这里,人类就像在利用茎与叶之间枝叶的自然流动通道,将自己的冲动注入一个外部物体,从而将它融入自己的生命秩序。(Simmel 1965b, 270)
制造与使用相连,或许是人类更普遍的智力与行动能力将它们结合——这一观念内在勾连起齐美尔《壶柄》中的论述与近来关注手在创造力和物质文化中的重要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压倒性地强调了,物体是人体的延伸,实践活动——包括创造性活动——往往模糊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例如,建筑理论家帕拉斯玛(Juhani Pallasmaa 2009,47-48)的《思考之手》(The Thinking Hand)提出:「在使用斧头、刀鞘或刀时,熟练的使用者不会认为手和工具是不同的、分离的实体;工具已成为手的一部分。」概言之,使用斧头、刀鞘或刀的行为涉及手对材料的巧妙操纵,它既是实用的也是审美的。因此,工具趋向于「通过一个小的改进、使用和拒绝的过程逐渐演变」,它们特殊的美源于许多意料之外的和「绝对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美学观念的物化」。(Pallasmaa 2009, 48)工具之美从「活物般的必然性之愉悦」中散发出来,「的确,它们拥有人手本身的美丽,是所有工具中最完美的。」(Pallasmaa 2009, 48–9)
示能:或如何使「给受虐狂的咖啡壶」有意义
作为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无法接受这一公式,即物体的美与精神意义主要在于其使用。但他显然对事物的示能感兴趣,而示能则主要涉及物的用法。在《日常物的设计》(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中,诺曼 ( Donald Norman2002, 9)指出「示能为事物的运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并举例如下:
一把椅子提供了(「目的是」)支撑,因此可以用来坐……玻璃用来透视和打破。木材通常用于保持坚固、不透明性,或支撑和雕刻。平坦、可渗透、光滑的表面用于书写……旋钮用于转动。插槽用来插入东西。球用来投掷或弹跳……因果性的心理学(a psychology of causality)正是……在我们使用日常事物时起作用。(Norman, 2002: 9)
齐美尔(1997, 214) 的论述——「椅子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坐在椅子上,杯子则是为了让人们把它装满酒,然后拿在手里」——在此有了强烈的回响。《壶柄》和《日常物的设计》之间存在有趣的对比:如果说齐美尔有时将审美性与实用性区分得太开,那么诺曼则认为好的设计和实用性相辅相成。对后者来说,美学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有的东西有效而有的无效,一个物体的成功设计基于一些基本考量,比如你是否需要说明书以正确使用某一物体,以及对用户来说它的功能是否即时可见。因此,《日常物的设计》的核心兴趣是确定「糟糕的设计是否会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问题」,以及常见或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否有「简单的、能够恰当地利用示能和自然约束的解决方案」。(Norman 2002, 87) 对作者来说,一个反复出现的(负面)案例是法国艺术家雅克·卡雷尔曼(Jacques Carelman)的《给受虐狂的咖啡壶》(Coffeepots for Masochists),它的壶柄与壶口在同一侧,所以基本不可用。这一物体出现在《日常的设计》的封面上,随后在《情感设计》(Emotional Design)的「序言」中再次出现。 (Norman 2002; 2005)
给受虐狂的咖啡壶或可为齐美尔(1965,272)作证,他声称:「壶柄和壶口(必须)在视觉上相互对应,作为瓶/壶外径的端点,它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这样壶柄和壶口才能「扮演」被分配的角色。关于这一物体的问题也支持了齐美尔的主张,即一个瓶/壶,无论多么美观,都不同于一件艺术品,因为它包含了与实际行动的世界的联系。有趣的是,诺曼(2002,2)将卡雷尔曼的咖啡壶置于艺术领域,说明它提供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日常物的例子,这些日常物故意不可用、大胆放肆或有其他不明智之处」。《情感设计》意在向我们展示认知和情感如何在设计中相互交织,其中给受虐狂的咖啡壶被描绘成一个「完全反思性」的,而非本能的(visceral)或行为性的物体。尽管「它没有用……可它讲述了一个多么美妙的故事。」(Norman, 2005, 6)
然而诺曼对示能的理解是否足够生态学,或是否对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感兴趣?如《日常物的设计》,这样的书既谈论「事物的感知与实际属性」,同时又奇怪地分割用户和语境。(Norman 2002, 9)在某些方面,诺曼的模型更多基于「认知科学」而非生态学,人类的意识及其与前在的物质属性间的关系成为了「不变量」(invariant)。在《环境的知觉》(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中,英戈尔德(2000, 19)批评了那些解释关系性情景的尝试,其中「有机体在进入环境前被基因型所指定」,同时「环境在有机体到达前被指定为一组物理约束」。或许可以说,并非所有关于示能的讨论都能如我们所愿,同等地解构主客二元论或再度激活语境。
齐美尔与物的当代理论
因此,尽管齐美尔有时似乎认为实用品不如纯粹的艺术品,但当谈到壶柄和壶口如何贯穿日常经验的能量与流动时,在许多方面上,他比诺曼这样的作者更具说服力。物体和手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感知、分类和心理支架(mental bracketing)的问题;这是由所谓「壶柄」介导(mediate)的能量流组成的关系。壶柄引导物体和世界之间的连结之流(flow of connectivity),正如「壶口」倒转了这一连结的方向性:「有了壶柄,世界就靠近了瓶/壶;有了壶口,瓶/壶就延展到了世界。只有通过壶柄接受流,并通过开口再次产出流,瓶/壶才能完全融入人类目的论。」(Simmel 1965b, 272)在此,目的论似乎是指通过实际活动的约束与引导的内在对比形式来塑造行动。壶柄与壶口用于提供瓶/壶和(包括实际活动的世界在内的)外部世界间的接触点。只有壶柄「向心地」执行这一生态功能,壶口才能「离心」地执行这一功能。(Simmel 1965b, 272) 物体被组织起来使它们能「通过这种特殊的能力抓住我们全部的能量,并将这些能量募集(enlist)到其服务之中。」(Simmel 1965b, 274)这种募集既是感官的也是灵魂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通过感官的敏感性,物质(corporeal)通达我们的灵魂;通过意志的神经支配(innervations),灵魂延展到物质世界。」(Simmel 1965b, 272)
这完全令人信服吗?在《齐美尔与社会》(Simmel and the Social)中 ,Olli Pyyhtinen (2010,38)注意到,齐美尔如何提供了一种社会关系模型,这一模型「不断揭示着对象之间的联系」,同时又支持如下观点:「被固定在一个位置的人将无法追踪关系」。Pyyhtinen赞扬了齐美尔「各种关于文化的文章」——大概包括本文迄今为止所涉及的各种反思(例如「社会学美学」「脸的美学意义」「画框」「壶柄」)——对「主客体间动态性」的关注,它们并未将客体框定为「本质化的与外在的,并简单将其因果规律强加于我们」。(Pyyhtinen 2010, 112)但他也提到了上文讨论的部分主题,他认为,从当代物质文化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角度来看,齐美尔将我们所说的「实践」(practical)视作当然,其分析也假设了「社会」与「物质」之间的「不对称」:
齐美尔认为物体的使用(use)不言自明……他只在应用艺术(与其他实用艺术品)和艺术作品间形成对比的情况下处理使用的问题……(许多)文章忽略了物体铭刻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方式以及养护、操弄(handle)它们所需要的能量、时间、技巧与注意力……应当更仔细地考虑物体如何为我们的行动创造潜力,提高我们的能力,影响我们,使我们就位、移动,阐明我们的理性、政治、激情和意志,参与我们的世界创造等等。于齐美尔,人类与非人类的能力之间总存在着先验的不对称:只有人类主体被赋予了生成和组织世界的能力。(Pyyhtinen 2010,129–30)
难以否认,齐美尔维持了人类与物质世界间的二元构造。同时也应承认,尽管齐美尔对日常物体与经历的微观分析抱有兴趣,但他却很少对它们的使用进行民族志或其他经验图绘。在许多方面,齐美尔是微观世界的形而上学家,他看到了普遍的与超历史的主题与人类灵魂本质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试图为微观化(micrologize) ——如果我能用这么糟糕的说法——而微观化的人。然而,在我们考虑如何再度激活语境的语境下,我认为有必要从对画框与壶柄等事物的讨论转向齐美尔对风景的思考。《风景哲学》的译者称「这篇文章让齐美尔将一条迄今为止未被充分揭示的线索引入其作品中,那就是在不断创造、维持和变革它们的无处不在的生命(Life)[8]中,人类和自然的统一性(oneness)。」(Bleicher 2007, 20)
风景作为物质语境之沉浸
风景或能迫使思考者更充分地超越二元论,这并不完全令人惊讶。正如怀利所言(John Wylie 2007, 2–11),风景迫使我们直面被社会性地调和的「张力」,如「靠近/疏远」「观察/栖居」「眼睛/土地」与最根本的「自然/文化」。或许正如一位颇具生态意识的人类学家所言,风景「并非你或任何人所能看到的一个整体,而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一个注意的介入(attentive involvement)……的语境”。(Ingold 2000, 207)我要补充的是,齐美尔在其关于风景的文章中试图解释的正是这种「注意的介入」的「语境」;同时,相比他对其他物质实体的思考,此文所提出的论点也使齐美尔的思想更明确地导向生态或场/网络。
《风景哲学》的出发点是,要想让某样东西构成风景,「我们的意识必须获得一种整体性、统一性,超越其组成要素,不局限于它们的特殊性或由它们构成的机械性。」(Simmel 2007, 21) 给予「树木和水道、草地和玉米地、山丘和房屋,以及光和云的无数变化」以不同程度的注意是不够的;风景需要一个「边界」或一种「存在方式」,以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视野」(field of vision)。(Simmel 2007, 21) 但是,齐美尔补充到(2007,21),视野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因为风景所要求的「自为」(for-itself)状态和「统一」的类型「可能是光学的、美学的或以情绪为中心的。」为解释工作中「感觉-知觉统一」(Sense-perceptual unity)的类型,齐美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类比:「那些只一瞥就能看到的,或出现在我们片刻的视野内的,无论如何都不是风景……正如一批依次排列的书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图书馆』。」(Simmel 2007, 23)
然而,感觉-知觉统一并不意味着——如近来一些风景理论所称——要施加一种特定的精神框架或凝视类型。齐美尔(2007,24)批评了经验主义生命的观点,即将风景看作一系列「已经存在」的「心灵造物」,当我们的生命从一段「前进」到另一段时,「基于欲望或目标」,这些段落被「融入」到这些预先存在的造物中。相反,风景就像艺术——它是艺术的「原型」——因为它「从生命中涌现……生命也包含了它所必要的构造性能量。」(Simmel 2007, 25) 可我们打娘胎里(embryonically)就带着的东西不一定会导向相同的结果。例如,齐美尔指出,与人像相比,风景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们带着一定的客观性来看待风景,可若是看一个人,这便不大容易实现……在后一状况下,我们为主观的干扰(如同情或反感这样的感受)所限……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仍未审视,对我们来说,如果这个人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因素,他将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对风景的感知中,我们可以将其各部分这样那样地组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重点可以各种方式转移,中心与边界的关系亦如此。人类的构型(human figuration)……则自行决定一切。它从自身之中,围绕其中心完成了一个综合,从而无歧义地界分出自己。(Simmel 2007,26)
但是,正如通过绘制人像来捕捉生命的方式殊异,理解自然统一性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风景的感官场域不同于「因果思维的学者、具有宗教式情绪的自然崇拜者、一个目的论导向的土地耕种者或战争战略家」心中的自然概念。(Simmel 2007, 26)风景模式整合了自然中的各种元素和线索,其独特之处在于最无形的品质:风景的心境(mood)。事实上,齐美尔(2007,27)提出,心境在风景中的中心地位(反之亦然)解决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是我们对一个物体的统一感知(unitary perception),抑或随之产生的感受(feeling)位居第一。」他断言风景和心境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两者都既是「因」又是「果」;风景的感知行为也没有「内在」或「外在」,因为场所的情绪与精神氛围是「风景固有的品质」。(Simmel 2007,27)此处的心境不仅仅指风景是「快乐的还是严肃的,壮烈的还是单调的,激动的还是忧郁的」(这些都是情感性的「抽象」)。相反,心境是一种「融合」(fusion),灵魂的「统一力量」能在风景之中,也在穿越风景时形成。(Simmel 2007,28)
风景的美学感知:对比齐美尔与生态学的方法
齐美尔的《风景哲学》值得与风景的感知与美学的生态学理论相对比。吉布森关于物理环境提供的各种感知示能的生态学理论理所当然地影响了风景研究领域。(Thompson 2013)必须要说,这种生态方法的本质相当「土」(earthy)或「接地」(terrestrial)。吉布森将风景看作「支撑面」,为不同的动作(如攀爬、坠落、躲藏、行走、跑步、游泳和碰撞)提供支撑;它的「实质」也提供了「营养」「制造」与「操作」的示能。诸物体附着和分离于地球之上,在它们下面的地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拥有了「家具」并且被「胡乱填满」(cluttered)。(Gibson, 1979,132)风景也提供了「开口」与「障碍」,如林中空地或无法通过的悬崖面;视知觉通过这些表面来提供「具有(afford)隐蔽能力之处,躲藏之处」。(Gibson 1979, 135) 吉布森的风景包含不变量(如若我背向它,风景将保持不变)[9],但是表面的相互作用及媒介与表面互动的方式(如凸凹起伏的山丘和山谷捕捉和重定向光线的方式)提供了一种作为语境的、关系的动态的风景的感觉(sense)。最后,在可以从不同的有利位置(vantage points)看到或「扫描」的地方(place),风景不是静止的(如乡村的航拍与普通照片或绘画有根本性的不同);随着有机体的移动,「地理环境」提供了新的「与所有运动路径的集合相应」的感知观点。(吉布森1966,206) 概言之,感知即移动(mobile),因为眼睛、头部或整体方向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氛围感(sense of ambience);还因为走动产生了新的看、听、触、嗅环境的有利位置。
英戈尔德已富有成效地拓展了吉布森的生态学方法,涉及风景及在其中行走的活动。英戈尔德表明,风景是一种「质性的和异质的」现象:想象你「站在户外,(风景)就是你周围所见:一个轮廓分明、纹理丰富的表面,各式物体充斥其上——生命与非生命,自然的与人造的。」(Ingold 1993, 154) 与齐美尔(2007,21)的观点——「要想有风景,我们的意识必须获得一种整体性……超越其组成要素」——相呼应,英戈尔德(1993,154)写道,「风景是一个充盈的(plenum)空间」,其中「没有可填补的空洞」。两位作者的相似性也可以从以下问题中看出,即风景如何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同时又与一系列其他事物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对它的意识:
风景中的一个位置,无论是在观念层面或是在物质层面,都不会与整体「隔绝」。相反,每一个位置都在与整体的某个特定的联结(nexus)上体现了(embodied)整体,在此方面,不同位置也各有殊异。一个位置的特点在于它给那些在此消耗时光的人所提供的体验——构成特定氛围的景象、声音和气味。而这些又反过来取决于栖居者们所从事的活动的类别。正是……在居/在(dwelling)的问题中,每个位置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Ingold, 1993: 155)
制图者的空间概念是静态的,它测量固定点之间的距离;相对的,居/在的视角从「实际旅行是通过一片风景进行的」这一前提出发,地方的意义不再「附着」(attached to)于而是「聚集于」(gathered from)我们所栖居的世界。(Ingold 1993, 155) 英戈尔德特别感兴趣的一种居/在形式是步行或以「脚」在风景中穿行。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已假设,正是平坦坚硬的表面支撑着行走;然而,平坦、不坚硬的表面(溪流或湖泊)却不能提供必要的「立足点」,高度差(vertical drops)要么是运动的障碍,要么是造成碰撞和伤害之处。我们再次面对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表面不是同质的。但是英戈尔德也对风景和步行如何通过(被感知和被栖居的)环境的纹理、节奏和时间性相互交织抱有兴趣。《行走的方式》(Ways of Walking)的导论描述了风景与人类移动的共同决定性:「栖居者所行走的表面……既不平坦也不同质……它们具有纹理。」(Ingold and Vergunst 2008, 7)他们认为砾石、鹅卵石或沥青等材料其上似乎不会留下人类行走的痕迹,但长此以往,或许会因为这些因素而腐蚀或开裂;相对的,像雪、沙和泥这样的表面「柔软且有延展性,容易被压印」,但这种「印痕往往相对短暂」。(Ingold and Vergunst 2008, 8) 因此,人类运动在地球表面留下的痕迹有「暂时存在与持续存在等种类,这与它们所属的风景的动力学(dynamics)密切相关」。(Ingold and Vergunst 2008, 8)这种思想对风景研究的启发是,位置本身是以时间和实际行动为标志的。或者,正如蒂利(Tilley 2004, 25)在《石头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Stone)中所说,要理解风景及其对行动者的塑造力,就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一个把身体、运动和位置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视角」。
齐美尔对风景的思考符合这种整体理解的要求吗?当他说「无论是自然还是艺术,作为整全存在的我们都与风景有关」时,他似乎是在朝此迈进。(Simmel 2007, 29)但是,借用英戈尔德和当代风景研究的语汇,齐美尔(2007,29)似乎把一种居/在模式置于其他模式之上,宣称「只有艺术家才看到并创造『风景』,其余的人则更多与(风景的)物质性相连,且仍倾向于只注意到这个或那个独立的部分。」这不仅与文章的其他部分相矛盾——例如,心境和风景的不可分割性是一种普遍体验而非特定的艺术体验——还抛出了一个观点,即风景的物质性仅仅是某种将被变换(to be transformed)的东西,而非某种永远不会真正放弃其结构效果或示能的事物。此外,我们可能会问,齐美尔将如何看待像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螺旋码头》(Spiral Jetty)这样的艺术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大地本身,就地形、大气、地质而言,是一个强大的、原始的和活跃的行动者(agent),共同建造着艺术品」(Wylie 2007, 143)。在此,我们或许要转向他的《废墟》(The Ruin),以获得一种更严肃地看待风景的物质性的表述。齐美尔(1965c, 260) 认为一幅「油漆颗粒从其上脱落的画」与一座建筑的废墟有着不同的秩序(order),在建筑的废墟中,「仍存活的艺术」和正在涌现的自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整体,一个典型的统一」。因此,我们或许会说,在废墟的案例中,(以类似于《螺旋码头》的方式)产生美学效果的东西是「同样的力量,它既通过风化、侵蚀、断层和植被的生长为一座山赋形,也在残垣断壁上发挥作用。」(Simmel 1965b, 260) 或者,借生态学术语,我们可以说,为建筑的建造和设计提供支持的土地,也可能为建造提供了材料,在这篇土地上,废墟与风景正在融合:「废墟不间断地使其自身进入周围的风景中,像树和石头般与风景一通生长——而宫殿、别墅或农家住宅,即使它们完全符合风景的心境,也总是源于另一种事物的秩序」。(Simmel 1965c, 263)齐美尔认为,一座未经毁灭的建筑,只有「在事后回想中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
结语:齐美尔与社会美学的未来
本文的主要假设是,社会科学迫切需要一个处理语境现象的新概念,而美学,在其各种表现形式中,或许能提供帮助。用「新艺术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art)(de la Fuente 2007)的话来说,艺术和社会、美学和社会生活不是分离的实体。它们协力生产彼此,使得语境概念成为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社会美学(Socio-Aesthetics),能够解释特定审美经验和过程中产生的整体感。我隐含的论点是,齐美尔对日常的和高妙的(rarefied)审美对象的多重思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从而将语境视为事物的美学生态。生态学的概念在此被松散地使用,如果你喜欢,它就是一个把握装置(holding device),用来思考感知和环境及它们如何融合。可以说,在齐美尔的例子中,生态关系可采取画框、壶柄和风景等形式,其中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统一以及自组织过程和生命之流动间的关系。画框提醒我们,我们努力无边界地欣赏事物;但是这种边界也维护了事物。壶柄要求我们把握、移动、放下并一般性地使用物品;但(至少在齐美尔看来)从未完全解决对美的向往与对实用性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相比之下,风景是一种语境,在其中,将生命合一的动态张力与过程得以充分展现。我们在风景上留下印记,但它也塑造我们,滋养我们,鼓励我们以多种方式居/在。风景也邀请我们更整体地体验事物,它既不如画框那样分割事物,也不像壶柄那般将事物一并握住,但却——就像给受虐狂的咖啡壶的案例——如此依赖设计和制造在事物的生态中所扮演的角色。齐美尔(2007,29)认为,风景提醒我们「感知和感受」是同一「行为」(act)的两个方面,只在「随后的反思中」,美学体验「才被分割开来」。
为什么事物的美学生态所提供的精神和经验整体性的类型很重要?在《迈向心智生态学》一书中,贝特森 (1973,101)提出,艺术是生活本身的竞争性能量的一种调和:「我认为艺术是人类对恩惠(grace)的追逐的一部分;他时而因部分的成功欣喜若狂,时而对失败感到愤怒和痛苦。」正如Efraim Podoksik(2012,10)所指出的,在其美学主题的几篇文章中,齐美尔提到了一种状况,它「将激起以下感受,即自然和心智间的对立已变得无效」;同时,他还将「无法解释的统一感」描述为一种「恩惠」或「不当的礼物」(undeserved gift)。无论是用「恩惠」「不当的礼物」「融合」「流」还是「超越」来形容,神秘的统一感——在存在的非美学维度中是可能的,但并不常见——都表明了,事物的美学生态为何重要。
目前对于Affordance一词存在着多种翻译,基于吉布森对主客二元论的反对及affordance作为一种「人物间交互」的属性,我未采用较为通行的「可供性」一词,因为它暗示了affordance是一种物的属性,并强化了物的客体性;同时,诺曼《设计心理学》中译本中采用的「示能」(物展示其所能)虽展现了人、物平等沟通的状态,但却不如钟蔚文(2006)等人所采用的「机缘」来得巧妙贴切。由于本文最初翻译时统一采用了「示能」的译法,因此将不再做出修改,仅提出「机缘」的译法以供思辨。 ↩︎
本文所用的context一词大多数是带有物质含义的「环境」,为与enviroment区分,后文统一译为「语境」。 ↩︎
本文中的perception绝大部分翻译为「感知」,sensation则译为「感觉」,两者对比出现时perception译为「知觉」。此外,feel或feeling统一翻译为「感受」。 ↩︎
本文中的camouflage既有「遮蔽」也有「伪装」之意,考虑到吉布森处的「遮蔽边缘现象」是一个专门术语,以下统一翻译为「遮蔽」。 ↩︎
本文中的object有客体与物体两种译法,前者同时也包含「对象」之意,后者则强调物质性。相对的,所有的thing都被翻译成了「事物」以表示非物质性的虚指。 ↩︎
本文中的dwell同时有「居住」与「存在」之意,为与being及inhabit相区分,后文所有的dewell将统一译为「居/在」。 ↩︎
原文注:本书标题后来改为What do Pictures Want? ↩︎
后文所有Life都将加粗以区别于life。Soul亦如此。 ↩︎
作者在这里使用的不变量的意思与吉布森原意有所偏离,背向风景时风景所呈现出来的不变量属于心理结构,这恰恰是吉布森的知觉生态学要排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