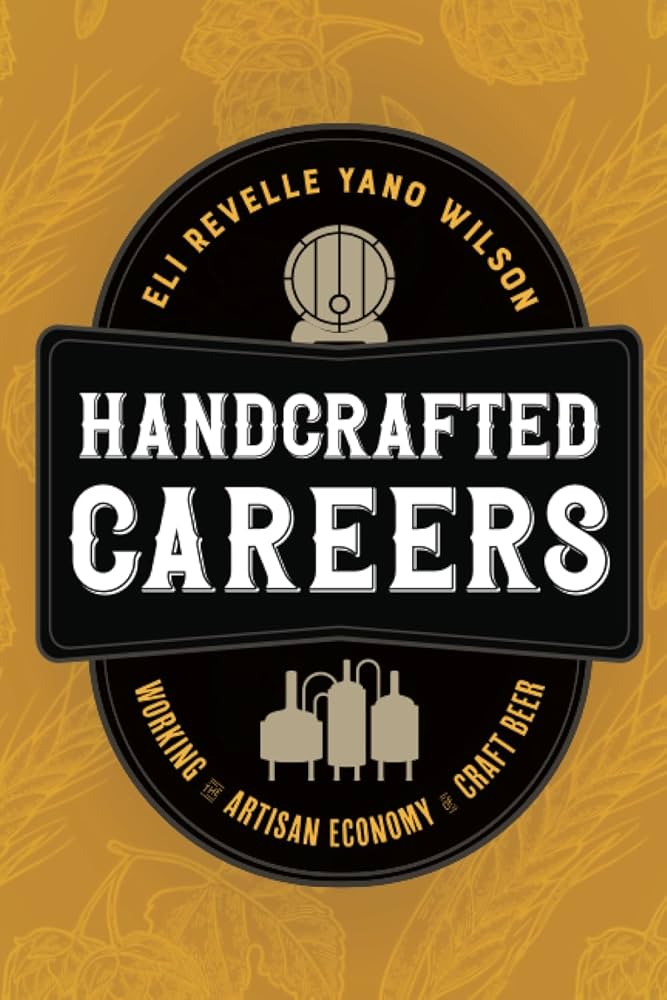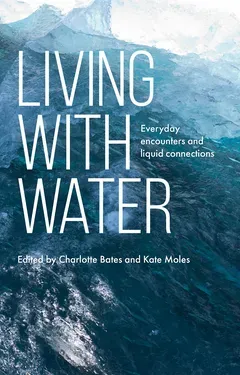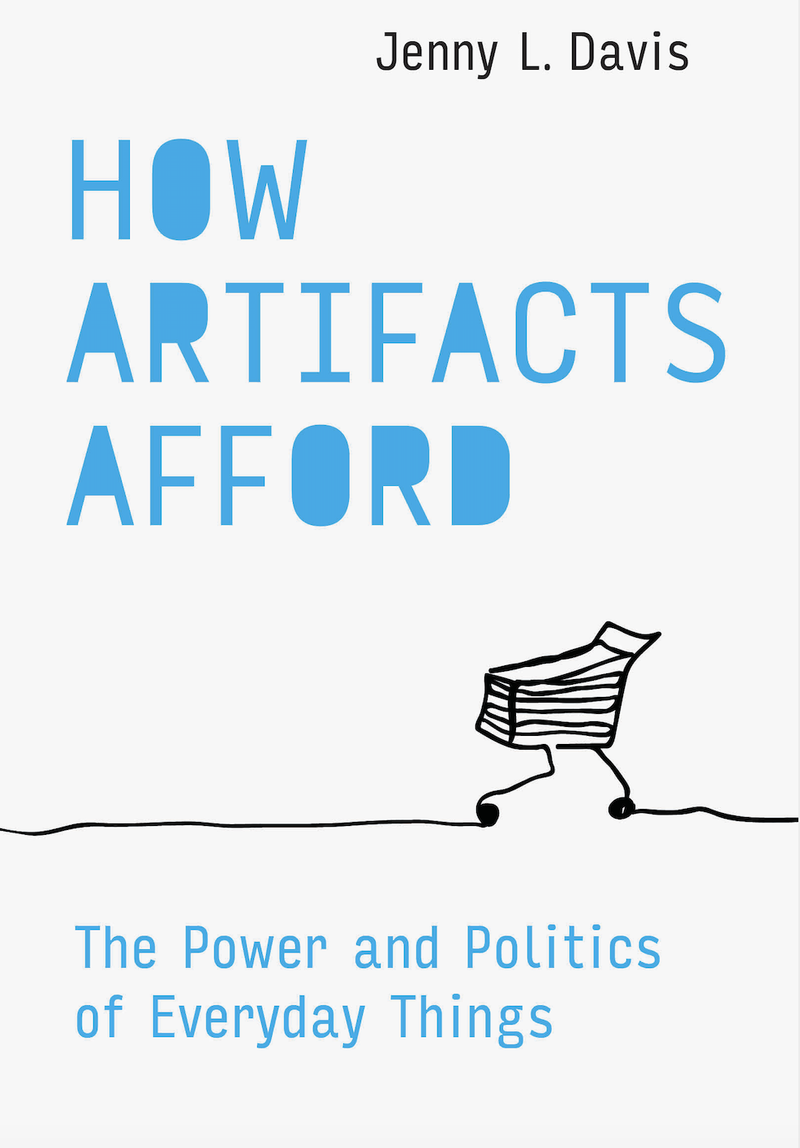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建立关于美的合理的、历史的理论,与唯一的、绝对的美的理论相对立」,为了寻找这种新的美,现代生活的画家必须投入到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在各式风俗速写中,在对人群的描摹中寻找「现代性」的踪影。[1]
若将波德莱尔的论断稍加拓展,「现代性」将不再只是那些转瞬即逝的生活碎片,而是意味着一种吊诡,一种「现代」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拒斥。就此而言,涂尔干同齐美尔或许可与莫奈、塞尚一并划入现代生活的画家之列,区别不过是他们更明确地表达了自我观察与自我拒斥背后的抽象社会,其阴郁的色调更接近现代主义,而非印象主义画家。
事实上,尽管一般研究认为涂尔干与齐美尔的理路取向相去甚远以致难以生成对比的空间,但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却都是对现代性的描绘与理解,甚至研究的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将自己研究的关键面向之一描述为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得到证明——即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都有可能发现它的意义的总体性」,由此,对现代的观察必然构成一种破碎与永恒的悖论,正是在那些瞬间的断片中,我们看到了意义的总体性,也看到了美。而在《自杀论》与《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失范」理解为一种现代的反常状态,一种社会在个体身上的缺席与危机,可是恰恰是这种反常最为有力的塑造了社会的实在性。如康吉翰(Canguilhem)所说,「健康就是器官处在沉默中的生命,因此,生物学角度上的常态/规范就是通过破坏揭示的」,正是在失范中,也只有在失范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常态与规范的社会。
仿照波德莱尔的说法,「分析的二重性是人性二重性的必然后果」[2],尽管涂尔干的社会是「对个体而言普遍的……一种特殊的主体」,而齐美尔的社会则是人际互动构成的网络或是一种结晶,但他们的分析核心中都包含了对人性二重性的洞察。在涂尔干处,现代人性的二重性体现为圣俗之分,体现为一种「越是个人便越是社会」的悖论,而失范便是个体人性中缺少了神圣的、社会的部分的制约,从而难以建构起自身;而在齐美尔处,人性的二重则关乎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现代的破碎与现代分化的来源之一便是由于客观文化不断膨胀,人们不得不进入更加狭小的空间中去以实现对部分客观文化的完全掌握,即便如此那些客体仍旧会不断凌驾于人性之上,使得个体迷失在现代体验之中。
若将涂尔干的人性二重性观点看作社会在个人身上的缺席,那么齐美尔的观点恰好说明了这种缺席的缘由。涂尔干并非没有意识到,分工与分化带来的团结正是以对完整的世界的遮蔽为代价的,多重的多样的世界自此形成,原初的整全的世界再也无法返回。其实正如齐美尔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无论现代如何延展自身,无论现代社会如何有多么破碎、多么冰冷)中寻找到总体性的美,涂尔干也完全可以在每一种社会状况中找到「常态」,可是涂尔干终究没有那么「现代」,他并不愿意彻底接受现代所塑造出的那种可能性,那种将世界的敞开与对界限的找寻合而为一的可能性。也不妨这么说,在涂尔干的「失范」所揭示的可能性与其对规范/限制的找寻之间,恰恰呈现出了现代最重要的特质:一种对现代自身的抗拒。
由于那种二重性,现代人必须通过对自身的限制才能塑造完整的自我,可是多重的多样的世界的存在恰恰意味着现代自我必须在对单一的「现实」的不断超越中才能发现自身。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表面上区分了利己、利他与自杀三种自杀类型,实际却只有两类,其中利己与利他都是一种形态学类型的讨论,而失范涉及的则是自杀的实质理论的讨论。不仅如此,两类不同的讨论其实也运用了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在分析前一类时,涂尔干是通过分析与宗教、年龄、地区等因素的相关的自杀率回到分析开头提出的「利己」或「利他」的分类,证明分类的可靠;在分析后一类时,涂尔干则是循着某种发生学的逻辑,更着重强调现代对人的限制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人的影响。在这里,由于社会/规范/限制的缺席,「无限的欲望像一种道德差别的标志每天都显示出来,而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产生」[3],实际上,无论是集体欢腾与社会缺席都是一种超越界限的「反常」状态,正是在这种反常中,也必须在这种反常中,社会才得以呈现自身,区别只是前者呈现为一种生理,而后者却被理解为一种病理。
这种超越/界限的辩证法同样可以在齐美尔处见到,「事实上,人方方面面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行为,都处在两个界限之间,这一点决定了人在这世上的定位」[4]。与涂尔干一样,齐美尔相信,如果缺少了界限,此世的生命/存在将是贫乏的,难以体会的。然而齐美尔所说的生命/存在却始终包含着一种「反常」性,生命/存在究其根本是超越的、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在集体欢腾与社会缺席中,而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断追求着对界限的超越,「这些形式为创造性的生命构筑了框架,不过,创造性的生命很快又会超越这些形式」[5]。
由此可见,尽管齐美尔与涂尔干都强调着界限,但由于齐美尔的社会是一个网络、一种结晶,他的社会便不得不外在于人,构成一种主客二元结构,界限的意义也必须在这一结构中得到说明,呈现为一种在「渴望超越」与「恐惧意义缺失」之间的摇摆;相对的,涂尔干则部分超越了这种二分,将外部界限的内化理解为现代个体自我创制的关键路径,「人是有限的存在……若他不去牵制自己的本性,他就无法超越方方面面的限度……人的本性无法成其自身,除非他受到纪律的约束」——社会虽然是一种实在的集体意识,却始终「活在」每个个体心中,社会决定论与道德个人主义之间虽然充满张力,却无根本性的冲突,反而是成就个人的必要条件。
不妨这么理解两者的分歧,对于齐美尔所描述的「漫游者(flaneur)」来说,世界存在一种先在的紧张,漫游恰恰与界限相冲突,现代的进展于是必然是破碎的断片式的文化悲剧;而涂尔干则并未重点关注那些作为异常的漫游者,处于其理论核心的形象是「社会人」,它们的世界是先定和谐的,只是因为作为一种异常状态的现代,其世界才患上了疾病,而这些疾病终究能找到治愈的方式(无论是通过法团还是教育),我们能找到某种新的规范状态。
某种意义上,当卢卡奇将齐美尔理解为「没有塞尚的莫奈」时,他正是与涂尔干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坚定地相信着齐美尔的研究不会是现代的最终状态,只要学者努力地观察、剖析现代,就能最终找到一种新的古典主义状态,它能展现现代生活下意义的总体性,能够终结现代的失范。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即便真的存在一个属于齐美尔的「塞尚」,他也不会达成一种新的古典主义,而只能是开启了更为破碎与流动的现代的潮流。面对无法遏制的现代,表面上齐美尔与涂尔干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拯救现代生活的方式,然而无论是齐美尔在断片中寻找整体性的美,还是涂尔干寻求一种新的常规状态(集体意识)以达成社会整合,其最终借助的都是一种神圣的超越凡俗的绝对性力量,而现代越是破碎,越是陷入吊诡,我们便越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拯救我们的日常。
不妨以波德莱尔作结,在《恶之花》中,面对形成之中的现代生活,波德莱尔问到:「你究竟来自深渊,还是降自星空?」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 现代生活的画家[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商务印书馆, 2011.
[3]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4]埃米尔, 迪尔凯姆, 冯韵文. 自杀论: 社会学研究[M]. 商务印书馆, 1996.
[5]西美尔, 刁承俊. 生命直观: 先验论四章[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6]西美尔. 货币哲学[M].. 华夏出版社, 2002.
[7]西美尔, 曹卫东. 现代人与宗教[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麦克·甘恩. 法国社会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9]渠敬东. 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M]..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0]基思·特斯特.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