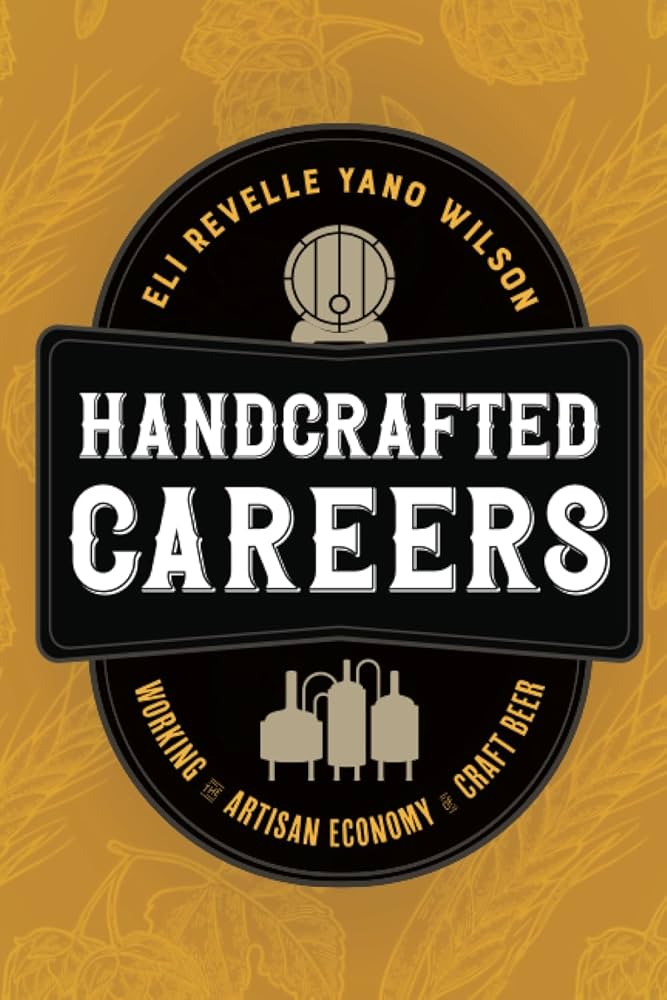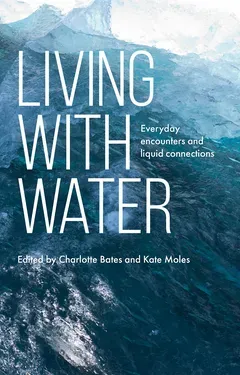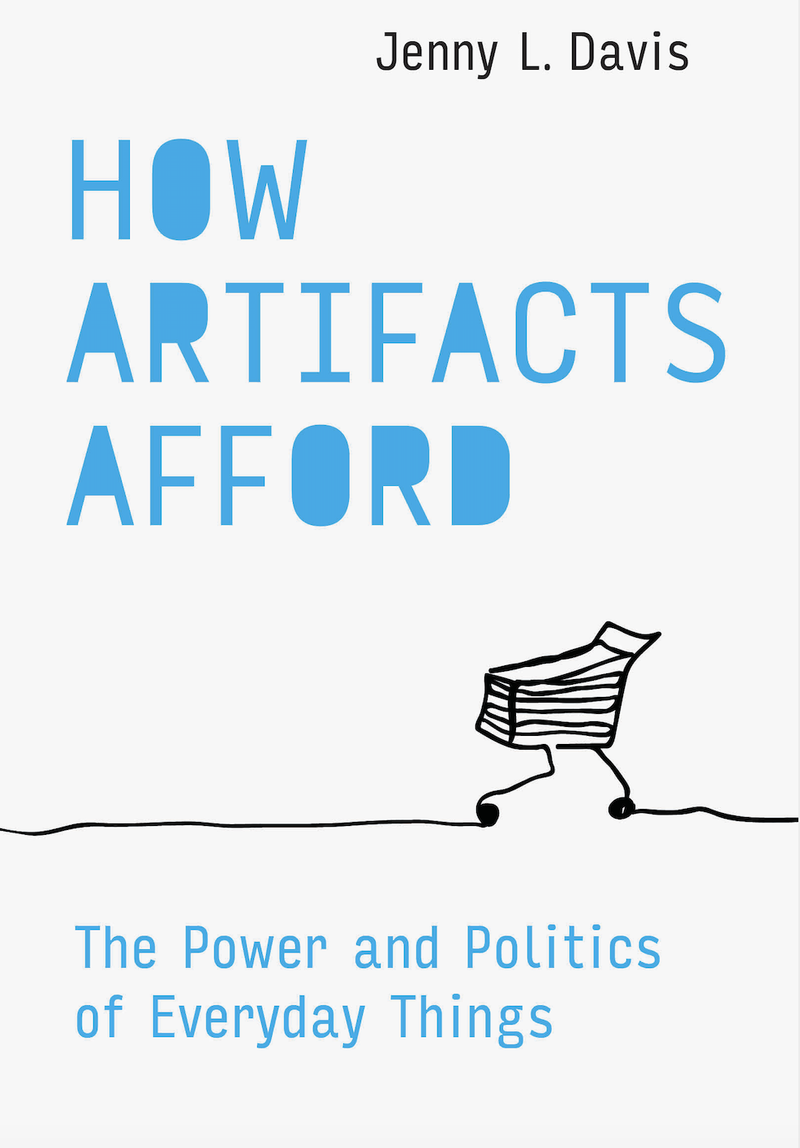在中文语境下,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是一位研究六十年代反文化与技术之关系的传播学研究者。的确,除去其早期进路类似集体记忆研究的《战斗的回声:美国记忆中的越南战争》一书外,特纳的后两本著作《数字乌托邦》与《民主环境》都与反文化有关,尤其是《数字乌托邦》一书,几乎被看作理解硅谷文化的密钥。然而在其研究脉络的最末端,《民主环境》却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面貌。
在序言中,特纳称《民主环境》所书写的是《数字乌托邦》一书的前史,两本书整体上完成了一个二级跳:首先将九十年代的硅谷文化溯源到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随后再将反文化运动与四十年代的反纳粹思潮相关联。可不同于《数字乌托邦》传记式地追溯,《民主环境》是一本议题优先的作品——特纳在后记中提到是先有了该书的整体想法,再去档案馆搜寻可用的史料——这也就意味着,《民主环境》必然容纳了更多「旁枝」,它呈现出的关联是理论性的,而不是经验性或生命历程性的。再没有KK或是斯图尔特・布兰德那样延续三十年的风云人物,特纳耗费三百页后抓住的只是一条不大稳当的草灰蛇线。
那么,特纳找到的六十年代反文化之父,所谓的四十年代生成的「民主环境」(Democratic Surround)究竟是什么?简单说,特纳找到的是一种与「魔弹论」相对的传播模式。魔弹论强调传播本身的效力,仿佛只要传播者向受众开枪,受众就一定会「中弹」。在最浅显的意义上,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魔弹论是对新兴的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施以理解的努力,同时也隐含着对大众媒介本身的批判。可究其本质,魔弹论图景中可怖的并非魔弹的效力(相当程度上,现代智术师或修辞专家的技艺),而是被魔弹整合起来的大众。换言之,魔弹论反映的是对大众社会的恐惧,或者说对勒庞的「乌合之众」观念的延续。
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刚过)的时点上,希特勒上台后的纳粹德国(自然也包括此后的墨索里尼与转向军国主义的日本)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恐慌。评论家们在寻求解释时既找到了传统的「文化论」(即强调德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具有生成纳粹的某些要素),也将魔弹论作为潜在的解释之一。如前所述,采取魔弹论解释的必然结果就是将被「魔弹」击中的大众当作无知的失去理性并任人摆布的人偶,当三十年代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们观察德国,再回望国内日益兴起的群众运动(其中确有相当部分纳粹倾向的活动且声势不小),自然生出惧意,希望寻找一种办法保卫国民健全、民主的心理。
对发起「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运动的语言学家们(如柯日布斯基或早川一会)来说,保卫国民心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会民众正确使用语言,使语言中无外延的抽象概念与真实相分离,以保障国民的「精神卫生」(mental hygiene)。可以说,「普通语义学」已经展现出了与魔弹论的关键分野:魔弹论的本质是一种内容论,这就是说,掌握了宣传机器(大众媒介)的人可以宣传自己想宣传的内容,从而达到特定的效果及目的。在此模式下,掌权者既可以用媒介行善,亦可作恶。然而普通语义学关注的是语言(也即传播)的结构,也就是说,无论被说出的(被传播的)内容为何,只要说/传播的方式内在是有缺陷的,无论它所传播的内容多么积极向上,它都会带来问题。
三十年代的阿多诺亦与普通语义学进路相似。在讨论爵士乐的文章中,阿多诺分析了爵士乐与古典乐结构上的差异,并认为爵士乐(流行音乐)是一种主动的召唤/唤起,而古典乐则需要听众主动、自由地理解,爵士乐(流行音乐)的实质是将整体的社会结构复制为一种听觉体验并灌注到听众的脑中,这意味着所有人正在享用的流行文化(通过大众媒介传递的所有咨询)均可能造成心理的侵害,且这种侵害不来源于传播的内容(语义),而在于传播(或被传播物)的结构。与阿多诺相对,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并不认为问题源于传播的发出面,而在于接受者——现代工业社会的原子化倾向与大萧条塑造了极其脆弱的、与维持其身份的地方性世界脱钩的个体,这种个体天然容易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并被整合进群体之中。
概言之,无论持何种立场,站在三十年代的节点上,大多数论者均认可,大众媒介倾向于强化极权主义倾向。因此问题便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如何防御极权主义可能的侵蚀。在此,特纳找到了两批人马:一批是心理学的人格研究,一批是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两边都希望通过构造一种属于美国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同时也就证明美国与德国在民主基础上的差异——来保卫美国的民主。两者汇聚在「国民士气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中,该委员会致力于提升美国的士气,以应对战争(尤其是所谓纳粹心理战)的冲击。
暂不论罗斯福总统最后是否采用了该委员会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答案是没有),「国民士气委员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区分出美国的士气与纳粹的士气。这就是说,要为提升士气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或者说方式,避免在提升士气的同时将人民转变为纳粹般盲从的人偶。自然存在许多区分的方式,例如宣称极权主义的士气是情感和理性解藕的,而民主的士气则是两者结合的;又如宣称极权主义的士气仅仅生产了「服从」,却未能带来「内在力量」,而民主的士气必须带来一种内在力量。
然而在这种区分的进展中,心理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分别发展出了对「人格」理论的需要。在心理学一方,阿尔伯特(Gordon Allport)与勒温(Lewin)等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对士气的区分本质上是对人格(Personality)的区分,换言之,民主士气的关键是它建起在对一种整全的开放的民主人格的依赖之上。由此,对士气的渴求变成了对整全的自我人格,以及对有助于促进这种自我发展的宣传战略和一整套传播策略的渴求。这就进一步要求背离静态的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发展出一种动态的人格理论。在文化人类学一方,类似米德(Margaret Mead)与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人类学者将文化人类学的基本预设——个人行动特征(Character)与社会文化构造的关联性——带入了人格领域,从而颠倒了纳粹对国民性的静态区分,从经验上证明了人格的动态可变。
类似的,在心理学一面,无论是勒温对紧张(tension)的强调还是弗洛姆(Fromm)对社会、家庭、个人三元结构的说明,甚至包括苏利文(Stack Sullivan)对弗洛伊德的背叛,或是在人类学一面,米德和贝特森对萨摩耶与太平洋海岛的研究及鲁思(Ruth Benedict)对南美洲的研究——整个三十年代的心理学与人类学带来了新的人格理论的转向,可将其共识总结为:文化塑造人格,传播则整合了社会、人格与文化。
新的人格理论使得纳粹解释的文化论几近破产。可人格与文化间的互动可能意味着国家责任的变迁:国家若能(或者说无论如何都必将)通过大众媒介塑造文化并进一步塑造国民之人格,那国家便需要确定以何种方式达成此目标。换言之,美国是否应当模仿纳粹的手段(戈培尔式的宣传)以对抗纳粹本身带来的心理恶果?答案是否定的,并不仅仅因为这一手段存在道德上的问题,更因为这一手段无法达到其目的——事实上,在阿尔伯特以降的人格理论中,人格的塑造不仅被互动的内容所影响,同样被互动的模式所影响,换言之,以宣传对抗宣传是不可能的,国家所要所要创造的并非特定的文化内容,而是一种结构性条件,以同时维持其公民的个性和他们为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力。
正是在此思潮下,米德与贝特森在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博物馆及出版物(Balinese Character)中进行特纳所谓的「民主环绕」实验,及通过构建的多图像、多文本的环境,为观众提供民主的选择的可能(可以说,可选择性与环绕性是这些探索的两个关键特征,因此这些探索也就是一种早期游戏实践),使之在此过程中锻炼感知能力,形成对自动机式的工具主义传播模式的抗拒。在此背景下,从德国赴美的包豪斯艺术家们(格罗皮乌斯、莫霍利-纳吉或拜耳)为「民主环绕」提供了实质性的技术支持。
早在德绍时期,包豪斯的训练便强调学生的选择权及对学生感知的训练,以期将学生训练成一个心理上完整融汇的个体。赴美后,包豪斯艺术家们也自然地接受了人格理论的转向,并试图将自己的技术灌注到民主环境之中。特纳集中分析了莫霍利-纳吉的「新视觉」(New Vision)与拜耳的「拓展视域」(Extended Field of Vision)两种思路:前者的核心是创造一种与透视法(「依靠体量的错觉关系构建假想的空间」)相对的、真实且自由的空间及与之相适的运动的(因而加入了时间的)新视觉,这一视觉内在是整合的、开放的[1];后者则希望创造一个观众可以走入的、环绕的立体的空间,在空间中并置不同的符号、图像、材料(这正是包豪斯教学的关键),让观众自由选择。特纳详细分析了二战时期的「胜利之路」(Road to Victory)展览如何体现了莫霍利与拜耳的思路,由于理论上未有推进,在此不作赘述。需强调的是,莫霍利与拜耳思路的实质都是将政治问题转制为美学、心理或进一步的感知问题:在此,展览本身的物理环境提供了一个在外部世界与内部心理状态之间来回移动并相互结合的场所。
类似的,特纳也分析了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也即知名的《4'33”》的作者——自三十年代以来的音乐实践。在二战前,凯奇致力于发掘一种拓展的声域,即一种能容纳更多声音可能的音乐(例如「特调钢琴」就体现了这一观念),这种音乐首先体现为对现代精神的治疗:从这些噪音中,现代人学会了如何聆听包围着自己的声音,聆听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之美。然而自二战开始后,尽管写出了类似《第三号回忆中的景色》(Imaginary Landscape No. 3)这样模拟战争的音乐,凯奇仍希望进一步解决音乐中的能动性(agency)问题。这就是说,观众是否能「主动地听」。
为此,凯奇找到的关键方式是从和声转向节奏:如果说和声是一种被动的感召,那么节奏就打开了声音之中的空间,在此空间内可以容纳各种可能的音调组合,最终塑造出一种敞开的、非牵引性的声音系统。此外,凯奇又通过构造随机系统(所谓偶然音乐,例如用易经与公式构造系统)进一步消除了作品中的人为因素,解放了表演者。这些探索最终在例如《Theater Piece》或《4’33”》这样的作品中构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却仍带有秩序的分布式声音系统:在前者中凯奇将不同的表演者(如诗朗诵者、舞者、钢琴家)并置,使之各行其事;在后者中,凯奇只设定了一个总的模式,表演者与观众可以自由决定作品的长度、小节或其他形式特征。只在这种特别的系统中,凯奇所期望的音乐的整合性(在随机世界中整合心理与人格)才得以实现。不仅如此,凯奇的创作同时构成了一种管理、整合社会的新可能与模式,社会与人格(内在心理)真正意义上有了同构的可能——尽管行动的空间仍在专家设定的界限之内。
莫霍利-纳吉、拜耳与凯奇等人发展出的媒介技术延续到了战后的展览中。战后的展览采取了类似的方式以应对截然不同的问题:从战场回来的士兵要如何融入到人群之中?问题不仅在于士兵本人的精神创伤,关键在于战争似乎诱发了人心底潜在的非理性(换言之,去欧洲作战的士兵感染了纳粹的精神病毒),因此国家需要用各种方式清除这些病毒。在此,国家所要面对的情况已与二战时发生了变化。若说战时的展览(对媒介技术的运用)尚可算是一种防御(免疫构造),那么战后的心理工作已成为一种主动的疗治或攻击。防御与疗治/攻击的区别在于,免疫构造的建立本身可以是自由的,而疗治/攻击意味着将错误/病毒清除出躯体,换言之,国家此时必须面临解放与控制的两难——保障精神自由与民主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用国家的强力控制(显然一种不自由的方式)来清除病毒的危害。
就此而言,二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使控制与自由融合为一。诸如教育学家的莱曼·布赖森(Lyman Bryson)和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这样的知识分子为这种融合提供了科学上的可能。维纳的控制论设想了一个初步的机器自主性问题,即若所有的人类都是一种能够理解信息并根据其行动的反馈(同样是一种信息)来调整行动并寻求新的反馈的机器,那么人类就拥有了一种超越法西斯主义下绝对被动的受众的能力。
必须承认,特纳在此的论述是相当成问题的,当然可以将控制论中带有协作性或初步理解力的机器(人的一种模型)看作对法西斯主义绝对受众的超越,然而这种自动机模式带来的自由同样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一模式相比魔弹论中的人类模型的主要进步只在于这种自动机「主动感知」的能力,不幸的是,只要放弃控制论对信息的执着,这种感知的能力甚至不需强调便可拥有。[2]抛开这一点,可以认为,维纳在控制论里构造了一种初步的控制与自由的结合体,其中控制由系统自身的运作保障,自由则源于主体(自动机)的主动感知能力——这就是说,两者都是由一种疗治性的「信息系统」的内在机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维纳模式的实质是将传播结构的管理者从极权主义与大众媒介转向似是中立的科学。然而此处仍存在着凯奇以降的问题:谁来保障科学(也就是系统)的中立?生活在专家或科学家划定的系统就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自由了吗?
对于控制论内在的问题(我相信冯内古特的早期作品《自动钢琴》非常完美地呈现了这一问题,而近年翻拍的《西部世界》电视剧同样响应了自动钢琴的母题),特纳在此提到了里斯曼(Riesman)对「系统」的焦虑,显然,这种焦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进入主流文化中。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最火热的展览仍是整合性的,1955年的《人类之家》(The Family of Man)。包括《人类之家》在内,五十年代的艺术界(尤其是和政府关系良好的MOMA)一直在寻求对大众精神上的疗治。特纳特别注意到达米科(D’Amico)对莫霍利-纳吉与杜威的艺术教学法的融合,及这种作为治疗的艺术教学实践从战时(回国士兵为主)向战后(儿童为主)的转变。
达米科在艺术教学中强调创造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延续了包豪斯(同样也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理念,即创造力可以疗治心灵的创伤,帮助心理整合;另一方面却也是对「复制/摹仿」观念的拒绝。在二十世纪初有不同学者(奥尔巴赫、塔尔德等)人从不同角度考虑了「复制/摹仿」的观念,这些讨论一方面延续了柏拉图以降的实在论序列(天上的形式是最高的,现实是对形式的摹仿,文本/绘画是对现实的摹仿),另一方面也将摹仿作为一种社会内在的机制。换言之,这些讨论为魔弹论提供了两方面的基础并使两者互为前提合而为一:其一是传播本身的机制,其二是传播内容的伪劣。因此,达米科一方面要求孩子抛开摹仿自行创造,一方面也打破了艺术教学中的权力关系,将师长都抛在一旁,让孩子自行其事,试图教会孩子自行构造民主的群体。
同样的思路也延续到了《民主之家》中。尽管在技术上显得乏善可陈,仍是莫霍利-纳吉与拜耳的延展,然而倍受批评的《民主之家》(可参考《表征的重负》第六章对《民主之家》采用的一些摄影作品的批评,这些摄影作品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构造,这种构造无法被特纳所强调的自由布置所取消)却通过这些技术为观众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即便作为一种选择的自由是极度不充分的。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之家》的展览被识别为一种与宣传不相关的「非叙事」,而是一种蒙太奇式的、视觉驱动的展览。除去开头一段必经之路外,观众可以在展览中四处走动,照片悬挂在展览的不同位置,不同高度(头顶、平行、脚部),来自全球的不同家庭将观众包围起来。观众也可以在出口处的一个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脸和全球的其他人并置在一起。
特纳此处的设想似乎接近本雅明对历史重压的拼贴逃逸,可无论如何,强调视觉对文本的优势——不同于六十年代后支配性的「景观社会论」对视觉的贬抑——显然是一种特别的想法,也值得进一步考察。可无论如何,系统的悖论仍旧存在,即便《人类之家》树立了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宽容的社会,这个社会中可被选择的一系列选项也已被当权者设置好了,社会中的群体只能「自由」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些选择,而不可能作出选择之外的举动。这种特殊的自由模式不仅主导着《人类之家》这样的国内展览,同样延续到了战后美国的国际性努力中。
在战后的重建浪潮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内的新兴国际组织都希望在人的思想中构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用多元文化消除个人心理与环境之间的张力(换言之,用文化叛逃或多元归属的可能消除张力),构筑出一个无紧张的地球村。然而这一地球村的梦想却仍旧笼罩在专制与民主的两类人格区分,以及对拯救专制人格(也就是时刻等待大众媒介召询的人格)的迫切需要之中。在此,以USIA(美国信息服务处)为代表的机构倾向于将每一次传播活动都视作一次潜在的对分裂世界(尤其是与民主人格对立的专制人格)的治疗[3]。这种治疗关注的不仅仅是症状,而是病因——换言之,不是要宣传对立的内容,而是要提供包容性的替代性的传播框架。
在此,作为治疗的传播与战后经济引擎的启动相结合,政治选择可能转换为一种经济选择,换言之,自由似乎就意味着在不同商品间的选择,而不同商品只不过是一种「设计」上的微妙差异。设计成了一种心理和政治理想的出口,「人民资本主义」成了流行术语(Potter 甚至将社会-人格的互动拓展为物质/商品-社会-人格的互动链,还通过考察早期西部的拓殖史,说明「丰饶」对民主的作用),这种可能则在世博会及各种外出展览上(在不同国家的相互注视中)得以实现。特纳详尽的描述了各类技术在展览上的使用(如迪士尼的环绕电影与苏联线性展览的对比),同样,因为缺少理论推进,此处概不赘述,唯一值得提起的是主导莫斯科展览的设计师是莫霍利-纳吉的学生(一位相信图像能整合心灵的设计师)以及美国会有意识地收集数据以改进展览的内容。
在全书最后一章,特纳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推进,即带入了反文化的视野。五十年代末之后,卡普罗(Kaprow)在凯奇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被称为「Happenning」的表演形式(可参考凯奇众声喧哗的舞台),然而区别在于:《人类之家》与凯奇只控制了环境,并未控制环境内的行动,卡普罗则控制了表演者和观看者,试图完全包围使之放弃理性。事实上,以卡普罗的Happening为代表的方式似乎可以称为一种「意识政治」(perceptual politics),它是对系统本身的一种反抗方式,即采用系统自身建构所依赖的媒介技术(如音乐、图像或灯光)以关闭理性,唤醒无意识。这一政治路径显然与彼时兴起的直接行动的新左派相分离。可它也找到了新的盟友:麦克卢汉。
相当程度上,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即信息」可被看作三十年代强调传播结构理论的发展的极致形态,即传播的结构(媒介)本身就是被传播的事物。在其早期作品(《机器新娘》《古登堡星系》)中,通过拆分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麦克卢汉使人们有可能恢复大众媒体的力量,从法西斯主义的记忆中汲取狂喜的经历,并将其转变为重建民主的工具。换言之,麦克卢汉提供了一种正当地使用大众媒介的方式,即将这种媒介转化为一种个体技术,通过构造一种总体性的局部环境(如范德贝克的多元电影或沃霍尔的Up-Tight,两者完全相反,前者希望引导观众向外,后者将观众向内、向地下拉扯),穿透外部系统对受众的控制。(换言之,一种二重辩证,当美国希望用开放结构的媒介将人民从单向的传播中拯救出来时,麦克卢汉们希望用紧密的单向结构将人们从国家的专家系统中拯救出来。)
重新审视全书,特纳的论述包含了两个关键的转变:四十年代将结构从内容中剥离出来,考虑结构/媒介本身的效果;六十年代强调「媒介即信息」,结构向内折叠到信息中,「环境」本身成了一种隐喻普遍连接的致幻技术。概言之,通过将人格与媒介结构分离并再度结合(相当意义上是转向官能症式的潜意识领域),六十年代背叛了四十年代的愿景(建构一种敞开的民主媒介结构),但实现了四十年代的理想(塑造一种民主的敞开的人格)。
作为全书论述的最高点,麦克卢汉被用来证明六十年代反文化对民主梦想的继承。可问题也正在与麦克卢汉所采用的「信息」隐喻。事实上,无论是四十年代的人格理论还是六十年代对系统的对抗,两种不同尺度的「民主环境」的实质都是对个体的询唤,即要求个体从有危险的外部世界进入这一环境中,成为安全的、整全的人,同时也成为一台「信息处理器」。换言之,就其策略而言,麦克卢汉所采用的仍是维纳式的戏法,一种通过「缩减」提供「能动」的方式:如果说维纳通过将人转变为自动机以提供一种主动感知信息的能力(这与六十年代后英国受众研究的脉络完全不同),那么麦克卢汉就是将自动机进一步限定为一块只与信息本身交互的芯片(维纳的自动机至少还可以射出导弹,麦克卢汉的芯片则徜徉在信息之海中,并不接地),使得个体能够通过更强大的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源摆脱较弱的信源中的问题。
因此,问题仍在人的容器隐喻。无论是四十年代的人格理论还是后续的控制论,所有此类尝试的基础都是将人类作为一个可以储存社会刺激的单口容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漏斗(大众媒介)限制了倒进容器中的事物,那么容器内的构造就会逐渐偏离真实。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倒入更多反向的事物,或是导入强力的溶剂将其溶解。可如果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容器,而是一个不断被外部事物铭刻痕迹的壳或是一个网络中的节点?壳不会存储下信息,也不存在倒空的可能,所有刻在它之上的痕迹都是它的一部分,它通过触碰而不是装载来理解世界。同样,一个节点并不存储信息,它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通过自身的网络结构,通过周边的节点。或者换一种想法,将维纳与麦克卢汉的戏法继续向前推进,一种完全的被动可能是主动的吗?一具不是信息处理器的肉体,是否摆脱了所有媒介与系统的威胁?这具肉体可能进一步敞开自己吗?他/她能看到天空的蓝色吗?还是说,他/她会在大众媒介的宣传下以为天空是绿色,必须通过潜意识的冲击才能找回天空之蓝?关键在于,一具肉体可以铭刻一切,它能听到、看到所有,只要它足够敞开,它就能找到天空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