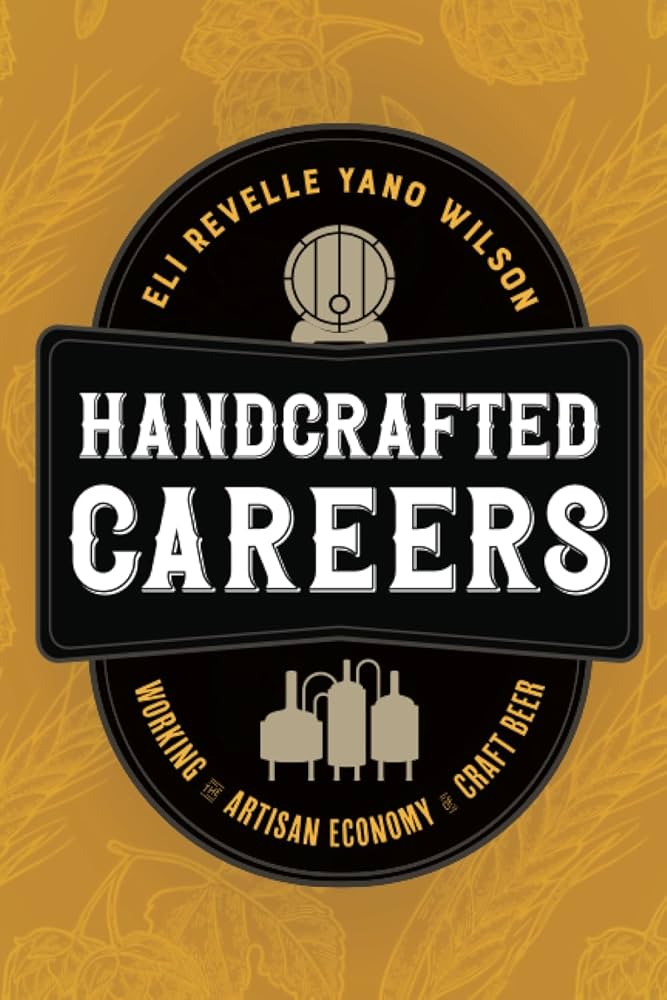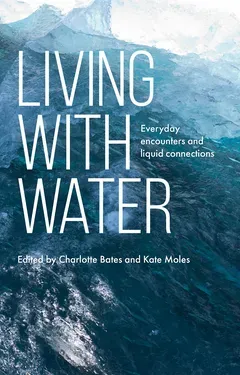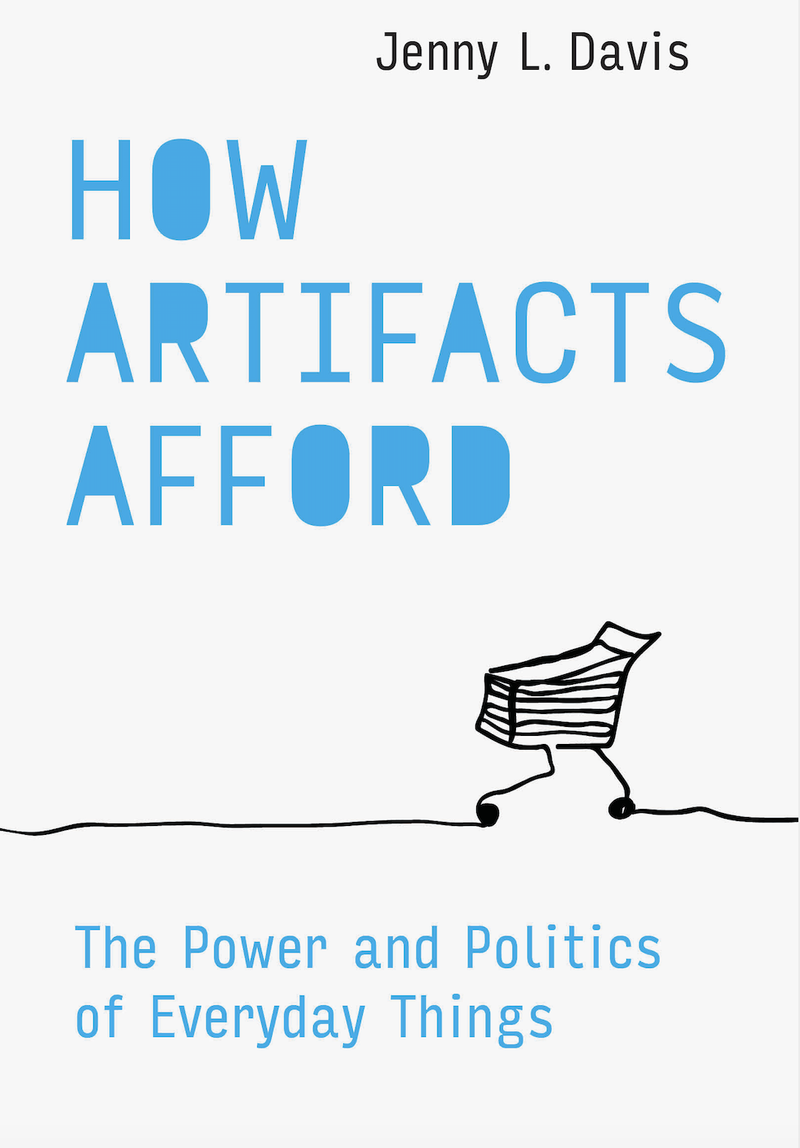两种文体:作为见证的《金翼》
1944年,在哈佛留学的林耀华著成《金翼》并最终刊行。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林氏最初并不打算将这本书当作某种「严肃的学术作品」出版[1],而其中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这本书「离经叛道」的小说体例与其初版的副标题:「一部家族的编年史」[2]。林氏大概也未想到此书后来竟掀起巨大波浪,其影响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贵州苗蛮》。不过与铺天赞誉协同而来的还有读者对这本作品体例的质疑:如果将其当作学术作品看,则太过「轻浮」;若是当作文学作品看,文学性又显然不足。林氏或许也正困扰于此书在「文学作品」与「学术作品」之间暧昧的定位[3],于是便对全书做了修订,在原来「纯粹」的故事中添加了不少理论论述,最后于1947年再版时将副题改为「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算是明确了此书的定位。
不过值得玩味的地方正在于,从今日来看,《金翼》一书两版中,最有价值的恰恰不是后来添补上的「理论升华」,而是那些与传统学术体例不合的「文学内容」——林氏对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早已成为某种「经典」沉淀在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之中,可那些家族沉浮、群体互动乃至人物在故事内外的生死别离,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被不断回顾的时代见证。
自然,我们可以将《金翼》放入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脉络之中并与沈从文、萧红等人进行对话。但对于「似小说而又非小说」 [4]的《金翼》来说,更合适的对话者或许是遥隔太平洋的《街角社会》与今日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只有在这一参照系(而非传统小说的、纯文学的参照系)下,《金翼》之中叙事与文笔上的缺陷[5]才不显现为问题,而是成为某种为故事服务的风格[6];也只有如此观之,《金翼》中那些于主干无关紧要的段落乃至章节才拥有了充足的合理性。
在进一步地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回到故事前后,较为完整地还原出《金翼》内外的风貌。
《金翼》一书的主要舞台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由于地处商业要道,外来的冲击显著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状况,商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当地的社会与家族生活则不免受到极大影响。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展开的《金翼》描写的是「两个家族」的兴衰故事,因此全书也可以借着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划分为三个部分:起初贫穷的东林(黄家)与芬洲(张家)抓住了机遇,在湖口镇开了一爿小店,此后跟上了时代的脉络,借助鱼米生意慢慢致富,从而展开了造房、供养子女教育等诸多活动。随后变故袭来,两家人分别遭遇了丧丁、分家、被绑架等诸多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芬洲被彻底打倒,东林却逐渐学会了与「命运」博弈,一度使家境回到巅峰。最后,芬洲一家几乎彻底从故事中消失了,只有东林还在不断攀升着,直到日本的入侵最后使一切回到了开始。
正如《金翼》的译者庄孔韶所说:「《金翼》不是玩弄技巧之作,它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画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宗族乡村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这些未经抽象的形象、关系与事件看似杂乱,却恰恰直观地揭示了家族制度、文化信仰等等生活内容在近代的变迁[7]。从这一角度来看,《金翼》完全配得上导言中英国人类学家弗斯(R.Firth)的赞扬:「如描绘竹叶一般的简朴的形式,却藏着高度的艺术。」
两重命运:作为寓言的《金翼》
可是正如全书内外所展现的那样,林氏并不满足于「直观地揭示」生活的内容,而是要更具体地去探究其间的主导力量与机制[8]。而对于两个家族的衰落的根本原因,《金翼》一书给出的答案便是「命运」。不过这一命运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运,正如林氏所说「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将『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金翼》中人物所面临的命运是唯物化的「历史的命运」,是物质环境、技术环境、人的适应力及各人际关系系统之间的关系 [9]——在这一意义上,承担命运的也就不仅仅是个人与家族,村落、地方、国家、历史都成为了命运的载体。于是《金翼》中的东林一家在与更大的单位共享命运的同时,通过个体的「把握」获取了对未来更加准确地了解,从而得以一步步将自己的生活拓展到了更高的历史地层之上。
「人的生活就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而在不均衡时刻把握住向上的机会,创造更好的均衡,便是推动个体生活拓展的最重要手段。《金翼》一书的大多数情节,都不过是对这种「平衡论」逻辑的展开与阐释。东林最初的发家致富是因为把握住了商业潮流与鱼米贸易在新时代的重要性(嗅到商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有「农业平衡」后取得了「新的商业平衡」。而此后芬洲的失败则是由于他没能适应家中丧丁的不平衡,从而最终走向了没落[10]。无论是几次分家、分店还是生意的拓展收缩,在作者看来,东林的成功正是因为他逐渐变得「聪明」,学会了应对「命运」,因为「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学习对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11],而东林恰恰是斯金纳箱中最引人注目的那只「白鼠」——他熟练地掌握了林氏所揭示出的影响「命运」与「平衡」的要素(即吴文藻先生所说的「血缘、地缘与职缘」),并竭力改变其中可以被改变的部分。
对于《金翼》一书的典型解读便如上文一般,认为其基底是功能主义的,反对「风水」与传统「命运」的。但此书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整个故事及其前后的真实家族历史所揭示出的,恰恰是两种「命运」(作者所追求的唯物的「命运」与传统的「风水命运」)的共存。为了区分,我们不妨将前者改写为「运命」,而将后者写作「命运」[12]。
在两重命运的展现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东林最初的「发迹」:家道的中落使得「黄家若不另寻某生之道,便注定败落下去」,看上去似乎正是「运命」推动着东林寻找新的生路,可是这一推动的直接结果却是他「开始同那些在商道上开茶馆和歇脚的人混在一起」,直到他「赌钱赢了几块」(这只能是由「命运」带来的)才最终能够开始在茶馆卖花生。自然,一个有力的反驳是这样的内容不过是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的偶然性,并不影响「寻找新生路」的必然。但类似的情节并非唯一,在后续篇章中,同样是由于家中兄弟的刺激/排挤,东林的儿子五哥也在村中与各色人等厮混并且常常赌博,看上去父子经历相差不多,可在书中的评价却大为不同——对于东林,厮混的经历是构成转机改变命运的重要推动;而对于五哥,厮混则被暗示为他人生中的一段歧途。正是这种微妙的差异揭示了作者态度与其理论的暧昧所在:「运命」可以为人所改变,但并没有固定的方式,于是确定人是否成功改变或应对了「运命」的方法就是看其结果,但某一事件乃至整个人生的结果却又相当依赖「命运」,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准确地区分「运气好」与「做对了」。只能后设地判定一个人究竟是「机智」或是「奸诈」,是在「捕捉机会」还是「无端厮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译者所赞许的此书「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是一个从根本上就无法达到的目标,因为这些叙事形象被叙事本身(尤其是作者叙事背后潜藏的理论预设)所截断了,不再拥有「不带偏见」的可能。
事实上如果仔细梳理文中许多人物的性格(较为明显的是大哥、五哥与那个飘渺的似乎不真正在场的「小哥」),不难发现人物本身的性格发展几无逻辑,甚至毫无缘故地发生较大变化。作者并未在本书中对这些变化作出解释,但在《银翅》中,作者口述五十年代回乡时,同样感叹四哥性格变化极大并认为这是天长日久的生活所导致的——文本内外的类似变迁或许可以进行对照,作者由于自身视角限制所以很多时候自然不能呈现家中事件的全貌;而「生活会改变性格」这种认识又使得作者与读者都得以忽略人物性格的变化,仅仅从人物短期的行动(与作者的预设)之中找到人物的形象。换言之,《金翅》中的形象之所以看上去客观,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未加太多个人判断,不过是「平铺直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些「不多的判断」都为前后的情节(或我们的生活「常识」)所解释从而变得不再怪诞,从而出现了「厮混的东林」是「聪明的」而「厮混的五哥」是「走偏的」这样的状况。
这种对人物性格的暧昧描绘与作者理论的暧昧是全然一体并且相互解释的。已经有不少论者指出,作者着力描绘的两家在面对打击时一兴一衰的差异几乎是一种必然(至少张家难免衰落):张家损失了太多男丁(茂魁、茂德、茂衡),而在农业社会之中,男丁不仅主要负责生产(经济),而且还是沟通家族与地方的重要社交节点(如三哥的学成回乡就大大提高了黄家的地位),甚至男丁数量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地位(「面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家的日渐衰败几乎是必然的:留下的人中大部分是需要被「供养」的妇女老人,经济上便先难以支撑(因为每人耕种而不得不将地转租出去);而芬洲在这种状况下的放弃又进一步加剧了家族的封闭,从而加速了家族的衰落。相反,黄家在直到全书结束的最后一章也仅仅损失了五哥一个主要男丁(这一损失在短短两章中就呈现出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拥有充足的「不衰败」的资本。
但作者的陈述显然没有着重于此,而是更加倾向于展现东林与芬洲在面临困境时候所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前者顽强,而后者软弱,快速地放弃。这恰好印证的作者在全书最初就提出的「竹竿理论」(一种平衡论的变体):「人与人之间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似乎正是因为芬洲并没能勇敢地抵御痛苦使得整个家族的网络彻底垮了下去,而东林则是那个支撑下来并获得胜利的人。这一出现在全书最重要的情节上的悖谬恰恰呈现了前文所说的人物性格与作者理论一体的暧昧——芬洲的失败最终证明了他的选择是错误的(尽管事实上他「无从选择」),他是不「聪明」的,没能改变「运命」;而这与东林的成功之对比恰恰是作者用于「直观地证明」其理论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此类「循环论证」在书中大量可见,但这并未证明作者的理论是一种全然的虚构,而恰恰反映出作者及其理论本身就处在一种「不平衡」之中。接受传统蒙学教育、宗族文化出身的林耀华,在接受了「科学的」社会学观念之后,很自然地变得不平衡了——在「运命」与「命运」之间,在「信仰」与「科学」之间,他需要取得一个可能的调和,获取一个新的平衡。从表面上看,这一新平衡毫无疑问是「全面科学化」的,张家身处「龙吐珠」却仍旧衰败与作者用于分析故事的功能主义视角恰是最好的例证;但那些无处不在的「悖谬」与更加直观的可见的内容(如「小哥小时候抓起笔」「道士给父亲算卦的结果」甚至常常出现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13])都说明,在这个故事之中有着强大的「命运」(信仰)的背景。尽管作者试图将之收编在「运命」之中(最典型的便是上述张黄两家的对比),但却终归是失败了,而他自身态度的飘忽不定也就通过这些「失败的收编」得以展示出来,从而制造了那种弥散在全书之中的「无力感」[14]。
这一失败显然为作者本人所知:「现在,当先生回顾四十年前所做的社会学分析时,觉得还有一定局限,例如他觉得对岭尾、湖口乃至古田县的乡镇社会经济矛盾及其发展的分析略感不足;对事物发展的原因的描述,亦有偶然性之嫌。」看上去在经历了思想上的改造与洗礼后,八十年代的林氏在反思《金翼》时似乎已彻底到达了自己设想的理论位置上。可事实却是,在那次访谈的末尾,当庄氏提到「三哥」的儿子现正带领大家庭重新复兴之时,作者的第一反应便是「我知道,是风水的解释吗?」这说明直到那时,作者仍旧没能完全放弃对于「命运」(信仰、偶然性)的某种信赖——同书写《金翼》时一样,只有在完全处于理论之中时,他才能够将「命运」转化为可实证的物质或某种「努力的结晶」;而一旦历史/现实出场,「命运」就复现了其占卜一般的意涵。
这并非是说我们应当迷信或是依赖命运,而是需要理解,《金翼》在「透过这个小小的黄家如何从一个僻远的村庄渐渐拓展到城市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刻画了人的社会文化体系如何一点点维持、拓展和改变的所有动力」的同时,也呈现了部分动力的「不可见」。而在日常生活与学术之中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些「不可见」的部分,并使之与技术化、科学化的现实得以共处,是作者与我们同样面对的难题。
不妨再不恰当地引用一次《祖与占》之中的台词作为结尾:
我们玩弄生命的源泉,却失败了。
参考文献
[1]林耀华, 庄孔韶, 林宗成.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1990.
[2]李培林, 渠敬东, 杨雅彬. 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林耀华. 林耀华学述[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4]庄孔韶等.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 [M]. 民族出版社.2005, 17.
[5] 庄孔韶.银翅[M]. 三联书店.2016.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 ↩︎
渠敬东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 ↩︎
有意思的是其弟子庄孔韶所写的姊妹篇《银翅》就几乎没有这方面顾虑,而是呼吁「不浪费的人类学」,即认定「文学作品」与「学术作品」可是一体两面。 ↩︎
渠敬东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 ↩︎
这种缺陷不单是「平铺直叙」造成的,也是两重翻译的过程导致的语言上的隔阂。 ↩︎
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生命传记法」也就是今日「非虚构写作」中常见写作方式的一种早期实践。 ↩︎
这种揭示甚至是超越作者自身所想的,不然他也不会将此书命名为「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而译者的续作《银翅》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应并拓展了《金翼》一书的主题。 ↩︎
这很明显地受到了吴文藻等人的影响。 ↩︎
吴文藻先生有过类似论述:「血缘、地缘、职缘这三种形式基本上可以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的结合方式。」 ↩︎
事实上在后文中我们会提到,芬洲的失败并非简单的不适应所带来的。 ↩︎
毫无疑问作者的这种看法有着强烈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背景。 ↩︎
也不妨假借一部法国电影的名称,分别称这两种命运为「祖」与「占」(前者是「祖先」、「家族」可以试图改变的,后者则是「占卜」、「上天」所赋予的)。而这种不搭边的想法正是本文标题的来源。 ↩︎
不难理解这一连接词带有强烈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感」。 ↩︎
因篇幅有限未能具体展开,但这种「无力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东林做出的每一个「聪明的」决策和行动都并不直接带来一项反馈,其正确性永远是后设的。于是我们永远不能像作者期望地那样直观地感受到人在改变「运命」,甚至常常迷茫于东林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这在东林老后尤其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