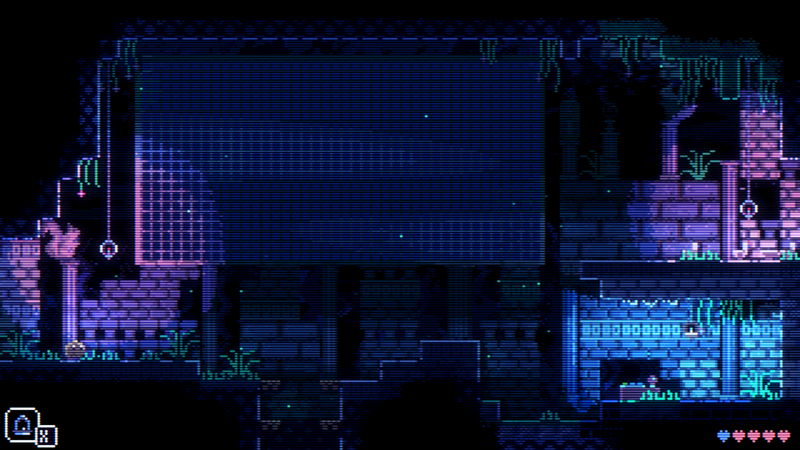性别/性相运动及其启发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以来,社会运动研究既为女性主义运动走上街头提供了理论指引,同时也在其核心议题上受惠于不断发展的女性主义思潮。在《性别与性相运动研究中的新理论方向》(New Theoretical Directions from the Study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Movements)一文中,Wulff 等人尝试梳理社会运动与女性主义的复杂关系,探索两个领域共同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性别与性相运动对整体社会理论研究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设想一种整合了更多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新社会运动研究。
如 Wulff 等人所说,现有的社会运动研究仍扎根于男性主义假设,这不仅限定了社会运动开展的形式,也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使得研究过度重视运动对政治与经济建制的结果,忽略了对多样的抗议、运动形式的观察,以及运动对性别、文化、技术等建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若希望进一步开拓其空间,便需要如 Wulff 等人所说的那样,抛开旧有的男性主义视角,重新思考社会运动领域的诸多基本概念,如国家(state)、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组织(organizations)、框架过程(framing processes)与情感(emotions)等等。
然而「重思」亦需承继一定的脉络, Wulff 等人选择的正是集体认同、多建制政治(multi-institutional politics)与情感(emotions)三个维度。三者之中,集体认同承继了图海纳以降的新社会运动脉络,希望探索特定的身份认同如何构成社会运动的动力,而社会运动的过程又如何可能在部署、维持、发展等多种层面上对集体认同产生作用;多建制政治则希望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拓宽对运动策略、结果、形成方式的理解,以纳入更丰富的社会运动实践,并对已有运动及其研究进行重新评估,甚至指导未来的运动实践1;类似的,「情感」维度要求研究者探索情感与运动的双向互动,既包括不同形式的情感2对运动的作用,也涵盖社会运动中的情感生成(如反讽、自豪或愤怒)。
诚然, Wulff 等人的确指出了当下社会运动研究的问题,也给出了不少解方。可由于篇幅的限制, Wulff 等人更多强调了社会运动与女性主义在研究层面的交汇(尤其详尽地挖掘了性别与性相运动这一特定议题中的研究),而较少关注性别研究与社会运动理论的内在关系,可以说是梳理充分而理论交融略有缺憾。行文策略的选择又进一步限制了文本的推进能力,使得 Wulff 等人指出的集体认同、多建制政治与情感三个维度显得并不稳固,似乎仅能作为某种「启发」,而不能像其所设想的那样,成为社会运动研究未来可以依赖的发展进路。
因此,为了展开 Wulff 等人的论述,挖掘其潜能,本文将首先回溯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观点与相关争议,尝试梳理性别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内在的亲缘关系;随后,本文将寻找性别理论之外的潜在资源,探索集体认同、多元建制与情感政治三个维度的复杂脉络,以进一步描绘相关脉络与社会运动研究融合之可能。
女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脉络
早期女性主义探索
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不同,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较为关注社会运动的实践,而并未在理论上深入推进。参照洛维尔(Lovell)的说法,或许可以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发展出的早期女性主义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女性主义的不同变体。其核心既包括劳动过程与劳动力的社会性别化、工作和雇佣关系、家庭劳动和家户分工这样涉及经济关系的议题,自然也包括女性选举权、受教育权等政治权利议题。
然而早期性别理论对政治、经济建制的关注却并未直接指向塑造劳动市场或政治机会的性别结构,而是始终笼罩在「家庭/家户」(family / household)——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整体框架中,一个进行生物再生产、子女养育与儿童早期社会化的场所——的阴影之下。(Lovell,2000)换言之,早期性别理论的实践性源于其「生产性」,其核心追求在于,从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两性关系」或者「家庭关系」还原出一种「正常的/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得整体的人类生产力(经济的、社会的与生物的)得以解放。
作为对现存社会的整体性反抗的一环,早期性别理论无法从现有的社会观念(如女性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因此不应拥有选举权)中寻找、界定出一种更真实的关系形态或性相。因此,与其整体理论立场吻合,早期性别理论只能从经济再生产出发设想「正常/自然」的状态,因此,在不同经济条件下,这一状态似乎既可以是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分工,亦可以是所有人作为平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去性别化,甚至可以是某种亦生物生产与群落维持为核心的母权社会系统。3(Adkins,1995)
为解决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内在的问题,同时不切断自身与整个马克思注意传统的关系,六十年代后的女性主义者有意识地引入了别样的资源(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的各种变体、索绪尔以降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尝试以新的方式理解性别问题,而阿尔都塞正是各种理论的交汇处。通过对马克思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以及对弗洛伊德的拉康式理解,阿尔都塞「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从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各种社会理论形式,专项以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说法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特纳,2003: 374)。在此基础上,通过阿尔都塞,第二波女性主义整体上转入了对文化、符号的关注,而这又进一步导出了四项关键议题。
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
其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是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最稳固的基础,无论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还是六十年代后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对女性特质之建构性的研究都是重中之重(Millett,1971;Greer,1971;Oakley,2015)。性别的社会建构论所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生理上的区分,在此,大部分学者选择反抗生物学话语,或是试图构造某种生理与文化的平衡(Rubin,1975),或是有意贬低生理上的差异;亦有如菲尔斯通(Firestone,2003)与波伏娃(2014)这般,采取了完全相反策略的研究者: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详尽写下了大量女性身体的特有体验,表现出一种对女性身体本身的反感甚至痛恨。
其二,男权制(Patriarchy)。对男权制的讨论最为集中地展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与早期女性主义的差异。在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框架下,「男权制」并不隶属于任何经济或政治系统,它是一种独立的支配形式,无法被还原为其他形式的支配。这一方面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不需再将任何性别问题还原为经济或政治上的问题从而将其无限延后),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意义的模糊:如米切尔(Mitchell,1974)或巴蕾特(Barrett)似乎希望将男权制限定在家庭关系互动之中;可相对的,大多数研究者,如沃尔比(Walby,1990)与佩特曼(Pateman,1988)则更倾向于将男权制理解为某种无处不在的弥散性的文化建制4。
其三,性相(Sexuality)。在早期女性主义思潮中,性相问题主要关涉到「性本性」5,尤其是女性本性的界定。这又进一步牵涉到两个问题:其一,如果「真正的女人」是用某种男性吸引力加以界定的,那女性主义者算是「真正的女人」吗?其二,即便抛开传统的性别角色,性别(尤其是女性性别)的定义是否与其性取向有关,换言之,女同性恋算女性吗?(Allen,1990)在这一议题中,生物学话语在不同层面上被解构甚至再利用(哈洛威[哈拉维],2010;Koedt,Levine,and Rappone,1973),可其最终结果仍是导向了一种激进的反「强迫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政治,也即后来的「政治女同性恋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6。
其四,母性女性主义的早期思潮。与前述三个面向不同,母性女性主义的似乎并不要求贬低女性的身体或胜利区别,反而要求发掘女性身体与身份中的特殊性。如乔多萝(Chodorow,1978)与吉利根(Gilligan,1982)就颇为重视子女养育的功能与经验,试图赋予这些女性特有的感知以特殊地位,并由此证明,女性不仅拥有独立于男性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男性无法企及的自然性与本真性。同样,也有如伊莉嘉瑞(Irigaray)以降的学者,通过恢复女性身体及其物质性,从而导向一种新的奠基于身体差异的「肉体女性主义」7。
内在的「女性」视角
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整体脉络相当复杂,因此,以上四项议题并不能概括该领域全貌,而仅能作为几个切口,帮助进入这一领域。然而我们仍可尝试由这四项议题及其相关讨论出发,分析女性主义内部的议题如何导向集体认同、多元建制与情感政治三个维度,两者之间又是否存在理论层面的内生关联,以期进一步理解 Wulff 等人的努力,为社会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提供更加可靠的联结。
回到三个维度本身。其中「集体认同」一维可以看作早期女性主义社会运动(以「女性」身份为中心争取各项权利)的自然延续,与此同时,必须意识到,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对生物与社会身份的区分,尤其是对生物学话语的贬义,在相当程度上取消了「自我」内在的本真性8。由于个体不再拥有稳定的外来标准以界定自身(马克思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自我」也就不再理所应当,而成了一个需要维护的对象,一项需要经营的事业。换言之,只在生物身份与社会身份极端分离的现代状况下,当代意义上的、需要通过(社会的或个人的)运动来加以维护的「认同」概念才得以实现。
与之类似,「多元建制」一维的拓展同样离不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传统的社会运动,无论处于马克思或是其他理论脉络中,运动的目标大多围绕经济或政治建制展开。就此而言,第二波女性主义对男权制的讨论,尤其是对「性别建制」的重视,本身就导向了一种初步的非政治建制的观念9。如果男权制不仅是资本主义系统或国家权力系统的一个侧面,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那么自然也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以这一系统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自然,「多元建制」观念亦收到「性相」讨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者面临的总体性问题是,既然国家与经济系统都没有否认同性恋本身(也就是同性恋处在政治、法律、经济的真空中),那为什么还存在针对同性恋的压迫?答案就导向了独立于以上诸要素的建制,也即性别/文化建制。
相较之下,「情感政治」一维的来源既有理论的面向,亦有经验之面向。一方面,情感政治的正当性,相当程度上源于母性女性主义及相关理论的努力,尤其是伊莉嘉瑞等研究者对情感本身(相对于「男性」的的理性)的去污名化;另一方面,不论是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家,还是后来学院性质更强烈的第二波女性主义研究者,女性主义者总是在学院内外遭受诸多阻力——或是个人被指责为「假的女人」,或是理论被评价为「故弄玄虚」「过度解构」——所有的阻力又进一步迫使活动家、研究者以更激进地态度保持自我(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s,1981),由此,一种剧烈的、完全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的情感成了女性主义运动内在的一部分。这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男性想象的「非理性」的社会运动形式。
迈向「非男性」的社会运动研究
超越认同与多元建制
如前所述,集体认同、多元建制与情感政治三维度不仅存在于性别/性相理论与社会运动研究的交界之中,更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理论关联,有助于拓宽社会运动研究的整体视野。然而要达到此目的,研究者仍需在 Wulff 等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换言之,在将三维度融入社会运动研究的同时,也要理解三维度的限制与短板,找到应对甚至超越其问题的资源。
如果图海纳(2003)所说确凿,集体认同已然成为当代社会运动的重要动力甚至核心动力,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集体认同内在的限制?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有过一段论述:「我们总是在与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承认的那些特性的对话中,有时在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不同于一种将认同理解为某种实在物的想法,在泰勒的观念中,认同原本就是一种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中被不断构造出来的东西,或者说,「认同」就是这种互动的过程本身。可与此同时,当代的集体认同实践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本真性」的强调。
以某种「本真性」(可以来源于国族身份、生理性别或是某种亚文化喜好)为核心的当代集体认同预设了一种先在的不可否认的「分类」。在社会运动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当活动家们在某种「集体认同」的旗帜下发起运动时,他们带来的首先是「差异」而不是「认可」。与二十世纪后半页强调差异的社会理论(如德勒兹或德里达)不同,对本真性的强调并非「以差异为同一之基础」——所有人内在的差异性为人类之间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而是「同时生成差异与同一」,也即在生成内群认同的同时制造了群际间不可磨灭甚至难以互通的区隔。因此,越是在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认同问题凸显之时,运动者与研究者越是应当仔细考察这一框架本身的限度,在运动策略上或是理论上,找到超越之道。
同样,面对不断分化的现代社会系统,当代社会运动的确在向多元建制发展,试图在有形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之外,捕捉到那些抽象的、不具身的、不可见的敌人,亦即某种以符号和文化为载体的权力。然而,当社会运动在接纳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建构论脉络时,也需注意避免陷入「文化化约主义」的境况中,将一切非政治与经济的建制视作不同形式的文化建制。只在特定的语境下,性别建制(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运动)、技术建制(开源运动)、教育建制(反减负运动)、知识建制(Open Access 运动)才可能被统一在「文化建制」的框架下。相对的,一种更加开放的社会运动研究不仅将引入多元建制的视野,也应凸显不同建制间的差异与关联。也只有这样,社会运动研究者才能进一步拓展其分析能力,深入理解运动的目标、行动及其结果间的复合关系。
从情感到情动
在情感政治的维度上, Wulff 等人付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其处理仍侧重描述性而缺乏规范性面向。如果希望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深入发掘情感政治的效果,研究者必须超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即用特定的术语框定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尝试将更完整的情感研究的脉络带入社会运动研究中,以补足后者对「非理性」面向的理解。相对的,正如 Bericat(2016)所说,发展已近半世纪的「情感社会学」也有其内在缺陷,即过度聚焦于微观互动,而缺乏对宏观的社会情感(Socialemotion)的考察。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研究亦可为情感研究理解「情感」的宏微连接(微观的情感互动导向/生成宏观的社会情感)提供一条进路。可若要实现这种相互补全,社会运动研究仍有两项任务亟待实现:
其一,丰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情感」定义。现有研究对社会运动中的「情感」的关注过于粗线条,或是笼统地讨论情感(emotion),或是讨论某种突发性的、作为应激的「激情/情绪」(passion/emotion)。事实上,当代情感研究已然认识到,不同情感(emotions)间的异质性远超出其同一性:慢性的长期的「感受/心境」(feelings/mood,例如慢性病患者对自我身体的感受,或是某种长期的压迫感、紧张感)就显著不同于爆发性的「激情」(passion);反思性的较为内生的「情绪」(sentiment)亦有别于刺激性的较为外生的「刺激」(stimulation)10。所有不同类型的情感都有可能与社会运动发生不同形态的联系,以不同的方式助推其发展,这也为分析社会运动中情感的作用提供了先在的框架。
其二,从情感的效果回溯到情感的发生与作用机制。现有的社会运动研究并不关注情感的出现(尤其是个体的情感或小群体的情感互动如何生成集体的社会的情感),即便有所论述,也只是归因于个体或群体对建制的整体性反抗与反应(如黑人长期面对白人主导的警察系统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整体上并未超出十九世纪群体心理学的水平。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倾向于将「情感」整体性地理解为运动的「助燃剂」(或「引线」),从而忽略了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尤其是其他潜在的可能11。在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从情感研究、身体研究、互动论等偏向微观的取径出发,在社会运动的经验研究中尝试构造完整的情感生成与转化的线索——这既需要社会运动研究者对微观社会学的深入理解,亦需要微观取径的研究者加强对「看似宏观」的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议题的关注。
如果说 Wulff 等人提出了一种「女性」视角的社会运动研究进路,那么在其基础上,通过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回溯及批判性讨论,本文设想了一种更加开放的「非男性」的社会运动研究:不仅作为对已有社会运动研究(侧重理性、结构、政经建制)反思,也尝试融合不同进路之优劣,以面向未来的研究发展;不仅从其他社会研究的分支中汲取养料,也能在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合作下,构成一种更加整体也更具贯穿性的社会运动解释框架,以反哺其他社会领域——最重要的是,它会将视角下放,既能看到运动进程、运动网络、运动的参与者,也将触及那些汗淋淋的身体,他/她们的认同和他/她们的情感。
注释
- 在论述多建制政治时,Wulff 等人特别指出,这一思路有主义拓展Armstrong与Bernstein的理论,即将组织增殖看作对「异质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的一种回应。此处,Wulff 等人所指出的正是社会运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日益分化成诸多相对独立的场域/领域(如经济场、政治场、教育场、艺术场)的现代社会中,对多元建制的反抗才可能生成。因此,从单一建制的社会运动迈向多元建制的社会运动,实质上是社会运动研究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必然要求。 ↩︎
- 这一部分是 Wulff 等人论述的弱点。与身份认同或多元建制不同,情感研究在当代尚未有非常成熟系统的理论思考。因此,反映到文章的论述中, Wulff 等人往往杂糅了不同层面的情感研究概念——如情感惯习(emotional habitus)、情感文化(emotion cultures)、情感劳动(emotion labor)——并尝试借这些概念整合其论述。然而就其结果来看,大部分较高抽象层级的概念都未能与对应的社会运动实证研究紧密结合,最后论述的推进反而更依赖诸如「愤怒的动员潜力」或「抗议的情绪」这样的概念——理论与经验之间似乎出现了相当大的裂隙。 ↩︎
- 尽管此处的「早期性别理论」并不包括诸如《母权论》或《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类在女性主义运动脉络外发展出来的作品,然而早期性别理论(尤其是其思考路径)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类作品的影响。 ↩︎
- 正是在这种弥散性的男权理解中,女性似乎成了永恒的受害者,她自身的命运只有通过反抗整个社会结构的所有层面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不仅如此,对男权制的描述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压迫,抹杀了不同时空中脉络不尽相同的性别实践。 ↩︎
- Sexuality 一词有多种翻译,包括「性性」「性本性」「性相」等等,此处采用「性相」这一翻译意在强调 Sexuality 的流变性而非稳定性。 ↩︎
- 正如维蒂希(Wittig,1982)所说:「女同性恋是我知道唯一超越男人的各个范畴的概念……因为使一个女人成其为女人的, 正是与男人之间的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女同性恋者通过拒绝成为或保持异性恋而拜托了这种关系。」在此,女同性恋身份已然成了一种政治选择。 ↩︎
- 正是在这一点上,母性女性主义远离了建构论的脉络,构造了某种新的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后续也发展出了非肉体性的面向,即强调女性的敏感、情绪化等等倾向导向了一种比男性更完整的人格,因而更合适发展出一个和平的世界。 ↩︎
- 这种解构中较为激进也极其具有影响力的尝试来自哈拉维《猿猴、赛博格和女人》。通过说明「人类」与「猿猴」(非人)之间微妙的界限,哈拉维将人之特殊性转制成了一种必须通过文化来完成的(因此也密布危险的)事业。 ↩︎
- 「多元建制」观念的早期来源也包括二十世纪早期文化人类学的进展,尤其是对多元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系统的发掘,揭示出了文化系统的独立性。 ↩︎
- 在当代情感理论中,一个特殊的分支来自后现代哲学:以德勒兹为代表的研究者从斯宾诺莎处挖掘出了 Affect(汪明安等人译作「情动」)一词,以表达一种更加主动的(不是作为对刺激的反应,而是对外部的主动接纳)情绪力量的迸发与释放。马苏米指出了这一概念与社会运动间的亲缘关系,然而目前尚未有成熟的后续研究。 ↩︎
- 已有研究者意识到,涂尔干传统或塔尔德(Tarde)传统(拉图[拉图尔],2017)对情感有一种相当特殊的理解。在涂尔干处,「集体欢腾」提供了一种「以运动为整合」的观念;在塔尔德处,情感可以说是社会运动与社会变迁的根本要素,也是社会运作的最基本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