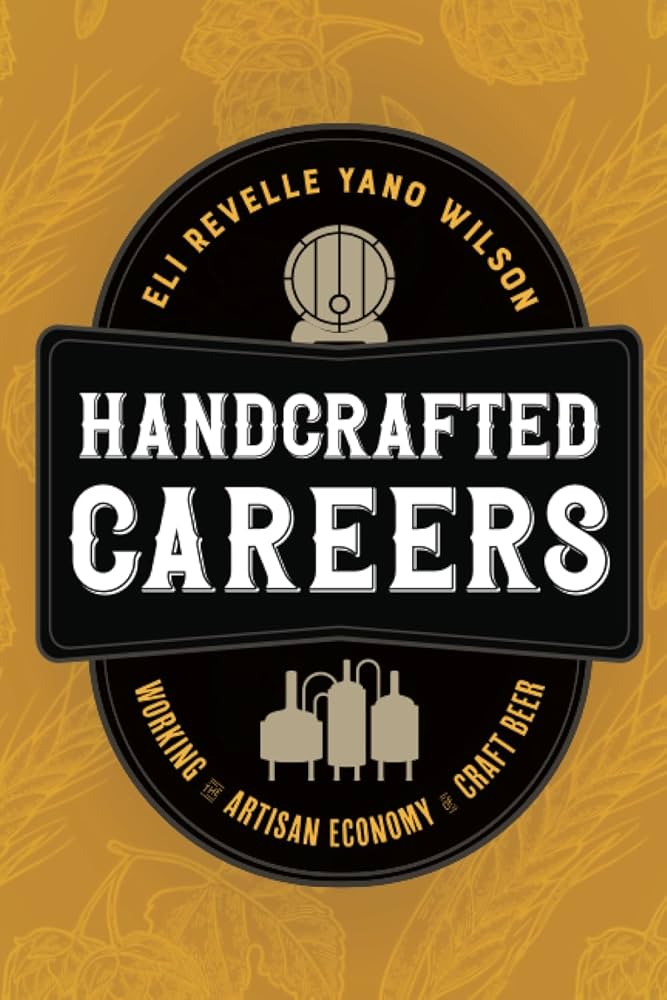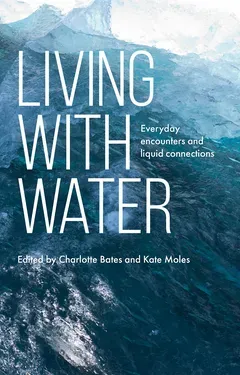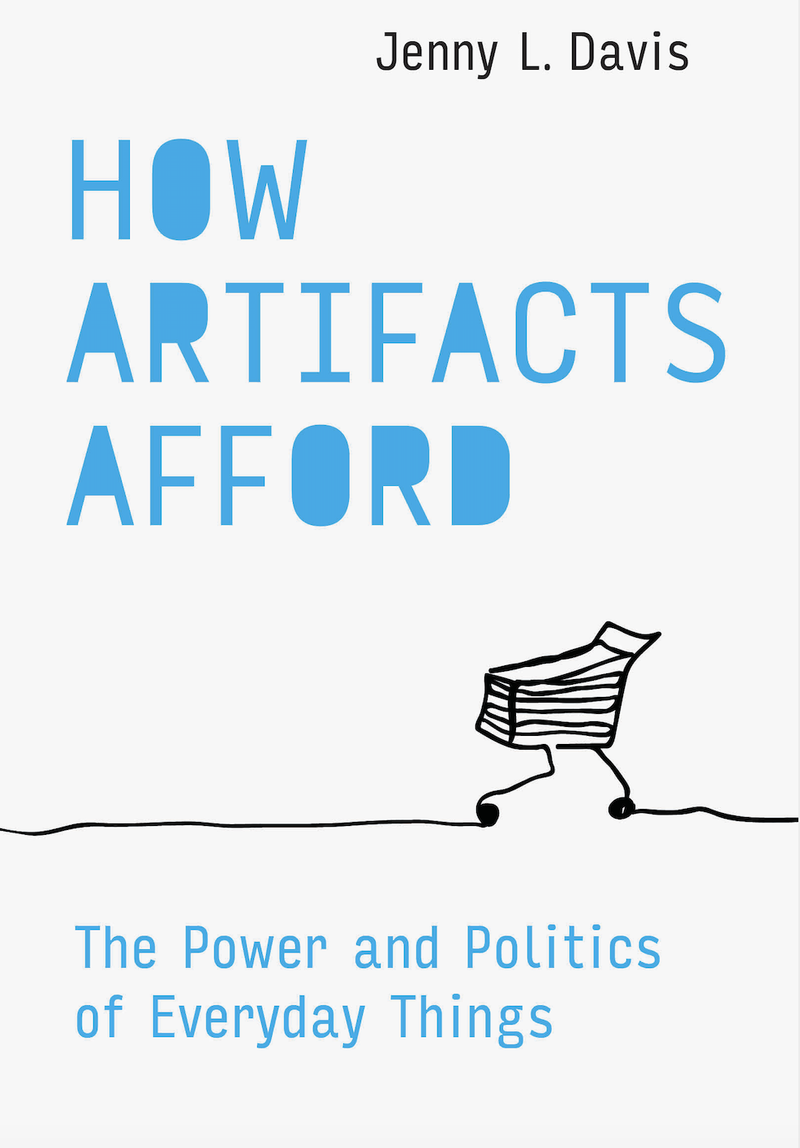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我们不喜欢这样。」「怎么会喜欢呢,」K说,「你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可是只能这样做。」[1]——卡夫卡
漫游:价值、货币与目的序列
「他可以随意保持自己的本色或化为他人。他可以随心所欲,附在任何人身上,像那些寻求肉体的游魂一样。只有对于他,到处都是虚席以待。」[2]——波德莱尔
在评论波德莱尔时,本雅明使用了「漫游者(flaneur)」一词,以描述波德莱尔及其所象征的一种独特的现代人格:他们游走于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拾捡各种生活碎片,但却从不融入其中[3]。毫无疑问,漫游者们最为理想的寄居之所正是工业革命之后不断兴起的大都市,这里同时提供了漫游所需的场所与「内容」,赋予了漫游现代生活的意义碎片。由此观之,弗里斯比将齐美尔这位大城市出生、一生衣食无忧的「边缘学者」描绘为一个「社会学漫游者(sociological flaneur)」似乎不无道理。但都市背景与小品文式的写作风格仅仅能够解释「漫游者」三字,实际上,齐美尔作为「社会学漫游者」的特点正在于其研究内容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漫游者」特质。
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一书中,货币的形象呈现了与波德莱尔诗中所描绘的漫游者形象的高度一致性——「可以随意保持自己的本色或化为他人」、「可以随心所欲,附在任何人身上」、「对于他,到处都是虚席以待」——货币可以作为铸造货币的物质实体存在,也可以随时转化为价值象征;货币在诸多人之间的转移并无任何障碍;货币也受到所有商品的欢迎。正如齐美尔自己所说:「在这里,货币仅仅作为历史世界中的一种构形物象征着事物的客观行为,并在自身和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4],作为漫游者的货币首先象征的(或者说其本身)便是时代在「实在」与「价值」之间进行的特殊构建,而实在与价值的这一对区分正是《货币哲学》一书开篇所进行的基础性的讨论。
为什么要区分实在与价值?齐美尔所给出的回答是:如果不将世界图景分割为二元的实在与价值,我们便无法清晰完整地了解世界图景[5]。但与常见的物质/精神二分不同,在齐美尔的理论中,价值所强调的并不是某种精神的主观性[6],而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联结与互动关系。主客体的区分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的「挫败」,如果需要被即时地满足,那「客体」的意义便不会被注意[7]。而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价值」也延续了这样的互动:主体需要的挫败促使需要的情绪转向客体而非需要本身,而这也就加强了(或赋予了)客体以价值[8]。与此同时,需要的挫败也意味着主客体之间必然存在着距离,这种由挫败带来的距离产生了价值,也期待被价值所克服[9],在此过程中,价值就成为了某种得到主体承认的客观形式[10]。而这也就为交换这一放弃自有价值换取他人所有价值的行为奠定了基础。
在交换之中,客体的价值悬置于交换对象之间,从而使其价值不再完全由主观决定,而是由客体之间互相决定,具有了「客观性」[11],于是「经济价值」[12]得以产生,「经济体系」得以形成[13]。但客体之间相互决定的价值所表达的必然是某种相对的关系,构成了某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序列[14],而「货币」既在这一价值序列之中,又在其之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衡量着其他的价值,成为这一序列的联结与条件[15]。而对于货币本身来说,它作为一般的存在形式的物质化,只有从事物彼此的相互关系之中才能找到意义[16]——换言之,货币本身是一种「特性的缺乏」,完全可以不拥有内在价值,只体现一种转化关系[17],尽管在历史维度上货币确实直接产生于使用价值[18],只是之后逐渐与其分道扬镳,通过牺牲其他价值成就了纯粹的货币价值[19]。当然,这种「牺牲」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并且实际上是一种永远无法完全结束的进程——一方面,经济的自然小幅通胀与通缩需要货币的内在价值以调节[20],而完全的观念货币也无法阻止政府的制造通胀[21];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货币的概念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互相的牵制,从而无法完全形成纯粹的观念货币[22]。货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由物质转向功能[23],也就不断由依赖其自身转向依赖外部的存在(即具有一定综合性与强度的社会[24])。在这里,货币作为一种对社会的「信任」与社会在交织中共同前行:社会促使货币愈发功能化,货币也支持着社会的结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5]。这种交互关系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货币中「物质意义」的下降使其「价值意义」不断上升,而这反倒使得货币的价值得到了增加[26]——尽管对于货币来说,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作为手段的「概念性」已经先于其物质性的价值(本源)成为了首要的「价值」[27]。
而这种置换关系似乎也被采用货币的领域所吸纳了。具体来说,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人的「目的」构成了某种序列,为了达成「终极目的」需要逐渐达成一系列小的目的,而这也就产生了对「手段」(工具的需要)[28]。而货币越发广泛的普遍性与适用性便意味着它将成为最常见的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29]——而正如货币价值的置换关系一样,为了最有效地达成终极目的[30],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在心理过程中逐渐地被置换成了目的。而这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颠倒,也就带来了贪婪、吝啬、奢侈、贫困、犬儒与乐极生厌(或者说无聊)等消极情绪。
如果简要地分析这些情绪,不难发现,它们虽然表征不同[31],却同时指向了货币的通行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即将衡量价值的标准逐渐由「质」转向了「量」。这种转换一方面与此前所说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有关,另一方面却也源自货币自身「特性的缺乏」。正是因为缺乏特性,所以货币的力量只能来自于「量」[32]。而这种货币的「特性」(即「无特性」)伴随着它在生活中的不断展开,席卷了整个生活世界——无论是历史研究[33]还是政治实践[34],量的重要性都在逐渐超过质的重要性[35]——但这却并不是都由货币自身所致,而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恰如作者在这一部分最后所说:「在这里,货币又一次成为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历史序列的顶峰。」而我们接下来就将要看到的,货币这一顶峰将从各个方面,影响位于它之下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
朋克:生活、自由与个体价值
正如朋克(Punk)一词同时具有「无价值的」、「无知的」与「反叛的」、「个性鲜明的」两重含义,货币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同时朝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货币倾向于强调最具个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发展他们的自主性;而另一方面,通过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到一起,货币却将不同事物、不同人的价值夷平了,使得事物与人逐渐失去了原本有差异的价值,逐渐堕落 [36]。
如果要讨论货币对「个体自由」的作用,那么必然离不开「义务」这个自由的双生子[37]。不妨以农民对土地所有者的义务为例:从最初古罗马时期以人的归属作为义务(依附农、奴隶),逐渐发展此后以上交劳动产品为义务,最后前进到以交货币租税为义务——人身逐渐从义务的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他人从直接要求人身的行为,逐渐发展到只要求人身行为的结果。而货币作为行为结果的特点在于,与直接上交实物相比,它更彻底地排除了人身的因素,从而切断了与个体间的内在联系[38]。
但问题的复杂性却在于,占有(无论是占有土地还是占有义务)是一种「行为」而非一种「状态」。因为占有意味着个体持续地使用或利用客体[39],而这也就同时也意味着对客体的拥有转化成了主体的一部分[40]。但货币的存在却使得这种性质拥有了被搁置的可能,货币本身的无特性意味着货币很难成为主体的一部分[41],并且极少地也更可能延迟地消耗主体的能量[42]。而货币的特性更使得占有者在空间上可以与客体分离[43],货币(被占有物)的力量也更加独立[44]。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劳动成果逐渐失去了个人的特质,甚至不再为单个人所能完成,个人与其劳动成果不可避免地分离了;失去了个人化劳动成果的人的劳动变成了某种「量」,得以与他人进行量的比较,于是完全可替代的个人也得以从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中挣脱出来。在这样的情形下,个体最便于为货币所组织起来:在货币的无特性之下,人们可以忽视除了货币之外的所有特点,仅仅利用货币结合在一起,这大大拓宽了结合的可能与范围[45]。而这正是货币将一切打碎后再重新联结的过程[46]。
可是正如「Punk」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这种重新联结之后的关系的价值大大降低了。个体用货币「免除」了义务,同时也就舍弃与义务紧密相联的权力与重要性,于是货币得以不断打量着每一个人,甚至拥有了衡量人价值的能力[47]。尽管从偿命金[48]、奴隶买卖、买卖婚姻[49]等早期历史现象来看,用外在价值为人估价古已有之,但货币的滥觞带来的却是一种奇异的悖谬:货币不断地将一切事物的价值从「质」降低到「量」,从而根本性地失去了在一些「高层关系」中出场的余地[50],因为这些关系本认为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不能为货币「衡量」(即「污染」);但同时,「卖淫」[51]与「贿赂」[52]的存在却说明货币实际上仍在不断侵蚀着人的价值,不断将人的价值从高处拉向深渊[53]。而这种价值的坠落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本身,还有他的生产与劳动:个体可以与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资料分离,但因为货币并非一个如土地与劳动成果那样打下了自我烙印的客体,这也就同时带来了生活的空洞和缺乏实质意义[54]。对这种情况的一个拯救策略是「劳动货币」这一概念,通过赋予劳动以直接价值,「一种十足的个人价值,甚至可以说是那特定的个人价值将会成为价值标准」[55],尽管劳动要成为一种「价值」或「货币」不得不对其自身进行简化,抹杀其中的个体性[56]。而「劳动货币」的这一悖谬似乎成为了理性化的现代生活风格最佳的隐喻之一。
在现代生活之中,客观化了几乎一切人和事的货币经济最终在越发漫长的目的序列中促成了个人生活的理性化[57],而个人生活的理性化经过货币基础上的人的互动,构成了超个体的理性化[58],也即某种兼具「无特性」与「客观性」生活风格。在这一生活风格中,「算计」[59]是题中应有之意,货币精打细算的本性必然会赋予生活「确定性」[60]。可这种确定性的物质象征,那些科学产品、艺术品乃至一部分现代艺术,作为总体的不断上升的「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却也在拉开与「个体文化」之间的距离:个人几乎没有可能取得与物质文化一致的进步,反而常常倒退[61]。而形成这一鸿沟的正是「思想的物质化」(如书籍、语言等等)与「劳动分工」,前者使得文化可以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得到有效的保存和继承(尽管这并不根本性地指向个体文化的衰落),是较为次要的原因;后者却将生产者、购买者与产品三者分开,使得在客体中的精神性特征不断下降[62],产品逐渐自在独立与生产者与购买者[63],形成完全客观的物质文化,将个体文化排除在外,并使其逐渐落后——在这里,事物不仅成为了独立的客体,而且开始对抗作为主体的人[64]。在这一对抗中,事物自身也逐渐分化了——不仅是劳动工具与材料的专门化,更是如「朋克」一般的产品的「多样风格」。而「风格」正意味着客观的事物似乎逐渐拥有了客观精神,可以使其形式独立于内容本身[65]——换言之,在自我与诸事物之间的「距离」产生巨大的变化,近的变远,远的变近[66],而这也正是现代生活风格的体现[67]。
在距离变化的同时,货币给现代生活风格带来的还有「节奏的机械」、「速度的加快」与「内容的压缩」。对于节奏来说,货币的持续使用节奏改变了原本的生活节奏,使之变得机械化,只能依靠理智调节;对于速度而言,货币快速的流通速度必然会带来生活速度的加快;而货币交易的集中所带来的正是生活内容在「集中」之下被不断压缩,成为一个干瘪的核体。这种持久的特性与快速的变迁统一在货币之上,似乎证明了货币就是一种「象征世界绝对的动态特征的记号」[68]——换言之,也就是象征了齐美尔所宣称的现代文化冲突的实质——一种在「限定」与「流变」之间的矛盾[69]。
可是正如我们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从朋克到赛博朋克(Cyberpunk)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鸿沟,齐美尔所讨论的现代文化是否延续到了今天?货币又是否仍是这一文化中的决定性要素?我想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回应。
赛博:比特、记忆与人工智能
「你好吗,南方人?」「我死了,凯斯。我在这台保坂上待了这么久,算是想明白了。」「死是什么感觉?」「没感觉。」「不爽?」「让我不爽的是,没什么能让我不爽。」
——吉布森
正如的第一部分从漫游者开始,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将回到漫游者之上——区别只是,大都市中的漫游者所研究的是《货币哲学》,而赛博朋克中的神经漫游者所关注的则是「比特哲学」。
吉布森将这本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起名为《神经漫游者》或许不无其道理。在真正的赛博时代,真实的空间或许早已消亡,唯一可以容许我们漫游的地方只能是我们的神经。这一巨大的限制从开始就划清了我们时代(以及将要到来的时代)与齐美尔所处时代的差异,也即比特(电子数据的载体)与货币之间的差异。
不妨将两者进行对比:从性质上看,与货币一样,比特自身是没有任何偏好的,比货币更吊诡的地方在于,相比「造币」这一活动,比特自身其实无从「制造」,从而好像天然是世界的一员。进一步地,如果说货币是客体间价值关系的物质化,那么比特则是客体间一切关系的物质化体现。从价值关系到一切关系的重要进展意味着相比货币,比特自身就有着巨大的能量能够直接作用于实在,而不需要通过价值体系逐渐侵入实在之中,换言之,货币作为一种关系的体现,毫无疑问地将会从属于比特——对此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案例便是比特币,其物质载体相比纸币更加「稀薄」,可是由于运用了特殊的技术,却相较任何一种货币都更难被直接破坏(谁又去破坏一段全球大多数网络中都存在着的代码呢),而考虑到它交易绝对的安全性以及天然的数量限制,类似比特币性质的电子货币几乎毫无疑问地将成为未来货币的一种主要形式(尽管在安全性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并不排除现行的货币体系直接电子化的可能)。
同样可以由比特币牵引而出的是区块链技术。比特币的不可毁灭性正是建立在这一技术之上的。这一技术的实质是将数据不分所有人地散发到全球所有的主机上,在数据需要被重新读取时由所有的主机提供数据源。这种去中心化的「散发」与「读取」延续了货币在主体与意义之间留下的沟壑——比特与信息成为了它们本身,而离其创造者越来越远,「占有」在这里并非是一个被模糊的可能,而根本是不可能,从而消解了主体与其所创造的比特之间的意义——并且更进一步地取消了货币交易中必要的「中心」,使其在客观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当然,正如货币时时刻刻存在的两面性一样。比特对于承载的事物也拥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当硬盘、内存、云盘等逐渐去实体化的储存器不断向实在招手,个体实际上无法抵御这样的诱惑,从而将自我的记忆逐渐地转化成了一段段以比特承载的「文字」、「图片」、「视频」乃至「感受」,可如此储存下来的是一种二进制的编码系统,而在记忆之上的编码系统恰恰意味着我们进一步地丧失对于记忆的控制能力与面对记忆的敏锐感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我们外出远游时,习惯寄回的仍旧是明信片而不是一封带着照片的电邮——这也就最终将导致我们与我们的记忆,也就是与我们持续关联实在的最重要的方式拉开距离;当然,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比特对实在的转译如此逼真与比特本身极度的不可把握形成了对比,当代生活对于载体之外内容的重视在一些情况下有所提升——一如货币时代关于人的「根本价值」的回光返照。
比特对于实在的影响在另一个事例中也得到了体现。我们很容易发现,当代消费主义浪潮不断吹嘘的「贩卖体验」的实质,即隔绝人与其体验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虚拟现实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虚拟的现实取消了现实的难度,可是正如齐美尔分析的那样,「挫败」的消失同时意味着价值的消失,在虚拟现实中,这一逻辑更进一步,即「挫败」的消失意味着实在的消失——因为现实的可虚拟性第一次使人意识到与实在的接触也是一种微型的「挫败」的过程——于是虚拟现实通过部分地模拟现实中的「挫败」(例如触感、视觉、听觉),加以重构的困难(例如游戏的关卡难度),从而使人错觉到实在。但这一错觉的后果,一如货币将一切其他事物的价值降低到它自身的「量」的水平上一般,虚拟现实的普及所带来的必然是人「感受能力」的退化,将人对现实的感知降低到对于虚拟现实的感知上(不难理解,虚拟现实终究只能部分模拟感受),于是实在(无论是记忆中的还是当下的)本身的意义被消解在各种无比逼真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或是神经漫游之中,而我们的生活,内心感受,或许将面临更严厉于货币时代之麻木的情况,变成那个《神经漫游者》中「让我不爽的是,没什么能让我不爽」的「客体般的主体」。
如果说货币是通过自身度量人将人的价值贬低为「量」的价值,那么比特则是通过自身承载「人」(除了肉体之外我们又有什么不能交给比特的呢),将人的存在贬低到比特的维度上。而这一存在的下降过程的终点便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之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那个货币始终祈求但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终点,也就是「完全的理智化」——正如无数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研究者所隐忧的那样,人工智能的任务或许就是将一切非理智的因素排除出这个世界,换言之,健全的人在这里不仅是需要被贬低的对象,甚至需要从存在意义上被消除,换算为一连串的比特。
但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隐忧,我们的时代仍然毫无疑问是为技术所充斥的。技术乐观或者悲观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本身不可能停滞不前。于是正如所有赛博朋克小说的核心所呈现的那样,反乌托邦、反集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技术来反抗——不然便只是朋克而再不赛博。
我们不妨回到《货币哲学》。在这本书将要收尾的时候,齐美尔几乎是感慨一般地陈述到:「这样一个年代如此地突出生活的手段内容,与生活的中心的、明确的意义针锋相对。在此之外我想再没有哪个时代是这样。」[70]站在齐美尔所处的年代,这一论断似乎并无问题。但是在百余年后的赛博时代,我们似乎可以带着悲剧色彩进行回应:在手段与目的的倒置上,我们的时代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并且似乎永远也不会回头。
主要参考文献
1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
2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卡夫卡:《城堡》,高年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 亚丁译,三联书店,2004.
5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 吉布森:《神经漫游者》,Denovo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8 李婷等:《离线》 ,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卡夫卡《城堡》.p.14. ↩︎
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 ↩︎
陈戎女《齐美尔与现代性》.p.37.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420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论述似乎预示了全书「悲观主义」的基调。 ↩︎
「在这里主体性仅仅是临时的,并且事实上很不重要。」齐美尔《货币哲学》 p.7 ↩︎
「只要客体没有为了我们的用处和愉悦立即被给予我们,我们就会需要它们,那就是说,从更广一点来看它们抵制我们的需要。」齐美尔《货币哲学》 p.9 ↩︎
「客体的价值确实依赖于对它的需要,但这个需要不再是纯粹直觉的。」齐美尔《货币哲学》 p.14 ↩︎
「建立距离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它。」齐美尔《货币哲学》 p.17 ↩︎
意志和情感的内容假定了客体的形式。这个客体现在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地面对主体。 ↩︎
「在这里客体的价值是被一种自动构造所决定的,而不管在这构造中有多少主观情感业已被作为前提或内容注入了进去。」「价值与交换之间的深刻联系,作为它们互相决定的结果,通过它们在生活实践之中是等量的这一事实而得到了解释。」「这个等式: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在经济价值中找到了最明确的证明。」齐美尔《货币哲学》 p.21-25 ↩︎
在过去的论述中,经济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实用与稀缺所致。但作者用上述的「挫败」与「交换」理论否认了这一观点。p30-34而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作者的反驳是「劳动」进入「价值领域」也依靠了交换产生的价值抽象,尽管其极有创建,但却是后发的。齐美尔《货币哲学》 p.34-39 ↩︎
「经济体系确实基于抽象、基于交换的相互性,基于付出与获得之间的平衡。」齐美尔《货币哲学》 p.22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40-42 ↩︎
「货币抽象的价值只是表达了构成价值的事物的相对性。」p58 但货币本身又具有着对于所有其他价值都适用的「绝对性」,为了达到这一绝对性,货币必须做到无特性。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64-65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66-72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76-80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86-89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89-p93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93-95 ↩︎
「要在技术上完成概念上正确的事情是不可行的。」齐美尔《货币哲学》 p.98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101-103 ↩︎
「货币的内在性质只是松散地与其质料联系在一起,因为货币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齐美尔《货币哲学》 p.105 ↩︎
「对贸易的促进、价值标准的稳定性、价值的流动性和对流通的加速作用,以凝聚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精华。齐美尔《货币哲学》 p.119」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122-133 ↩︎
「事物的意义在本源与目的之间交换了位置。」 ↩︎
手段」只有在通向「目的」的过程中才存在,因为只有人的「目的」需要「手段」以付诸现实(动物只有本能没有目的,而上帝的目的即现实)。见齐美尔《货币哲学》 p.134-137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139-146 ↩︎
「我们促进最终目的的实现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手段看作目的本身。」齐美尔《货币哲学》 p.160 ↩︎
贪婪与吝啬的表现都是「仓鼠人格」,但前者是认为物体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只能占有,后者则是认为被花掉的钱赋予了物体绝对价值。与前两者不同,奢侈拒绝价值度量,从而使价值充斥在价值转换的过程中(延展性);而贫困则拒绝货币这种手段,以拒绝目的。犬儒以拉低价值作为乐趣。而乐极生厌则是麻木的,根本性地漠视价值。
齐美尔《货币哲学》 p.168-187 ↩︎
「货币的手段也就是它的力量。」p188「无形式和纯量化的特性是同一个东西。」齐美尔《货币哲学》 p.201 ↩︎
「是那些日常小事的总量而非领袖的特殊的个人行为决定了历史图画的全景。」齐美尔《货币哲学》 p.206 ↩︎
「这种民主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并且被提升为一种世界观。」齐美尔《货币哲学》 p.206 ↩︎
「量的范畴主宰了质的范畴,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质被消融在量之中。」齐美尔《货币哲学》 p.206 ↩︎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p.6.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211 ↩︎
「其结果是他们以前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一种纯粹客观化的关系。」齐美尔《货币哲学》 p.213 ↩︎
「不以任何一种行动方式体现的占有仅仅是一种抽象观念而已。」齐美尔《货币哲学》 p.230 ↩︎
「那么它对主体的内在和外在本质的影响就越清晰明了,越具有决定性。」齐美尔《货币哲学》 p.233 ↩︎
「无论钱与个人的这种关联发生在什么地方,它的存在并非和整体意义上的货币相关,而仅仅与货币数量之不同相关。」齐美尔《货币哲学》 p.235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254-255 ↩︎
「货币的作用跟主体及其财产在空间上的疏离联系在一起」。 ↩︎
「在主观性与事物规范之间各司其职的劳动分工现在就是完美的了。」齐美尔《货币哲学》 p.258 ↩︎
「惟有货币能早就出这种对个体一视同仁的联合形式。」齐美尔《货币哲学》 p.268 ↩︎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同时发挥了分裂与统一的作用。」 ↩︎
这一情形的荒谬之处可以从我们时代的新闻中直观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每日赔偿258.89元》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277-278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292-294 ↩︎
「现代文化使货币与个人价值之间相距遥远,使得货币的意义越来越不能与那些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相提并论。」齐美尔《货币哲学》 p.290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296-p298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03 ↩︎
「高级水平被拖下水沦落的程度比低水平擢升的要大。」齐美尔《货币哲学》 p.311 ↩︎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p.8.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44 ↩︎
「要想有劳动货币,劳动就必须创造出可互换性……这又只能经过简化劳动才能实现。」齐美尔《货币哲学》 p.343 ↩︎
「生活的组成部分日渐转变为手段。」齐美尔《货币哲学》 p.347 ↩︎
「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性……最终拥有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形式与规范。」齐美尔《货币哲学》 p.351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85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60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63 ↩︎
甚至可以使得「劳动者不再拥有劳动」齐美尔《货币哲学》 p.370 ↩︎
「主体及其产品间逐渐疏远。」齐美尔《货币哲学》 p.373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74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76 ↩︎
「现代人与周遭环境的关联通常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他越来越远离同它最亲近的圈子,目的是凑近那些曾经离它比较近的圈子。」齐美尔《货币哲学》 p.387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82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419 ↩︎
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p.11 ↩︎
齐美尔《货币哲学》 p.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