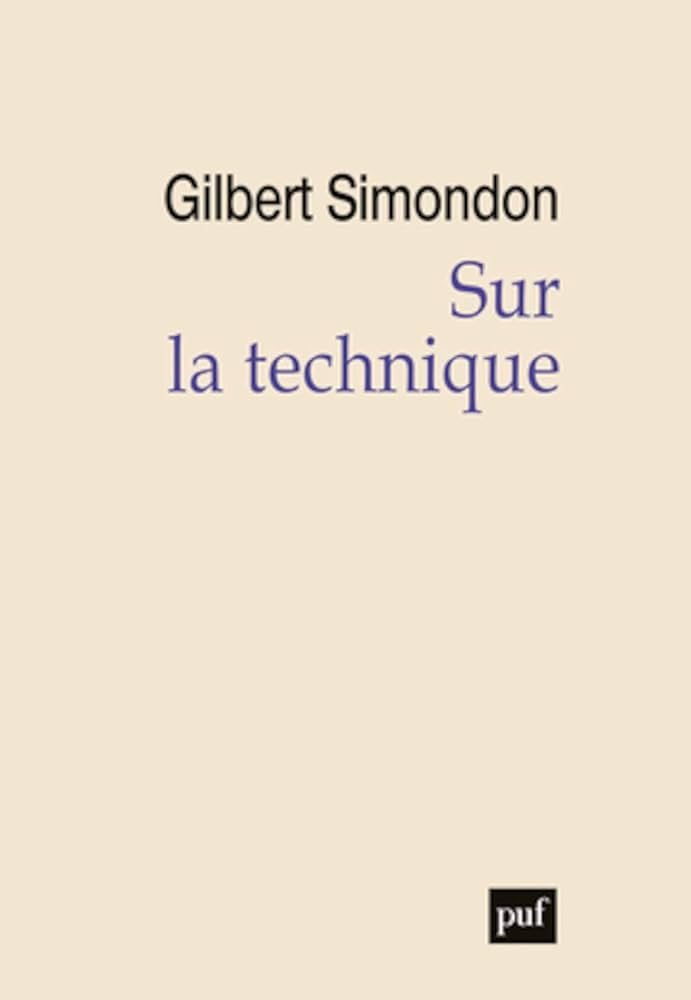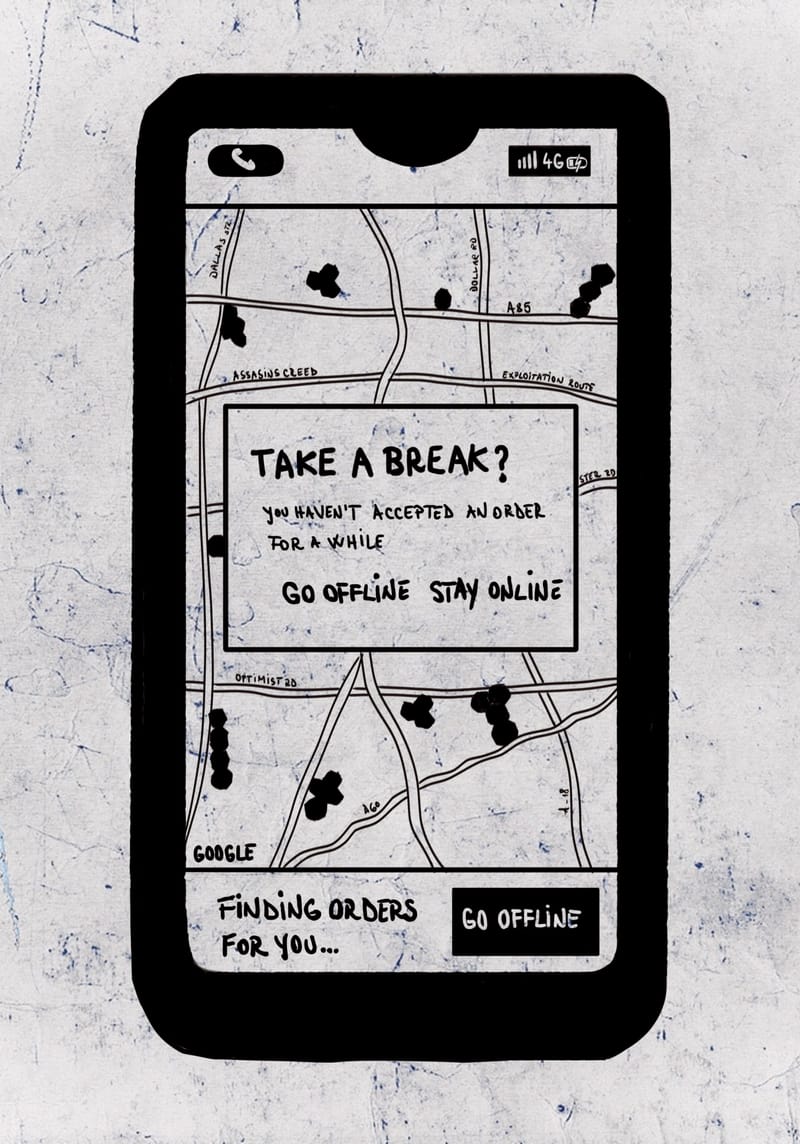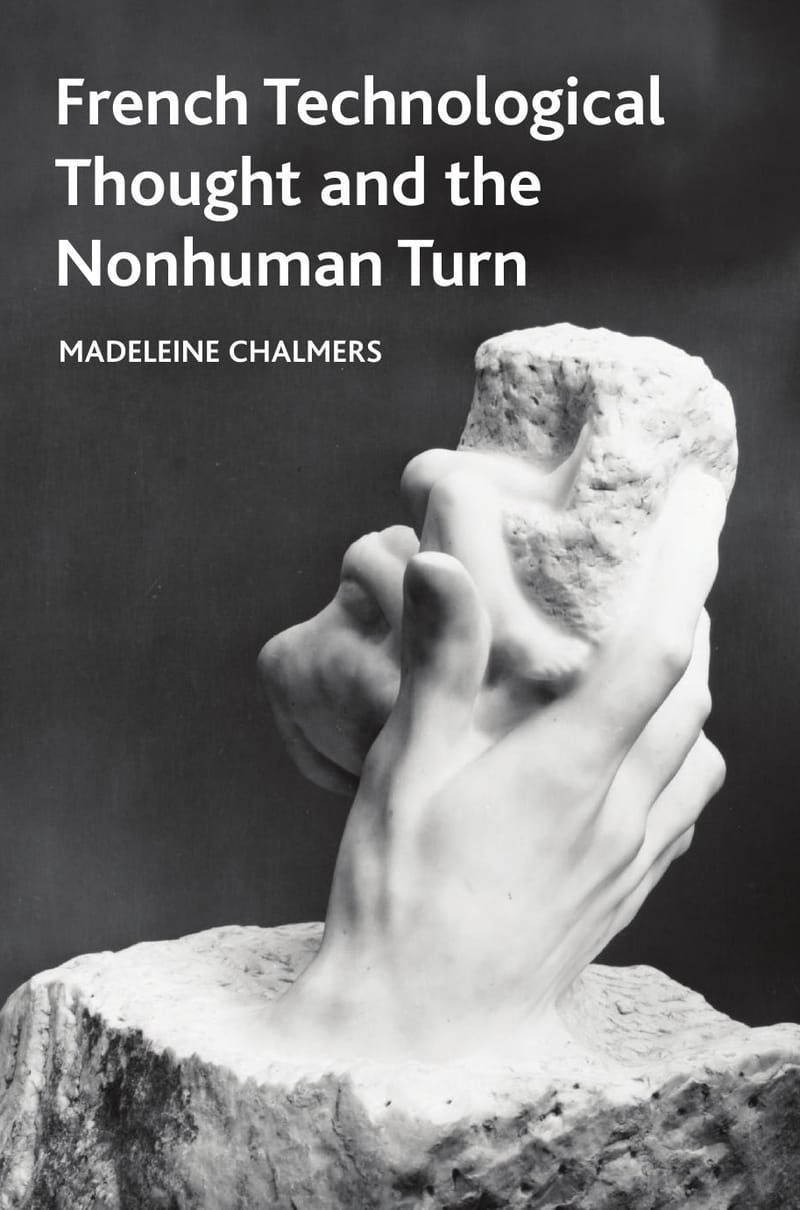导论
技术性(technicité)存在于操作中,也存在于这些操作所产生的事物中;构建一个技术物需要技术操作,但某些技术操作却只是用来生产艺术品或建筑物(如粉刷墙壁、给画布上清漆、配制艺术铸造用的合金)。产品脱离最初的操作者(艺术家或生产者)的能力,意味着所生产的事物开始了一段自由的历程,这段历程既包含了穿越时代而存活和传承的机会,也面临着沦为奴役的危险;或者在一种更为根本的矛盾性层面上,人类活动可能在其作品或产品中被异化、被封闭,如同被结晶化一般。当作品源自一个受制约的操作者或操作行为时,它会通过效能的反馈来驯服操作者:在由操作者、作品以及操作者与成品之间的所有中介现实所构成的往复共振系统(système réverbérant)中,存在着转导(transductive)关系和递归因果(causalité récurrente)关系。
当一个技术物是可分离的时,它才算被生产出来;在其他文化中,人与事物之间的这种分离也存在着不同于可售性的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遗传传承,它需要学习和知识的连续性,否则工具的功能意义就会丧失。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可售性是这种解放最普遍的形式,这种解放发生在事物被生产之时,也就是说,事物既被构建出来,又脱离了构建者,就像年轻人被生育出来,然后在确切意义上被成年人教育。在这个关系具有多元决定性(surdéterminé)的宇宙中,处于自由状态(这并不意味着自主性)的技术物被赋予了一种相当于自发性(spontanéité)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其所处的人类群体的主导文化中表现为被认可的品质:声望、经济价值……这种暂时的、次生的自发性越强,事物就越具有事物性,越容易从其生产者那里分离,越独立于使用条件。但是,正是在这种相当于自发性的特质显现时,规范性(normativité)的问题随之产生:技术产品的事物性特征或许只是技术存在物状态的一个限度,即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其存在方式,也不应该必然被视为其本质的组成部分。
技术产品一旦在社会宇宙中获得自由,就会提出有别于劳动和生产问题的问题。这些属于技术产品成为事物后的自发性存在的特有问题可以归为三类:使用、历史性特征、技术性的深层结构。
A. 作为使用物,技术物涉及分配、维修、转售,因此在生产者、经销商、使用者之间存在着各种依赖关系,这包括了与国外市场、老化、事物价值变化(新品、过期、过时、古董、极为稀有)相关的特殊方面和表征。技术存在物成为事物,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物质性,也是因为它被一层社会性的光晕所环绕;没有任何事物是纯粹的使用物,它总是部分地被多元决定为社会心理的符号;它使其使用者归属于某个群体,或使其所有者归属于某个阶级;它也可能将人排除在某个群体之外:在我们的文化中,用锤子钉钉子既不是贵族的行为,也不是女性化的行为。
B. 作为历史现实,技术物包含着隐含的信息:它等同于对特定存在方式的接受或拒绝。一辆老式汽车不仅仅是客观现实,它还是一种将过去插入现在的特定方式,可能是为了「震惊资产阶级」(épater le bourgeois),就像学生们有时用五颜六色且写满字的汽车所做的那样;也可能是一种混杂着怨恨的贫困表现,体现在那些破旧、保养不善、缓慢且在更快的车想要超车时毫不着急靠边的疲惫车辆上。除了这种审美主义或对习俗的挑战,除了这种攻击性的抗议之外,老式汽车还可能带来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旧赞美,或者成为见多识广的鉴赏家(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英国)的珍贵收藏品:汽车,就像一件乐器或家具一样,进入主人的住所并在那里静止不动以供观赏。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物被视为社会地位和人类态度的符号。某个印度土邦王拥有五十五辆汽车。四五年前,电视机在摩洛哥曾被狂热地销毁。英国贵族故作姿态地表示不拥有电视机,实际上却把它安装在仆人房里,这使他们能够优雅地与下层人同流合污。在法国,资产阶级圈子里,人们经常声称是「在朋友家」看了某个电视节目。
技术物的历史性特征可以通过拓扑学分析来研究。当一个技术物随时间演化时,它会发生分化,我们可以看到同心区域在其中形成。最内层区域是最纯粹和最高度的技术性区域:在演化的终点,它几乎完全摆脱了文化的多元决定性。最外层区域则是最纯粹的文化性区域;它几乎没有技术性,对于功能区域来说,它相当于有机体的衣着。最初,在汽车领域,发动机的长度需要引擎盖有相应的尺寸,这既是机器力量的标志,也是人的社会声望的标志。但是,发动机随着气缸从直列式改为V型布置,然后是顶置气门、压缩比提高和转速的增加,能够在减小体积和质量的同时提高功率。然而,作为社会符号的引擎盖保持着其威望性的角色,它虽然让出了长度但却获得了更多的宽度。这种功能的分离,也是区域的分离,导致了一种组合:一个巨大的引擎盖内藏着一个小型发动机,或者转变成行李箱。
有时,技术物的专业化区域之间会产生冲突,难以相互兼容。一个车辆的空气动力学外观可能与真正的空气动力学特性相去甚远;一些技术上的纯粹主义制造商有时会因为追求真正的空气动力学效果而不是「空气动力学形态」的刻板印象而令客户不悦:比如霍切奇斯生产的格雷瓜尔(Hotchkiss-Grégoire)汽车和雷诺 Frégate 就是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所有那些过度发展(hypertélique)的附加装饰和「外部器官」(phanères)上,它们增加了汽车的自重,损害了空气流的无湍流状态。挡风板无疑是最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东西;然而,这个配件却符合人们对空气动力学的社会原型认知。汽车在个性化的同时也在社会化,它扮演着一个角色,通过位置、速度、颜色、光泽、噪声帮助驾驶员扮演他的角色。一辆东方君主的汽车会装饰金银饰片。
技术物的二分裂变,造就了一种技术性的狂热和一种社会象征性的狂热,这并不是唯一的演化途径。有时,一种「技术显现」(technophanique)的炫耀部分地在美学相遇中调和了这两个区域:某些精密钟表会突出展示一个金色的、闪闪发亮的摆轮游丝,它在玻璃罩下缓慢摆动,显得格外华贵;齿轮也是可见的。
C. 技术物的实用性和历史性之区分完全没有穷尽其现实性和意义。有些技术物就像纪念碑一样:它们具有价值多元性和多元决定性。想要把金字塔解释为实用性的建筑,或者把它们呈现为法老傲慢的表现,都是走错了路。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意象与象征》(Images et symboles)中更深入且更本质地将它们呈现为中心,按照神圣性的结构将三个基本空间区域联系起来。这也是我们必须用来真正分析技术物的方法。在那种将这些事物视为器具(海德格尔使用的术语)的实用性之外,在那种简单且表面的阶层归属或地位象征之外,我们必须努力发现一种技术性的意义,就像米尔恰·伊利亚德努力在意象和象征之下发现神圣性的意义一样。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这正是我们将要提出的假说——技术性不能像神圣性一样构成一种文化的基础。技术性和神圣性之间当然没有同一性,但技术性的结构和神圣性的结构可能同构。圣埃克苏佩里在《夜航》中问道,为什么印加人要把巨大的石块运到山顶上来纪念太阳神。但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要建造艾菲尔铁塔,在它还没有用处的时候。后来,它变得有用了,用于测试那些本身还没有用处的技术,比如在万神庙和艾菲尔铁塔之间首次建立无线电报联系的时候。在第三个阶段,同一座铁塔直接变得有用了,作为观测台、航空信标的支撑,最后作为发射天线的支撑。最初,在某些技术物的产生中,实用性和社会象征性只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方面。这些事物首先具有一种直接的人性现实,一种恰当的文化性。实用性和象征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的占据现象,有时甚至是降格现象。这种占据现象在神圣性模式的历史中也并不罕见:某些需求、某些群体可以占据技术性的形式,就像占据神圣性的形式一样,并将它们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使它们部分地失去其文化意义。
技术性和神圣性有着共同之处:意象或结构的多声性(plurivocité)和多功能性(plurifonctionnalité)。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简化为单一客观意义的意象或符号就是去神圣化的意象或符号。同样,一个抽象的技术物,一个物质化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的技术物,而只是一个教学或科学的装置。艾菲尔铁塔之所以能在作为其建造契机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存活下来,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座塔。它不模仿任何东西,它具有其完美性和绝对的自我证成(concept matérialisé)。与艾菲尔铁塔同时代的摩天轮,以及布鲁塞尔最近的原子塔之所以没能存活下来,是因为它们只是物质化的概念;它们没有多元决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某种类型的技术物的接受或拒绝,几乎以道德选择的方式让人投入其中。那些试图从选择动机中把握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欲望的动机研究,实际上与那些基于经济标准的市场解释处于同一层面:相对于技术物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而言,其实用性和社会象征性仍然是表层的方面。
第一部分:使用物发生的社会心理学面向
通过饱和(saturation)的进步和重铸(refonte)的进步:科学与技术 - 文化与文明 - 文化排斥新的技术物 - 对排斥的防御反应:二分裂变、隐匿技术性(cryptotechnicité)、显现技术性(phanérotechnicité) - 仪式化与技术显现 - 技术显现、幼态延续(néoténie)、业余主义与原型事物 - 技术物与儿童;发生学技术 - 技术物与女性 - 技术物与乡村群体 - 技术物与处于孕育状态(situation prégnante)的亚群体。
通过饱和的进步和通过重铸的进步:科学与技术
使用物(objets d'usage)和生产技术的发生,在法国已经被勒鲁瓦-古兰——《人与物质》(L'Homme et la Matière)、《环境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现在需要延伸这项主要关于前工业物文明的研究,来考察工业物文明中技术物的发生。每种类型的事物,经过或长或短的发展历程后,都会达到一个饱和水平,这个水平使其图式稳定下来,并在经历了一段分化和差异化时期后产生类型的普遍趋同。这种趋同性演化当然可以通过交流或影响而得到促进;但它源于功能性本身在这个互为因果的系统(即事物)中的进步。技术物像公理系统达到饱和那样具体化。当达到功能多元决定性的最大值时,其图式就稳定下来。进一步的进步需要对图式进行重铸,也就是一项发明;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进步只能通过层次的改变来实现,比如通过它自身引发的一个新的科学理论:技术无限完善(可以说是线性完善)的障碍,是对科学知识的呼唤,要以这个障碍本身的意义作为「积累点」(point d'accumulation)为基础,这个积累点是在不改变公理系统的情况下所有可实现进步的收敛极限。即使佛罗伦萨的水工工程师们能够把圆筒车削到百分之一毫米的精度,即使他们能够制造出能产生完美真空的密封段或填料函,靠抽吸,水也不可能升得比 10.33 米更高:达到了一个上限;抽吸泵可以被视为一个饱和的事物。要发现一个新图式,就需要层次和结构的改变;伽利略提供的大气压力概念,就是这种改变的概念框架,是新的线性进步的起点。后来,对物质状态变化及其能量条件的研究——热力学的起点——使得从纽科门机器过渡到瓦特机器成为可能:这里不仅仅是进步,而是图式的重铸。
文化与文明
要实现显著进步就必须重铸图式,这种必要性解释了为什么在每个社会群体内部,技术物中包含的图式与文化的其他要素具有同质性。在技术变化缓慢的时期,一个文明的文化内容和技术内容是相适应的。但是,当技术发生变化时,构成文化的某些人类现象的变化速度和程度都不如技术物:法律制度、语言、习俗、宗教仪式的变化都不如技术物快。这些缓慢演化的文化内容,从前在构成文化的有机整体中与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形式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现在却成为了部分悬空的符号性现实。于是形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缓慢演化的文化形式的伪有机体,只能被已不复存在的技术形式所平衡;另一个是具有微弱惯性的新技术集团,看似错误地摆脱了一切文化意义,显得「现代」,而缓慢演化的形式则被归类为「古老」的现实。这种从现实的活跃中心向着过去和未来这两个相反维度的相位差,至少在法国,在「古老」的标题下留下了比「现代」标题下更多的要素:这个多数倾向于把自己视为组合(ensemble),并把自己呈现为文化,而实际上它只是文化的符号,是通过对一个受制于发生和分化的原始独特现实的分裂而获得的。这就解释了文化与技术之间出现的刻板对立,技术被降低到纯粹工具性的角色。文化被呈现为意象和原型的源泉,而技术则仅仅界定了文明。实际上,文化和文明是互为补充的相互符号,只有它们的重新统一才应该被视为大写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族志学家所说的文化意义。大写的文化,包含并统一了小写意义上的文明和文化。在文化内部发生的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时间相位差和质的分化是由技术的快速变化引起的危机现象;这种变化暂时打破了文化的同质性和有机统一性特征。社会心理学(psychosociologie)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一个目标可以是研究重建一个文化的有机统一性的条件和手段,以一种更高级和积极的方式。事实上,存在着一些次要的和消极的手段来虚幻地维持这种统一性,即否认文明的文化特征。这种防御性努力可以比作一个精神病患者对个人统一性的部分重组。就像一支被击败和减员的军队,无法保卫一个大型营地,就退缩到这个原始营地的一角并草草加固 (fortificate)一样,处于分裂和危机状态的文化退缩到缩减的文化领域,退缩到古老性中,将技术遗弃给外部力量和混乱。
文化排斥新的技术物
然而,在我们称之为古典的时代,这种时间相位差并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是技术被排斥和驱逐到堡垒之外。当然,文化分裂为文化和文明的现象可能在文化内容发生变化后出现过,但技术并非注定处于外部,处于文明一方:当罗马的古老文化在征服希腊后被希腊文化渗透时(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技术总体上保持不变,这无疑是因为罗马的技术并不逊色于雅典的技术,而语言和艺术则受到了新的影响。与我们今天在法国发生的情况相反,恰恰是这些语言要素(哲学的、艺术的)被排斥了,而技术则提供了文化永续的要素,构成了堡垒。西塞罗使用希腊词时只敢带着歉意;他对待艺术的态度有点像我们「有教养的」对待技术物的方式:我们知道它们存在,与它们打交道,但我们知道要统治它们,不让自己被它们支配。相反,同一位作者在《论演说家》(Orator)中借用了一个关于小麦发芽和生长阶段的冗长而艰深的隐喻。在其他情况下,是航海家的技艺为他提供了应用于治国的心智图式、规范和解释原则。农业、航海、战争艺术这些罗马人的主导技术,提供了心智图式、具体范式、词汇,最终成为一种隐含规范性的源泉:这些技术,以及它们使用的特定事物(犁、马具、盾牌、壕沟、诱饵),都是文化的材料,它们的稳定性使它们能够将那些在今天被视为文化内容的形式排斥为文明。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今技术物被视为文明内容的事实是其最近变革的结果:它们被排斥不是因为它们的技术性,而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新的形式,这些形式与作为文化的有机体中已存在的结构异质。这种排斥对一个人类群体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滋养了一个累积因果(causalité cumulative)或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米尔达尔(Myrdal)在美国研究的黑白种族歧视领域的情况。
对排斥的防御反应:二分裂变、隐匿技术性、显现技术性
打击技术物的排斥标准是什么?最持续的标准是:为了进入文化的城堡必须戴上面纱或伪装;这面纱并不能造成幻觉,但它维持着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离,甚至可能成为优雅的契机——变得文化化——就像女性在教堂中戴的面纱一样。汽车用引擎盖遮掩发动机,用散热器格栅遮掩散热器。这种强制的羞怯有时允许完成度、制造的细致程度或材料选择相对退化。1930年那些经过抛光、镀铬的大型散热器,无论是导风型、尖拱形、梯形还是椭圆形(霍奇基斯),都已经高度文化化并让人能辨认出车型,但自从被格栅遮掩后,就变成了低矮的黑色块体;格栅承载了文化的过度负载,这几乎是它唯一的功能。我们已经指出了汽车发动机和引擎盖之间的这种二分现象,而摩托车的气缸长期保持可见;发动机作为可见事物正在从两轮车辆中消失(小型摩托车,最近还有辅助动力自行车,所谓的「豪华」型号配备了带有鼓风机的整流罩)。通常,显现技术性的事物被视为实用性的(例如,发动机水泵、发电机组、耕耘机、某些拖拉机都有暴露的发动机),而隐匿技术性的事物则有可能被引入文化的城堡。人们经常把一些特征当作残留物来对待,而这些特征只能由事物的隐匿技术性地位来解释和证明。某些电暖器用红色灯泡模拟火焰,灯泡放在风扇叶片后面,造成光亮变化和移动的反光:这里并不是壁炉中火焰的残留,而是对效果的积极追求,需要添加额外的装置。某些收音机被设计成酒吧的样子,另一些像写字台,还有一些像书本,有些甚至像是一个装有箍的酒桶或醋坛。此外,隐匿技术性的事物有时会刻意地、炫耀性地揭示和展露自身的某个有限部分:这个象征性的部分通过文化化而承认自己的技术性。1930年前后,某些赛车配备了引擎盖外部的排气歧管,经过镀铬,排列整齐,高度可见。特殊处理的排气系统仍然是跑车的文化化特征标志:自由排气是发动机功率的显现技术性表现;在某些竞赛用摩托车上,人们在排气管末端添加喇叭口,让轰鸣的加速声传得更远;当然,它们的存在或多或少真诚地被性能相关的论据所证明。但它们的使用似乎更多地属于技术显现而非理性的技术学。
仪式化与技术显现
这种被认可和文化化的技术显现,是技术物在将其排斥的文化中重获一席之地的途径:事物通过一种富含意象和符号的仪式化重新进入文化的城堡,就像被排斥的、被衣着遮掩的性特征在优雅着装的文化化仪式中重新显现一样。优雅的着装是一种选择性的着装,它赋予性特征中的某一个以特权并凸显它,通过其多元决定性的特征,也就是通过单一要素代表整体的能力,赋予它只有意象和符号才具有的力量。一件优雅的外套是一件选择并展现某种女性「模式」的衣服,作为整个机体和完整人格的被感知的意象和符号:它是选择性和象征性知觉的工具。同样地,汽车的仪表盘集中并呈现了一些功能特征;它们通过仪式化来展现这些特征;仪表盘的魔力来自其技术显现的特征。仪表盘、控制面板或控制测量设备的呈现方式最常见的是沿着技术显现功能的路线;工业物美学的一个几乎本质的方面就是组织技术显现:当细节属于被选择来实现技术显现的事物部分时,它们都被多元决定为意象和符号。以指示灯为例:当然,它具有一个原生的单一功能意义,即指示电压或电流的存在;但除此之外,它还是技术显现区域的信标,是功能存在的符号,它指示一种在场和现实性。一个没有指示灯的复杂技术物看起来死气沉沉且荒谬;与事物的交流始于对指示灯的感知把握;它有点像在听我们说话的对话者的目光,或说话时看着我们的目光。这种技术显现功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制造商的名称通常重复出现在测量设备的面板上。测量设备制造商的名称也被铭刻在最具技术显现性的部分,也就是测量设备的表盘上。这种铭刻是仪式化的,并服从于功能需求:在飞机最重要的测量设备的表盘上,不能在有意义和有用的指示(刻度、单位、指针)之外添加无感知用处的指示,比如制造商名称。但一个制造商,积家(Jaeger),通过在其高度计的哑光黑色表盘上用亮黑色字母刻写「积家航空」(JAEGER AVIATION),解决了信息理论和仪式化之间的兼容性问题。「积家航空」这个符号只有在某个角度,当光线反射在其抛光表面上时才能被读取。对于飞行员来说,在正常照明的飞机中,更不用说在无光的驾驶舱中,当测量仪表只通过符号和指针的发光而显现时,制造商的名称虽然铭刻其上,但却是不可见的。
被文化认可的技术显现的存在使得与技术扩张相关的艺术形式得以诞生。摄影和电影部分地从工业物中获取其灵感源泉和素材:石油钻探——弗拉哈迪(Flaherty)的《路易斯安那故事》(Louisiana Story)——核裂变研究、天然气开采。但这些面向大众的技术显现比起那些面向业余爱好者、狂热者、鉴赏家这个有限群体的技术显现来说,选择性较低且定义不那么清晰。这些选择性低的广泛技术显现重新找到了前技术的原型,并从有限的技术显现中获取养分;科克托在评论一部关于核研究的电影时,将辐射计数器的氖气指示灯比作龙的眼睛。科学奇幻——「科幻」(science-fiction)小说、未来主义电影——通常是选择性有限的技术显现的契机。
技术显现、幼态延续、业余主义与原型事物
此外,被文化认可的技术显现可能是重建文化统一性的一条途径,因为它们具有那种特征性地呈现给儿童的文化内容所具有的开放性、扩展性和通过内部增生而发展的能力。就像玩偶对儿童来说是女孩的意象或符号,而不是客观的女孩一样,代表火车头的玩具也不仅仅是火车头这个事物,而是一整类可发展的技术存在物的意象和符号。玩具具有原型性,它包含着一个意象。那些缩小模型,这些真正的艺术品,这些精确性的杰作,几乎算不上玩具:它们与真实技术物的关系如此精确,以至于部分失去了其象征性和想象性力量。它们更多地吸引成年人而非幼童。在对技术物的每一类热情中,这些业余爱好者,这些具有幼态持续特征的成年人,都被驱使着回归到所谓的「老式装置」:无线电爱好者们会时不时地(带着一种秘密的喜悦感和仪式感)回到反馈检波器的装配,甚至回到晶体管收音机的方案,比如用锗二极管重新制作;他们感受到了向某种力量献祭、回溯本源的感觉;他们把这些装配方法传授给那些想要入门的年轻人。儿童和业余爱好者,以及更普遍地说,所有转向技术物的主体,都在寻找原型并理解技术显现的意义。
技术显现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张力,这种张力赋予它们文化价值,与史诗氛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骑士在危险紧张的战斗场景中与自己的宝剑或战马之间的关系,在那种将生命和荣誉置于考验之中的情境下,飞行员与他的飞机之间也有着这样的关系——尤其是更具原型性的早期飞机——正如圣埃克苏佩里在《夜航》中所表达的那样。同样,在《白衣人》(L'Homme au complet blanc)中,年轻的化学家就像一位身着白色铠甲的骑士,抵抗着所有诱惑以拯救他的发明。面向儿童或青少年的文学作品也体现了这种联系;在《丁丁历险记》中,至少有两部作品包含了技术原型事物以其孕育力(prégnance)、威望和庄严呈现的段落:这就是《奔向月球》和《月球探步》。特别是在第一部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对火箭出现的巧妙铺垫。在故事的第一部分,人们谈论着火箭,参观车间,遇见不同的人。火箭在这整个历程中无处不在,却又不可见。正是在主角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的时刻,突然间,在一个机库的转角处,对于主角来说,也是在翻过书页的那一刻,对于读者来说,一枚巨大的白色和红色火箭以其绝对的垂直性完整地展现出来,占据了整个视野和整页篇幅。在它面前,就像在一座巨大的雕像前一样,人类渺小如蚁:这就是情节的核心(nœud de l'action)。
在仪表盘的仪式化中尚显次要(mineure)的技术显现,对于那些尚未形成消极的文化防御态度的具有幼态持续特征的人来说却变得至关重要(majeure)。诚然,我们不能仅仅基于仪表盘、测量刻度和指示灯来构建一个技术的世界。但这些仪式化可以被视为可逆的交流和信息传递途径:它们首先使技术物能够以某些特定形式被文化所接纳,并与人类及文化内容进行交流;它们也能使人类越过文化的界限,进入未经仪式化的技术物世界,就像完成仪式的入门者跨越神圣领域的界限一样。作为仪式化的技术显现是文化与技术性之间的中介(médiatrices),它们有能力在两个方向上建立交流。
技术物与儿童;技术发生学
对于技术物来说,与童年和青春期的关系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通过游戏来理解事物会在这个事物中唤起一种原型力量,使其成为一个存在物而不仅仅是一个事物。在人类身上无疑存在着印记(Prägung 或 imprinting)的可能性,这种印记特别是通过游戏来实现:通过游戏把握的事物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接受发展、分化和丰富的文化范畴的源头。仅仅因为一个人或一个人类群体经常有机会将某种类型的技术物用作器具,并不足以使他们真正认识这些事物,更不用说达到构成印记的那种原初的、不可逆的联系层面——按照洛伦兹(Lorenz)和廷伯根(Tinbergen)在心理学中使用这个词的方式,用来描述某些本能行为现象。印记所给予的事物认识既不是归纳性的也不是显性概念性的。它是对图式的把握,而且不是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可能实现的;它需要一种特殊的注意力,一种特殊的觉醒,这些主要在非成年的存在中才有可能。然而,要使印记有机会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技术物上实现,这个事物必须被包含在儿童所经历的情境中。在这样的情境中,事物和主体是同一个情境的动态往复共振组合的组成部分,它们有着相同的生成,相同的瞬时命运:它们形成一个功能单位,相当于一个有机整体。原初的非二元状态(adualisme primitif),富含着可能的参与,是这种印记的基本范畴。在印记情境中的幼童,不仅仅是看到或听到一辆汽车:他就是汽车或卡车,他自己发出发动机的声音,通过参与,他就是发动机;他刹车,他加速,这意味着他在给自己刹车,给自己加速。玩火车的儿童自己就是火车头或车厢,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待在火车里。技术运作的图式被活生生的有机体所扮演。之后,这些图式可以被概念化和客观化。但它们首先是行为的、操作的图式。这种与事物的关系比使用或所有权的关系更为原初。狼孩四足行走,在吞食之前会嗅闻食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包含着技术物遭遇的文化中成长,能够把握某些源自技术的行为和运作图式,并将它们保存在自身中作为原型的基础,这使得日后能够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隐含的、被体验的熟悉关系和直觉理解。
成年人的思维中,科学的因果概念确实能够解释这个或那个装置的运作。但此时技术物被理解为科学原理的应用;它被间接地、抽象地认知,缺乏那种建立参与性的原初功能亲和性(connaturalité)联系,这种联系相当于一种兄弟情谊。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必要给儿童提供的玩具,与其说是火车或汽车的精确模仿品,不如说是能够运作、具有自身存在的实在物。特别是工具,必须是有效的、真实的,与成人的工具仅在尺寸和重量上有所不同,以适应儿童的能力。然而,在一个旨在重建文化与文明统一性的「行动研究」层面上,我们只能指出这种寻求印记意图的教学后果。人们通常认可儿童的「手工劳动」,因为它们被认为能发展智力;这也许不错,但智力并非一种无差别的、整体性的官能;手工劳动必须由更广泛的技术教育来补充,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前工业物文明。
对每类技术物的印记把握是否存在对应的年龄层次?这是很可能的,但很少有"技术发生学"研究对这个主题进行过系统性研究。1953年和1954年,我们在图尔男子中学的实验班级中,在教育性手工劳动的框架内,尝试在不同年龄层次建立技术练习。事物的使用可能先于印记的形成:当给八年级(quatrième)的学生一个无线电接收器和发射器时,他们对远距离传输的人际互动方面比对设备的运作更感兴趣;他们互相交谈,说说笑话或打趣。较年长的青少年则关注接线、天线和运作:他们正处于形成印记的年龄。同样,八年级的学生倾向于轻视一辆旧汽车或一个晶体收音机;他们的分类仍然停留在社会层面;其中一个学生,在听完某个汽车装置的工作原理解释后,问这个原理是否也适用于 Facel-Vega,一个对图尔资产阶级来说极其高贵的汽车品牌。
根据这些教学探索和实验,印记形成的年龄阶段似乎如下:四岁之前是建模、剪切、磨削、粘合,以及一般的手工劳动。四至六岁是火的技艺,包括金属熔化、铸造和使用烙铁焊接。六至十二岁是机械装配,然后是发动机,热力学装置。十二至十五岁是电气装配,十五至二十岁,直至成年,是电子学和自动化,以及无线电和电视。皮亚杰在研究空间概念时注意到的倒置现象,即在个体发生(développement ontogénétique)过程中出现与历史顺序相反的顺序(在科学发展中是欧几里得空间,然后是投影空间,最后是拓扑空间,而儿童则遵循相反的顺序),在技术阶段的演进中似乎并不存在:儿童的理解能力大体上重演了不同人类群体中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最后阶段是处于最近的技术水平,这些技术目前正在完善中,并向成年人提出问题。
技术物与女性
在每个人类群体中,所有被支配的亚群体,而不仅仅是儿童,都会相对于技术物表现出一系列与支配亚群体不同的态度。在我们当前的西欧社会中,女性与技术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矛盾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它包含着重建文化统一性的可能性之一,通过减少文化对技术物的抵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排斥。
儿童的游戏是矛盾的:在被成人视为不严肃的程度上,它将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表现相关联的不利因素投射到所有技术显现上;它保持在边缘。但正是在这种边缘性中,它实现了与被排斥现实可能接触的条件。儿童在发展并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中,将他在原始游戏中实现的印记引入文化圈。同样,女性的社会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技术物贬值的契机,这些事物可能被当作奴隶的装饰品和半魔法式的地位标识(prestige),如果不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被支配者的受气包的话。罗马讽刺文学给我们展现了一位优雅的女士命令人鞭打她的一个奴隶;在此期间,她在试穿衣服;鲜血流淌;行刑者问是否可以停止鞭打;这位女士没有回应,继续试穿其他衣服和装饰品。类似地,我们曾看到一位女学生在集体郊游时开车,她在男性同学面前故意粗暴地操作离合器和变速器,以展示客体化的女性气质。在另一场合,我们遇到两位参加汽车拉力赛的女士:一辆车发动机出现故障;另一辆车用保险杠推着它。发生故障的车辆的发动机布满厚重的机油污垢。我们的讽刺报刊充斥着对这种刻意而夸张的漫不经心的评论:用起动杆挂手提包,等等。仅仅这些有意的疏忽被视为一种态度并成为粗俗玩笑的素材这一事实,就表明它们源于一种劣势处境:每个处于异化状态的存在都会反过来造成异化。
但是,很多时候,救赎(rachat)的条件要求最好和最坏同时存在或具有同等可能性。重要的不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对技术物的破坏性;重要的是她面对这个事物并非中立;她可能使其沦为奴隶;因此她也可能通过将其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并解放自己来解放它。在厨房和餐具室这个次要的、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开始了女性与技术物的某种结合:诚然,家用物品仍然是标识地位的工具,以或多或少奢华的方式呈现在搪瓷外壳之下。然而,作为家务操作者的女性与这些技术物一起工作;她调节它们,组织它们的交换;事物和主妇构成了一个可能成为印记基础的功能单位。诚然,广告和信息销售渠道充斥着关于机器是奴隶而女性是女王的神话,这对重建文化的统一性并不有利。但工作情境本身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认为它将成为生产、广告、市场净化(assainissement)的源泉。从家用技术物到普遍技术物,存在着可能的连续性途径,一种非异化的人类态度可以从家庭条件上升到普遍条件:在西欧国家,继技术物与儿童的关系之后,它与女性的关系将是行动研究的第二个关键点。
技术物与乡村群体
更广泛地说,我们可以假设在每个被支配的亚群体中都存在一个关键点。我们已经提到了年龄群体和性别群体。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地理和职业群体,特别是在法国,考虑相对于城市群体处于劣势地位的乡村群体。「乡民」(pagani)的劣势是一种复杂类型,因为它概括了多重文化方面,其中曾经存在宗教方面:从前,乡民是异教徒,落后于来自罗马的基督教化;如今,他们仍然落后,在城市人口「去基督教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去仪式化」的同时,继续遵守宗教仪式。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着装、语言也可以提供标准并构成文化特征。一个普遍的刻板印象认为农民比城市居民「落后」;「落后的」这样的形容词相当经常地被用于农村人口。然而,在技术装备领域,我们发现关于乡村世界的情况与我们在儿童或女性处境中观察到的那些矛盾情况相同:乡村世界被支配,但这种处境提供了遭遇技术性的机会,导致技术物进入文化领域。作为被支配者,乡村世界吸收和使用城市居民的废弃物:过时的汽车在乡村销售。旧的豪华轿车在农民手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它们可以拖拽相当重的负载。在其他情况下,它们被改装,后座被替换成小卡车的货台。这种二次使用被视为一种堕落,以至于某些生产豪华汽车的英国公司强制购买者不得将车辆用于实用任务;这些公司只有在调查买家的名誉之后才销售。我们的经济有一个相当典型的特征:在汽车领域,城市车型种类繁多(某些还通过配件「个性化」),却没有一个适应农村条件的车型:人们暗含地假设农村条件是通过城市条件的退化而获得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农村条件有其特定方面,特别需要更高的离地间隙、四轮驱动、带防滑钉的轮胎,以及低速时更大的减速比。某些公司,如雷诺国营工厂,有时会制造农村车辆,特别是草原车型(Prairie);但仅仅在广告海报上展示一辆载着穿工作服的农民和戴头巾的农妇的汽车,或者展示一个装有小牛的拖车,并不足以提供一个适合农村生活条件的完整方案。事实上,这种车辆与其说是严格响应农民需求的车型,不如说是军用车辆——也就是沙漠(Savane)车型——的民用版本。它的油耗和宽度都令人望而却步。面对这种缺失和不当适应,我们看到了农民特有的车辆出现了,那就是拖拉机,它适应了农村条件。尽管有「拖拉」这个名字,拖拉机不仅仅能够牵引。它是一台多功能的传输机器,成为农业的基础机器;这台携带工具的机器可以耕地和收割;通过其发动机,它可以通过动力输出装置驱动固定设备(锯木机、压榨机、搅拌机等等)。此外,拖拉机是一种能够适当运输货物的车辆(可以在后桥附近固定一个悬臂式货箱),经常还可以在挡泥板上载人。作为车辆,拖拉机的特点是能够在泥泞或岩石的路面上,或者在陡坡的小路上安全通过。城里人认为拖拉机是农民标识地位的工具;事实上,一个农场拥有拖拉机是其能够「腾飞」(décollage)的条件,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台适应农业的传输机器(machine-transfert)。而在农村领域,与作为技术物的拖拉机的关系是人与技术物的完整关系的典范,富含原型和规范力量。那些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小型耕耘机的效益可能高于拖拉机的经济学家们,忽视了拖拉机作为农业领域基础传输机器的原型特征。
技术物与处于孕育状态的亚群体
最后,除了稳定的亚群体之外,每个人类群体都包含着临时或过渡性的亚群体,在这些群体中人与技术物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在儿童、女性、农民案例中所呈现的那些关系有相似之处。比如船员与船舶之间的关系,或者飞行员与飞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赛车手与他的赛车之间的关系;在危险的紧张感面前,在机器与人构成的功能统一体面前,那些非本质的威望、社会参与的方面都消退了。这种统一性由海军的荣誉准则所象征,要求船长与其船只共存亡;这样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孕育的,或者说是完全饱和的。人的命运和事物的命运在彼此之中往复共振(réverbérant)。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耦合,因此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被人性化、个性化、受洗礼、赋予人名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也可以理解,当一家大型航运公司解除了我们最著名的法国船只之一的武装,并将其出售给一家外国公司,而这家公司要将其交给一家电影公司,用于拍摄船上的火灾和爆炸场景时,职业水手们爆发的愤怒浪潮。这艘大船只有在被除名之后才离开法国港口,当它驶入迷雾中前往那个无法返回的国度时,港口的所有汽笛长鸣相送;船员们致以最后的敬意。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年老,在长期职业生涯结束后就将其出售。也许一场新闻宣传就足以使这艘「海上圣伯纳」(saint Bernard des mers)免于受辱的结局。但只有海员这个亚群体表现出深深的愤慨,因为只有他们以隐含和体验的方式知晓人与船舶之间的关系。购买或出售的经济行为并不能穷尽事物的完整现实;它并不能赋予对事物的全部权力。就"法兰西岛"号而言,如果大众传媒之一为这艘船只的命运发声,认为通过集体募捐来回购这艘邮轮并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并非不合理,比如作为海军浮动博物馆或训练船。但需要作家、记者或演说家的工作才能让广大群体像小群体一样思考和感受。要使这种救赎成为可能,就必须为它和类似事物完成贝切·斯托夫人为黑人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所完成的工作。对价值和责任的意识觉醒可以从一个小群体开始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古希腊禁止砍伐橄榄树。也许有一天,在某些文化中,破坏技术物将像杀死奴隶一样被禁止:这将是一个新的法律范畴的诞生,与保护动物的法律范畴平行,而后者目前正在发展中。这样的法律可能具有范式价值,并为更广泛的现实领域提供可用的规范。在自动化领域,优化(optimisation)这样的概念标志着规范性的诞生。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来自最初分离领域的不同价值源泉,能够聚合并使迄今未知的价值论(axiologiques)倾向渗入文化。收集和阐释这些规范性倾向将是旨在通过重新统一文化与文明来重建文化统一性的行动研究的第四个关键点。
因此,由于将文化与文明对立的二分现象而被文化排斥的使用技术物,部分地重新进入文化,要么是通过分区(文化化区域在拓扑学上包围纯技术性区域),要么是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局部的技术显现(仪表盘)或普遍化的技术显现;这些与印记相联系的技术显现出现在永久性或临时性的被支配亚群体中,这些亚群体可能基于年龄、性别,或职业和处境:这些是为实现文化统一而进行的行动研究的基本关键点。
第二部分:技术物的历史性
历史性与超历史性(surhistoricité) - 文化物与技术物:事物的异化与劳动的虚拟化(virtualisation) - 超历史性的程度 - 开放的技术物与封闭的技术物 - 手工艺物的开放性 - 工业物的封闭性;人的编码与机械编码 - 工业物生产作为开放性的条件 - 微观技术尺度与宏观技术秩序。
历史性与超历史性
我们应当以广义来理解「历史性」一词。米尔恰·伊利亚德将文明的历史性与文化的无时间性(intemporalité)对立起来;确实,作为使用物,技术物具有某种历史性:它对应着特定人类群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需求。然而,作为器具的器具并不是最直接地与某个时代相连。可以说,事物作为器具的历史性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性,它被一种文化的历史性所强化和多元决定,后者由一束针对事物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类态度产生,这个事物被标注日期也标注着时代。一个埃及凳子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日用家具使用。在工具领域,说一个工具没有日期并不完全正确。然而,当我们在壁橱里发现一把锤子或一把锛子时,我们可以在更换手柄后使用它们,而不必过多地询问它们的制造日期:我们很清楚它们是古老的,但我们说不清它们是在 1880 年还是 1910年 左右制造。事物越复杂,越与使用的社会方面相联系,它就越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性。一辆自行车比一把锤子有更精确的时代性。一辆汽车比一辆摩托车有更具决定性的时代性。一整套家具属于一个明确的文明,而一个凳子却可以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社会心理的历史性(historicité psychosociale)与技术物作为使用物的历史性相互扰动(interfère),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心理的历史性部分地独立于作为使用物的历史性。
作为使用物的事物会因磨损、腐蚀、变形而经历一个渐进的退化过程。在某些事物上,比如显微镜,如果维护得当,这个过程几乎不会发生。然而,一种光晕效应从那些会退化的事物开始,笼罩了所有技术物,使人认为它们会随时间失去使用品质。几乎所有军事用途的制造品都标有制造日期。诺伯特·维纳引用了一位英国作家的观点,在他看来,一辆马车的完美境界在于车轮、弹簧、车厢和车辕恰好在同一时刻完全磨损:在复杂事物中,某些零件局部和隐蔽的磨损确实可能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可见但可以推测的退化过程视为使用物随时间贬值的基础之一。
文化物与技术物:事物的异化与劳动的虚拟化
然而,前述特征更接近于老化而非真正的历史性;要形成历史性,制造日期必须成为人类某种明确态度所指向的事物。这种态度确实存在,但仅仅用老化和磨损造成的退化很难解释它。我们也可以援引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普遍信念:一个新近的事物可能比一个古老的事物更加完善,这种信念是普遍的,即使在进步缓慢的领域(例如光学)也是如此。实际上,首先是人类态度决定了事物的历史性,而不是严格的使用性能标准。而这种将事物视为过时或落伍的态度具有选择性:它主要针对技术物。小提琴被认为会随时间变得更好,因为它是文化物。一本古书并不比一本新书价值更低:它参与了文化的无时间性。一位地毯商声称他销售的地毯在被长期踩踏后会变得更加美丽,这使它们被归类为艺术品。人们也谈论雕塑、家具的铜绿......所有这些表征可能都只有微弱的客观基础,但它们显示了人们在文化物的演变和技术物的演变之间建立的隐含对立。
技术物的本质历史性在于它确实是一个事物,是可以被出售、购买、交换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文化堡垒中:它可以移动,可以从生产它的群体、从导致它出现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它就像一个种群(population),不仅仅作为原型和通过其图式而存在,还以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一定数量的实例的形式存在。它是或可能是异化的载体和原因,累积因果(causalité cumulative)过程的基础。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已具体化的且可从生产者身上分离的人类劳动。费尔巴哈描述了在神圣与人之间发生分离时的异化过程。马克思接过了异化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资本与劳动关系中的剩余价值运作。但还存在着第三种与前两种不同的异化形式:它产生于技术物的这种解放,技术物在找到使用者或购买者之前就从其生产者那里分离。当一个手工艺者为了在自己的工作室使用而制造一个事物,或者当这个手工艺者执行一个明确的订单时,就不存在事物的异化,因为事物从未与生产者或使用者分离。但在工业物生产中,生产与使用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事物的生产并不基于潜在使用者明确和特定的预先愿望(vœu préalable);产生了一个中间时期,这对事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定义了事物的异化状况:大量事物,一个事物种群在市场上等待着可能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作为购买者出现。
如果事物没有被售出,没有被选择,它就失去了其技术性特征;它所具体化的劳动被清除,变得好像无效且未曾发生。换句话说,在这种待售事物的状态下,事物还没有被完全承认为技术物:除了生产行为之外,它还需要第二个选择行为,这个行为将其认可为值得购买的事物。生产的事物的现实性被还原为技术命运的潜在性;它本身并不具有其存在和目的性的自我证成;我们可以说它被可售性的条件「虚拟化」(virtualisation)了。通过它,生产性劳动本身也被虚拟化;它失去了一个现实性的层级。由于生产的事物的状况反作用于生产劳动(对所有生产劳动,既包括资本也包括狭义的劳动),这种劳动变成了一场赌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这里启动了一个循环因果(causalité circulaire)的过程;工业物生产是一种被虚拟化的生产,这种虚拟性的状况笼罩着生产者和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物技术物就像一个奴隶,因为奴隶的处境包含着这种虚拟化:奴隶只有在其主人允许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最初,当人从其环境中分离,被贬为奴隶时,他发现自己的存在和正当性取决于另一个人:这种对另一个人及其目的的依赖性就是奴役的本质。当撒丁人在市场上太多时,人们会说「撒丁人待售」,他们被用来喂食七鳃鳗。同样,一整系列从其生产环境中分离出来的技术物可能找不到购买者,被贱价出售用于回收某些零部件:这种违背其固有目的性、违背其发明和运作图式的低度使用,使它们变质并将它们湮灭于荒谬之中。然而,即使它们并非活物,它们仍然包含着某种活的东西的结晶:用于生产它们的人类劳动时间,以及使其得以构想的发明努力。购买者通过其选择或拒绝的权力,拥有着赋予这些物质化的人类姿态集合生或死的专制权力,就像那些统治者民众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的拇指手势,决定竞技场中战败的角斗士的生死。由于所有事物都必须经过市场,一种光晕效应从一类事物扩展到另一类事物,最终所有的劳动都因此被虚拟化。
在这里建立的累积因果现象导致了一种不同于费尔巴哈或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类型;实际上,它更接近于费尔巴哈描述的异化(通过神圣化的异化)而非马克思描述的异化(通过剩余价值的异化);这很可能是因为技术性和神圣性之间存在着同构性的方面,正如我们将在本研究的第三部分中试图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描述的异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力量和角色的分配,这种分配与人类群体相重合:在异化状态下的劳动是无产阶级、无产者群体的存在方式,而资本则是资本家的存在方式;由此产生阶级斗争和可能通过革命解决冲突的阶级斗争思想;由此也产生了否定性的工作和通过剩余价值运作而加剧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辩证演化的观念。社会革命可以被呈现为对异化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异化的施行者和异化过程的受害者被分配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很可能代表了第一次工业物革命时期异化现象主导结构的意识觉醒和表述。这种异化形式可能仍然存在。但第二次工业物革命的后果带来了另一种异化,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的区别在于,在同一个个体内部,人作为预期的购买者,虚拟化了人作为技术物生产者的劳动。在同一个人身上,购买者的功能异化了生产者的功能;购买者的功能,更普遍地说是使用者(utilisateur)的功能,使人与生产的物品产生距离,并且通过递归因果的运作,与生产功能本身产生距离。人作为购买者,为技术物创造了一种超历史性,这种超历史性作为异化过程,相当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剩余价值。在特定的生产领域中,这种超历史性越增加,生产就越成为技术外部规范和要求的奴隶,这些规范和要求仅仅旨在通过新的细节使产品更受欢迎;由此导致了这种笼罩技术物并使其生产负担过重的超历史性的膨胀,以至于危及根本性的进步。生产者成为超历史性的生产者,就像他们是技术性的生产者一样;作为购买者,他们要求自己生产出这种不断增长的超历史性边际。
这种超历史性创造了障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辆汽车过时的速度比磨损的速度更快;要使用一辆过时的汽车,就必须克服某种社会障碍。超历史性的普遍存在使制造商必须成为超历史性的生产者,要相当频繁地创造新型号,这相当于主动分割对应于技术性真正进步的结构改革,有时甚至推迟这些改革: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对比,即限制技术结构改革的马尔萨斯主义与外观变化的大胆奢靡之间的对比;超历史性集中在外部区域的层面上,也就是在技术物中相当于人类衣着的那个层面。这个外部区域也是仅仅依靠纯自然和历史因素就最快降级的区域,无需超历史性的介入;但超历史性通过选择易损的颜色、油漆、搪瓷来表现自己,这些很快就会退化,就像服装领域的时尚求助于易损的布料或罕见且不稳定的色彩一样。如果一辆汽车被设计为纯粹的技术物,没有超历史性,它就会像快车车厢一样用不锈钢板制造。
一个事物的超历史性可以通过其使用时间的倒数来衡量,可以只计算到第一次降级(déclassement)为止,也可以计算总的使用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铁路设备具有历史性,但很少具有超历史性。非常古老的蒸汽机车(七十年)仍然被用作车站的调车机车。服役三十或四十年的机车并不罕见;在这里,历史性表现为载重量和功率的增加,这是牵引越来越重的列车所必需的条件。但一辆机车并不会真正地过时;它变得古老(archaïque),它显得像一个祖先,但它不会像另一个时代的服装那样被感知,甚至也不像自行车那样被感知,后者在近些年时不时地在滑稽游行中重现。
在某些最近发明且快速发展的领域,如航空领域,历史性表现为比铁路领域更快的技术变革;然而,这个领域几乎完全缺乏超历史性(除了客运领域,这是由于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这表现在旧型号可以与最新型号并存使用,而不会被打上耻辱的标记。最近,英国皇家空军退役了一种在上次战争期间使用的旧型飞机;这种型号的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机库时,面对的不是嘲笑,而是庄重的面容和崇敬,在其最后的飞行中,它受到最新型号飞机的护航。我们可以将这个由法国广播电视台转播的仪式,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国「法兰西岛」号邮轮在被出售后启程最后航行时受到的致敬相比较。在航运领域,时尚现象仅限于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s),且只涉及邮轮。在欧洲的某些湖泊上,仍然存在着桨轮船。一艘帆船完全不会被视为过时;三年前,德国海军的训练船中仍有两艘帆船;其中之一的「帕米尔」号已经沉没。帆船具有原型的价值,其操作被认为比蒸汽船对年轻人更具教育意义。最近,英国海军也重建了「五月花」号,仅出于安全考虑增加了雷达。
汽车与火车、飞机或船舶之间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购买时的选择现象:汽车是在呈现给可能的购买者之前就已经建造好的;相反,飞机、船舶、机车是在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距离小得多的条件下生产的。很常见的是,生产者以维修者、调试者、原装零件供应商的形式保持在场;使用者对生产者的信息反馈不会受到长时间的延迟;通常是使用者向生产者表明其需求:订单先于生产,而在汽车领域,订单跟随生产;它不能对生产产生调节作用,生产活动和使用活动构成的组合并不构成一个功能单位(unité fonctionnelle)。即使订单与生产同时发生,在汽车领域,订单也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订单,因为它不携带信息;它不强加特征;如果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那就是在超历史性附加物的领域:白边轮胎、颜色、装饰轮毂......这种在订单时提供信息的幻觉体现在「个性化」汽车的模式中,而这实际上是社会化和超历史化的。
开放的技术物与封闭的技术物
超历史性现象在技术物本身中如何表现?——通过封闭性(fermeture),这与纯粹技术产品中发现的开放事物特征相对立,后者不会成为异化的契机。封闭的技术物是在准备销售时就完全构建好的事物;从这个可能的最高完善时刻开始,事物只能磨损、退化、失去其品质,直到最终拆解并回归到零部件状态。这种封闭性(在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障碍)表现为一系列禁令,比如当设备的封印或铅封被破坏,或者在未经授权的品牌特许经销商之外进行维修时,保修就会终止。在某些情况下,事物的封闭性可能被呈现为完美的象征,成为一种声望性的广告手段,给某种制造类型蒙上一层虚假魔力的光晕。这种封闭性在工业物机器中比在家用设备中要少,尽管后者较不复杂且质量更加可疑;这是因为工业物机器是在从生产行为到使用行为的功能连续性语境中被生产和使用的:它保持可调节、可改进;如果材料生产的进步允许用具有更优特性的新零件替代旧零件,这种替代在工业物机器中通常是可能的,而在封闭事物上却无法恰当地进行,有时甚至不允许维修。开放的技术物具有幼态持续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处于建构状态中,就像一个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因此,开放的技术物比封闭事物具有更大的持久力。一辆机车比一辆汽车有更长的「寿命」,因为机车是为定期检修而制造;它可以逐件拆卸和修理,就好像它一直处于永久的生成状态(état de genèse permanente);在同样程度上,它具有显现技术性而非隐匿技术性;人们接受机车的连杆、滑块、曲柄可见,这使得它们无需拆卸就能轻易检查;机车上一个发热的轴承箱通常会在达到不可逆状态之前就显现出来。而在汽车上,一个同等的损坏通常会导致咬死或断裂。不过,最新的型号通过在最易磨损处使用可更换零件显示出一些开放性的特征:气缸衬套、悬挂系统中的减震胶块。开放事物的图式与封闭事物的图式根本不同:封闭事物的最优状态,就像那辆所有部件同时达到最终磨损程度的马车一样,是一种无需修整或干预就能提供尽可能长久使用的组织;所有这些部件在其共同的退化过程中是同质的。整个系统都趋向其终点,并将被整体抛弃。相反,开放事物必须在受变化影响的部件和不受变化影响的部件之间二分。永久性部件必须用材料和完善程度来执行,使其实际上成为永久的;它们对其他部件起着静态和不变条件的作用,例如支撑作用,其中磨损和必要的重新适应被减至最低。非永久性部件要么是根据任务多样性而更换的部件(如车床等工业物传输机器上的工具),要么是那些根据运作图式而将磨损局部化的部件。
技术物的这种开放性条件可能会引起混淆,但特别值得研究,正是因为它是我们所指出的那种异化类型研究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种条件在两种情况下得到满足:手工艺生产(production artisanale),或者高度发展和精良的工业物生产。当生产仅仅是相当粗糙的工业物性的,也就是面向大规模商业传播的系列化生产时,这种条件就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仅仅产生出磨损后就该扔掉的事物,受制于退化的事物,或者说纯粹文明的事物(objets de pure civilisation)。
手工艺物的开放性
手工艺生产对应着可调节和可修理的事物,因为零件之间的适配是在建造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事物依次生产;零件之间通过可逆程序(用木栓连接、螺栓连接、楔形件固定)相互适配。修理行为重现了生产行为的姿态和程序。干草收割后,人们更换耙子的齿,像最初制造整个工具时那样削制它们。人们重新锻造或加固锄头、斧头;重制犁铧。许多修理程序重现了最初制造的条件,构成了制造的重现:例如焊接开裂钟的程序就是这样——比林古乔(Biringuccio),《火工艺术》(Pyrotechnie),1550年;引自弗雷蒙(Frémont),《铜铸造的演变》(Évolution de la fonderie de cuivre,),巴黎,1903年——这是使用特殊形状炉子对原始熔化然后浇注的局部重现;钟就这样被部分重铸。手工艺物保持开放是因为手工艺行为贴近可加工的材料(matière ouvrable);手工艺的目光(regard artisanal)把事物把握为可改造的、可延展的材料。一些零件更多地以其材料而非功能来命名:刨子的铁件,木工机器的铁件。某些手工艺者通过只购买某些零件来建造他们的机器,比如轴承、齿轮、发动机。在法国市场上,可以找到尺寸较小的手工艺型木工机器,通常被业余爱好者用来建立个人工作室。这些机器被设计为本质上开放的:受磨损的零件(铁件、轴承),或可能断裂的零件(用于锯木的轴端),使用者可以轻易更换,且由制造商提供。此外,这些设备被设计成可以从一些原始要素开始,通过附加和适配逐步完善(例如,平面刨可以接收一个补充装置,将其转变为可拆卸的厚度刨)。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性的手工艺条件通过业余工作的方式和形式重新进入我们的习惯;有时,这种重新引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非本质的文化因素:声称木制木工机器优于铁制木工机器,这是在利用对手工艺者古老木工机器的记忆。对真正的手工艺者来说,这种木制构造提供了更大的开放可能性,因为它允许手工艺者自己根据需要建造这些机器,扩大它们,修理它们。对购买现成机器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与其说是技术开放性,不如说是手工艺氛围的重建(atmosphère artisanale),与其说是从生产到使用的真实连续性,不如说是氛围的统一。然而,这样的构造程序融入了手工艺类型的一般经济中,将事物的生产和使用功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技术物开放性的首要条件。
工业物的封闭性;人的编码和机械编码
相反,封闭的工业物是使用那些要求预先构想组合、且导向一个无法被修正、延续、重现的组合的装配或组装程序的事物。焊接、粘合、铆接、压制成型构成了不可逆的操作。建造之后,如果事物在测试中没有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特征,它就被淘汰,被报废:规范变成了某种「公差」(tolérance),而不是在发生过程中逐步伴随规范性关切的事物或已构成的子组合各个连续部分的渐进适配;在手工艺制度下,规范性在发生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引导它并使其自我适应,而在全面且广泛的工业物制度下,规范性主要在制造结束时发挥作用。工业物生产通过试错而不是渐进修正来进行。它通过性能标准来控制整体。封闭事物的生产对应着大规模生产所特有的信息获取类型。产品是一个单位,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却封闭、本身不可分离、不可分割、不可修理。此外,通过机器实现的生产使产品的结构远离了个体的和人性的干预和修正方式。用螺丝和螺母装配对人来说很容易;对机器来说,这可能比一段很长且规则的焊接要复杂太多(infiniment plus complexe),而人类操作者难以实现如此完美的线性焊接。然而,人类操作者更容易拆开一个螺丝和螺母的装配,而不是拆除一段长焊接。人和机器达到可比较的结果,但通过显著不同的方法。计算机使用一种对人来说不实用的计数系统(二进制编码)。对人类组织来说简单且熟悉的操作,比如绕过家具打扫房间,如果要通过完全机械的方式来实现,就会带来巨大的问题。通过完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方式建造房屋会比用同样方式打扫它们更容易。当人面对一个按照工业物生产操作的最佳组织方式构建的事物时,他遇到了一个预先的解码(décodage)问题,这使得这个工业物机制的作品对他来说难以解读。在电子领域,修理印刷电路比修理手工布线更加精细。感知和动作互补。通过这种需要预先解密(décryptage)自动化机械实现相应结构的必要性,在通信框架内显现出工业物革命启动的异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它的存在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手工艺生产可以显现为文化统一性的保证。人们通常断言工业物生产压垮了人,因为它生产的事物不符合人的尺度;实际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工业物生产使人困惑,因为它让人面对那些对他来说并不立即清晰的事物;作为使用物,它们离他很近,但它们对他仍然陌生,因为它们不容易被解读,而且人类行为不再能找到其介入点。除了焊接、铆接和保修封条的物质封闭之外,还有一种更本质和更具异化性的封闭:事物不再可解码,不再作为构建操作的结果而可理解。人们无法在其中读出构建操作。它像一门外语一样陌生。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物会被当作机械奴隶对待。人们不试图理解奴隶的语言,只是试图从他那里获得特定的服务。对于处于异化状态的技术物,仪表盘和控制器足以在特定工作框架内进行实际使用操作。这又是一个有利于建立特征于所有类型异化的循环因果过程的基础:不再可解读的事物打消了维护的关切;使用者期望它能尽可能长时间地无需修整而运行,在这段时间之后,事物将被整体报废。这个作为封闭整体而被使用或拒绝的事物也作为整体而被选择或拒绝,这是基于可见但外在的,因此通常是非本质的特征或方面,它们属于社会心理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须关注整体特征,而可以毫无损害地对人是否能解读具体运作实现方式表示冷漠:生产操作与可能的后续使用之间的交流完全中断。取代这种已变得不可能的交流的是对意见、动机的研究,以及一种强调整体特征的广告活动,这是按照一种半生机论的神话学:一辆汽车被说成是智能的;一台大型号的电视接收机据说比安装更紧凑的另一台「呼吸」得更好。然而,关于技术图式,意见研究和广告活动不能被视为生产和使用之间的良好信息渠道。它们的存在产生了一种掩蔽效果,加剧了产生异化的分离。
工业物生产作为开放性的条件
然而,规模化工业物生产(production industrielle de série)在使用和建造之间造成分离,在生产领域给予技术图式研究以充分自由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准备着一种生产与使用之间新的、处于更高层次的交流条件。这种交流的工具显然不是那个被可售性条件虚拟化的、现成的、封闭的事物,而是构成它的可分离零部件(pièce détachée)、构成元素。
在手工艺物中,严格来说,没有零部件,或者至少没有可分离的零部件;零件被切割、加工以适应其他零件,并在必要时通过连续的修整来纠正它们的不规则或偏差,零件就像一个器官,带有所有其他器官的印记,因此它是这个特定身体、这个特定有机体的器官,而不是其他身体或有机体的器官。在手工艺物渐进生成的末端,有机性将部分与整体联系起来,使它们不可转移(non-transférables)。相反,在工业物建造中,每个组合都是由系列预制的子组合(sous-ensembles)组装而成,因此这些子组合必须是可互换的,因为在一个整体的组织中某个零件与另一个零件的相遇是随机的(aléatoire):在 2000 个活塞中,有 500 组四个活塞的组合,可以装配500个四缸发动机,但这些组合并不是预先确定的。每个活塞都可以与任何其他活塞互换。在这里,可分离性存在于预制元素的层面上;它通过其功能、其特征融入整体。它可以被单独研究,被单独生产,单独演化。在电子装配中,可以用同类型、具有相同特征的另一个灯管(电子管)替换一个灯管,即使新灯管的形状和尺寸与旧的不同,也不会改变其功能。甚至可以用另一个采用不同技术图式的复杂子组合来替换一个子组合,就像在高频放大中用串联的两个三极管替换一个五极管的情况。在这里,具有开放力的是元素而不是整体。封闭的工业物技术物是一个虚假的整体,但这个虚假的整体包含着真实的整体,这些就是元素或零部件。
零部件的演化遵循着真正的技术规范(normes réellement techniques);它们比构成的事物要少得多地直接受制于虚拟化:电视接收机在几个月内就改变形状,但除了阴极射线管外,装配其中的变压器和灯管在几年内保持不变;出现的新型号通常可以替换旧型号,并带来更好的效果:在零部件方面,制造商关注连续性(continuité)。零部件的变化并不总是可见的;它们不必然对应于事物的整体类型的改变。最后几款标致 203 都装配了为 403 型号设计的差速器。
元素的解放使其能够变得具有纯粹功能性,具体化,因而得以完善。这是工业物阶段技术进步的基本条件。这种开放性条件又反映在作为整体的制成品上。具体化的元素,在其特征上变得稳定和明确,能够更广泛地互换,无需通过预先的选择和试验来挑选个体。只需要进行类型的选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技术物可以重新开放,不是通过调整和修整,而是通过更换工业物生产的零件。所有零件同时磨损的马车不再是最优:相反,磨损或断裂必须局部化,这样损坏就能以完全可逆的方式修复。电气装置中的保险丝是一个故意设置的薄弱点,目的是使损坏局部化,并通过完全更换保险丝而得到完全修复。我们可以设想开放的机器,在其中故意设置可触及的薄弱点,并预先准备易损的备件。使用开放机器需要一定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需要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越强,开放性就能越完整,这预设了更高水平的知识,和一种接受机器监控和维护的态度。然而,购买者当前对寻找封闭技术物的期待,有时使制造商走向有争议且具有欺骗性的简化之路;在汽车领域,出现了自动启动器和取消手摇启动曲柄;这些简化是表面的,因为它们赋予了一个间接装置(dispositif indirect)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在发生故障时无法由人类操作者来扮演;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事物的复杂化,尽管它们表现为仪表盘或附件的简化;它们加剧了事物的封闭性。此外,这些还与随车提供的描述文件精确度的显著降低相关。
最后,通过替换零件(pièces de rechange)具体化实现的技术物的开放性预设了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第二种类型的关系:生产者必须通过拥有必要零件的经销商网络在整个使用区域内得到代表。换句话说,除了技术信息之外,一种物质性的交流必须将使用者与生产者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创建一个技术性网络,就不可能有技术物真正开放性的展开。这是个基础性的条件,我们将在本研究的第三部分研究它。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对于特定类型的事物而言,这样一个网络的诞生预设了生产的工业物化发展,以及足够数量的相同事物正在使用中。整体性不再像在手工艺阶段那样位于事物层面:它在零部件中凝聚,并在遍布世界的零部件分配网络中扩展。
微观技术尺度与宏观技术秩序
技术物的超历史性的发展与事物在某个特定层面上的封闭性相关,这个层面恰恰是作为使用的实践层面的人的身体维度层面。汽车或电视接收机被要求在车辆或家具的层面上封闭,这些是人类尺度和使用的层面。但是这种作为整体被感知和操作的使用物的封闭性,并不导致子组合(零部件)或这些子组合的分配和交换网络的相应封闭。这正是工业物生产最重要的积极特征所在。超历史性的异化在人类层面上产生并集中于这个层面,从而解放了零部件这些真正要素的微观技术秩序,以及分配和交换网络的宏观技术秩序,后者是技术生产环境在空间上的真正延展,保持着与使用空间的接触。这种真实技术性载体的量级秩序的二分在手工艺物中不可能存在,因为手工艺物无论是作为劳动产品还是作为后续工具都处于人类尺度。事实上,事物真实技术性得以发展的层面,就是在事物中建立互为因果(causalité mutuelle)过程的层面。手工艺者通过基于自我调节和偏差修正的建造方式,在建造过程中的事物的整体尺度上考虑互为因果性,就好像他在建造一个有机体:既没有子组合的具体化,也没有作为网络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类技术物种群的具体化,因为对手工艺者来说,单位、发生个体化的物理系统就是人类尺度上制造的事物。相反,在工业物中,作为人类尺度事物的制成品只是一个组装体而非有机体;但是,为了使这个组装体运作,每个预制零件都必须自行满足此前手工艺方式下整个事物所满足的要求。可能的标准化体现了技术子组合的具体化过程。而一旦具体化,子组合在其适应和流通能力上就超越了使用物的范围:它进入覆盖整个地球的分配和交换途径,它供给着世界维度的网络,它可以通过组装参与多种类型使用物的构建或修理。
因此,在寻求文化的统一性时,不应该为工业物生活不符合人类尺度而感到遗憾。在工业物技术领域,恰恰是那些超出人类量级秩序的东西,以最少的超历史性负担而发展。工业物生产将技术现实从对人类量级秩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就像测量和观察工具的发展将科学从对人类理解手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一样。如果观察尺度仍然停留在人类尺度,科学会是什么样子?技术遭遇了与科学相同的情况:它们摆脱了最初的方法论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几乎完全自发且不可避免地赋予了发生在人类理解场域(空间场域和时间场域)中的现象以特权。从微观物理学到天体物理学的量级分化,伴随着时间尺度的分化,这种分化超出了人类平均测度的两端,出现了微秒和光年这样的新单位。空间尺度的分化在技术领域已经完成;也许我们还将看到时间尺度的分化的实现,这种分化在稳定子组合与注定磨损或断裂以保护其他零件的子组合的功能区分中已经初见端倪:一个校准良好的保险丝在几千分之一秒内气化,以确保那些安装后可使用二十或三十年的电机或设备的保护;保险丝的作用时间远短于人类有机体的时间。只有被超历史化的中观技术区域(zone mésotechnique)才保持在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尺度。
我们必须注意到技术物超历史性的显著社会心理特征。从某些方面来看,技术物与特定的社会状态相关联。就其速度、重量、消耗而言,一辆汽车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因为它具有历史性:它反映了它被制造时的技术发展总体状况和生产方式。只要它与这些它所适应的条件保持一致,它就能发挥其作用,也就是说,对我们的社会而言,大约十年时间。然而,实际上,除了社会条件的缓慢变化之外,还存在着更快速的社会心理条件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划分时间,将各个时代和时期切分为被感知为连续的、无交换和过渡的系统,创造了超历史性,这些系统像物理学中的绝热系统(systèmes adiabatiques)一样封闭在自身之中。不再流行的东西,就是属于一个被感知为已经过去的绝热时间系统的东西。同样的社会心理过程在空间中和时间中都创造了绝热结构;它们叠加在社会异质性之上并强化了这些异质性,就像超历史性叠加在历史性之上一样。
总之,文明的事物是超历史的、社会心理的;但并非所有技术物都被超历史化,而且在工业物体制下,超历史性并不涉及技术物的整体性,而仅涉及使其处于人类使用尺度的那个部分。然而,技术物的超历史性触发的异化过程并没有完全腐蚀或消除事物的技术性:这种技术性离开了中等量级秩序(ordre moyen),转而在微观技术层级和宏观技术层级上发展。文化统一性的重建将要求中间层级也被技术性所渗透,同时摆脱其超历史性的负担,这可能通过其他两个量级秩序的影响而实现。但是,要恰当地构想这种对保留给人类行动的量级秩序的影响,就必须研究文化和技术性的结构本身。
第三部分:技术性与神圣性
结构及其生成、退化和相容性条件的比较研究
导论 - 1. 附着于封闭技术物的虚假神圣性(sacralité)。自动化对应着处于不安全状态的个体的需求。事物的现代性范畴具有古老心理(paléopsychique)的基础 - 神圣性和技术性的平行退化;当代人在古老的魔法需求的驱使下才是现代的 - 2. 神圣性和技术性的同构性 - 真正的技术进步预设网状(réticulaire)结构 - 原初的仪式化;仪式化与网络化 - 神圣与技术的古老重合 - 神圣与技术的当前重合 - 神圣性和技术性在未来可能的相遇:文化的统一性 - 技术价值普遍性感知的到来;百科全书主义的意义 - 技术性和神圣性作为参照系统和信息编码 - 大规模人类群体层面的技术性 - 结论。
导论
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各种二元论相呼应:灵魂与肉体、无时间性与生成、古老性与现代性。但这里涉及的是存在于群体层面的二元论。按照米尔恰·伊利亚德在《意象与象征》中的说法,文明由那些能够被理性和概念性地认知的工具和内容的总体构成;现代人的特征在于,对他而言,文明已经超越了文化。自启蒙世纪以来,随后是科学主义时代,概念战胜了意象和象征,或者说战胜了神话。意象、象征、神话是一些表征,它们指向那些一旦被客观化就会失去其意义和实在内容的现实类型。意象、象征、神话指向一种现实类型,按照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范畴,这种现实类型不可能有完全理性的表征。参与范畴对于恰当地思考神圣性是必要的。荣格已经确立了原型的多元决定性特征:一个原型(archétypes)从来不是某个单一事物的概念或感知者;它是一个意象,因为它将多个情境浓缩在一个单一表征中。同样,按照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说法,存在着一种抗拒理性分析的表征类型,正是这种表征类型构成了文化的内容。科学的民族学和人种志学未能发现并通过恰当的表征转译文化的内容,因为科学关切只能还原甚至清除那些本质上具有多元决定性的内容。
然而,当米尔恰·伊利亚德将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神话的内容归于文化的庇护之下时,他却将技术性的表征和使用内容与文明的各种方面归为一类。在这一点上,他的做法与海德格尔相同,后者将技术物视为功利物(utilia)、器具,除了回应实践目的、人类需求之外别无其他本性。在这种将文化与文明分开的区分之下——这种区分为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所珍视,并被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以及人文科学的作者们(特别是汤因比)在未经重新审视的情况下普遍接受——可以读出一种防御性的规范关切:必须保护文化,重新发现文化,防止它被来自技术发展推动的文明浪潮所淹没。
然而,正是为了寻求重建我们希望完成的文化统一性的途径,我们有必要质问这种排斥措施是否合理:技术现实的结构确实与最真实的文化内容相对立吗?我们是否面对的是一个防御性的神话,最多只能与一个族群在面对不同族群时发展出的心理刻板印象相比,这种刻板印象甚至否认另一群体中个体的人性?我们希望避免神圣性及其代表者与技术发展,尤其是与技术完全整合进文化内容之间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在我们看来源自一个社会心理的神话。这种与虚假敌人的斗争在我们看来对神圣性本身有害。技术物太容易被当作替罪羊。如果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来自技术物,那么在通过仪式将我们的过错归咎于它们之后,把它们扔进海里就够了。但是,相比于让技术性和神圣性陷入一场战斗——其观众并不比罗马衰落初期观看基督徒在血染的沙地上与野兽搏斗的群众获得更好的净化——更好的做法是按照它们的真实本性来认识它们,这种本性不仅仅是它们的功用。从被诅咒的技术物中获得的轻易的净化作用无法重建已经分裂的文化的统一性。更好的做法是尝试不带偏见地发现技术性的真实结构和实在本质,看看它能给予我们的价值萌芽、价值论路线是否与神圣性有着深层的一致性。我们不是试图替代或削减神圣性,而是要表明在神圣性和技术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isomorphisme),这种关系在神圣性和技术性被祛魅之后,允许在社会心理领域中存在一种协同作用。我们将这种结构分析呈现为对神圣性和技术性的平行祛魅。
1. 附着于封闭技术物的虚假神圣性
自动化对应着处于不安全状态的个体的需求。事物的现代性范畴具有古老心理(paléopsychique)的基础
我们在米尔恰·伊利亚德那里发现的对立的动力无疑在于面对众多文明事物时所体验到的去神圣化感受,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技术物,或者至少是某些技术物,那些在文明前沿最引人注目并最直接受制于前文所述异化的事物。这些事物被赋予了一种低等的、零散的、分离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与人类寻求护身符和物神(fétiches)的态度相关。任何封闭的技术物,在其封闭的程度上,都呈现为提供一种它所包含和携带的特定力量;它是一个威望或魅力的事物,令人生畏,故意神秘和令人印象深刻。它知道如何保护其所有者,保护他免受危险;或者它像传说中的侏儒一样工作,无需监督。某支钢笔、某辆汽车确保商业成功。制造商和销售商知道如何捕捉存在于人类群体中的这种魔法饥渴(faim de magie),这种饥渴因个体所处的情境而异:对危险的恐惧、面对工作的沮丧、对商业或爱情失败的担忧、对优越性的渴望,这些不一定具有集体意义,而是具有个体意义。正是个体的倾向造就了这种魔法对技术物的附加。特别是,人们经常指责家用设备机械化了生活:但实际上是处于主妇处境中的女性要求洗衣机或其他机器在艰苦的任务中替代她,这些任务她担心完成得不好。童话故事给我们展现了过去时代的主妇们,被工作压垮,在劳作中睡着,被气馁打败;但是仙女在守望,蚂蚁或侏儒们在夜间来工作。醒来时,一切都干净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现代洗衣机之所以具有魔法性,是因为它是自动的,而不是因为它是一台机器。正是这种自动性被人们所渴望,因为主妇希望在她身边有另一个主妇,一个模糊而神秘的主妇,它是洗衣房的善意精灵,就像冰箱是现代厨房的精灵一样。对使用者的个体潜意识而言,「现代」意味着「魔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魔法暗含着自动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机械事物,而是为了实现这种使操作者获得一个分身的条件。在这种自发性自动化的功能中,它复制了人类的努力并确保成功,消除焦虑,其机械特征或作为技术物的存在并非不可或缺:洗衣粉可以被呈现为自己洗涤,并使如此洗涤的衣物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确保这种成功的洗衣粉不仅仅是一个东西,一种化学产品,而是主妇的朋友,它有一个名字,在感激之情中,值得「勇敢」的美誉。相应的心理范畴是对神秘品质的信念(例如,某种洗涤剂带来的一种与其他所有不同的特定白度)和笛卡尔曾强烈批评的印记种类(espèces impresses)。正是通过对古老心理欲望形式的回应,一个事物才是现代的,而现代性品质的真实内容则由古老的思维图式(schèmes archaïques)构成。自动化,这个如此困扰文化捍卫者精神的东西,由人类的焦虑感,由对失败和危险的恐惧放入技术物中。它不是一种技术必然性,而是表达了人类个体对责任的逃避,对工作努力的逃避,或对烦琐操作约束的逃避。这种魔法式的自动化是一种贫乏的类型,更多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一台自动洗衣机的「大脑」并不属于很分化或很复杂的类型。积累在汽车上的自动化装置属于同一类型。从人类动机的统一性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家用或汽车自动化领域经常将「大脑」与伺服电机混淆:自发指令和从属控制归入同一范畴,这不仅仅是因为部分同音,而是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将一个具有足够自发性的存在物用作人类的辅助物。
文化捍卫者面对这些自动机器的扩散所表现出的恐惧,这些机器既被奴役又具有奴役性,这种恐惧本身也是古老的:在最遥远的过去,人就梦想被其他存在物所复制,无论是动物、自动机、被赋予生命和受洗的雕像,就像布拉格的拉比(Rabbin de Prague)为戈勒姆魔像(Golem)注入生命能量一样;但是,在实现这个愿望时,人又受到看到所有这些力量反过来对付自己的恐惧的限制。他感到自己像个学徒巫师,处于不安全的境地。现代时期只有在人将机器构建为人的复制品时才能被赋予机械化人的力量:自动机是一个拟人(anthropomorphique)的作品,它的魔力来自于它与人的相似性。雕像(例如伊勒的维纳斯)、肖像、反射图像的镜子、对原始人来说的地上痕迹,以及对我们祖先来说的巫毒(voults),都具有这种魔力。魔法意图就在技术物作为自动机的制造的起源之处。不是技术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自动化,而是人向技术性要求一种魔法式的自动化,而技术性往往只能非常不完美且完全虚幻地提供这种自动化。自动化是对技术性的低度使用(sous-emploi),特别是当它必须是拟人的时候。原因在于拟人的自动化必须是多价的(polyvalent),有时甚至是普遍的,以模仿自发性,而技术运作要达到最优化,就必须高度专门化。我们的祖先要求独角兽的角在接触任何种类的毒物时都变黑,而化学指示剂通常具有高度选择性,除了一些整体功能,如酸碱性的检测,但这些还不足以定义食物的毒性,后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化特征,且有几种不同类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只有一个神话动物的角才被认为能够完成这个非常复杂的功能,这个功能只有从人类个体的恐惧角度来看才对应一个简单的范畴。同样地,家用自动机也无法实现,除了一些操作之外。
最后我们注意到,在特定情境中的自动化欲望构成了一个总体性需求,它获得了多种专门化的回应,其中一些构成了自动化的等价物:以罐头或冷冻产品形式准备食物使冰箱能够成为已准备好的食物的分配器。正是在这里,文明通过创造特定情境,迫使技术性屈从于其要求;这种对技术性的迫切需求的源头是个体对特定文明情境的反应。这种情境越是痛苦和紧迫,社会心理动机对技术性的回响(retentissement)就越强烈和专断。这就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个体——也就是说,女性——会向技术物要求最多的魔法力量(pouvoir magique)。
魔法性的技术物,注定要在特定情境中复制个体,是一个事物,也就是说,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分离的现实。正是在这个事物中,生产后的异化过程最完全地显现出来。事物的力量在购买时、投入使用时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条件改变引起情感冲击的时刻;当习惯的适应逐渐形成并让人感知到需要另一种帮助的新任务时,这种力量逐渐消退。然而,这个自动机事物是封闭的,无法完善,即使没有过早磨损,它也会失去其现代性特征,也就是魔法特征,即回应当前情境所产生的关切的能力。只有灰姑娘的马车,在舞会时刻敲响时由南瓜变形而来,才是完美的事物。最漂亮的汽车也只有一次是渴望王子的灰姑娘的马车。舞会归来时,马车重新变成南瓜。每个愿望都需要一辆新的马车。工厂取代了仙女。确信自己力量的战士不会为每场战斗要求一匹新的战马。他忠于他的坐骑正如他的坐骑忠于他,因为他的坐骑不是他的复制品:他与它构成一对(faire couple),他与它一起战斗,而不是通过它战斗。灰姑娘希望人们看到她在马车中;她需要马车就像需要毛皮凉鞋(sandales de vair)一样,为了被介绍给王子。她需要马车和凉鞋是因为她部分地是一个事物,一个待嫁的少女。马车和凉鞋确实是复制品,它们扮演了她角色的一部分:王子找到的遗失的凉鞋是灰姑娘的象征;只有她能穿上它,也正是这样她才会被迎娶。我们可以对神话进行分析,展示它们所表现的欲望如何存在于人要求技术物扮演的角色中。说我们的祖先接受步行作为跨越空间的合适方式是不正确的:飞行的幻想由来已久。「青鸟」(L'Oiseau bleu)在英俊飞行员存在之前就被想象出来了,七里靴早已跨越过我们祖先生活的乡村。
神圣性和技术性的平行退化;当代人在古老魔法需求的驱使下才是现代的
面对某些技术物的现代性中存在的魔法负担,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退化与神圣性的退化(dégradation)是平行的。非但不应该将技术物当作替罪羊,让它为现代人的神圣性退化负责,我们反而应该说,现代人以同样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时降格(dégradation)了技术性和神圣性。他在焦虑引发的情境中降格它们,当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或威望受到威胁时,当他感到自己丑陋、软弱、贫穷时。将要决斗而感到恐惧的人,当他让人对他的剑念咒语时,就是在降格神圣性。想要激发爱情而给心上人喝下魔法药水的女人降格了神圣性。出于恐惧、贪婪或野心而发假誓的人降格了神圣性。神圣性的退化在于整个神圣网络的碎片化,它失去了其有机的和宇宙的整体维度,而封闭在这样或那样的事物中,能像工具一样被搬运,能成为所有权、交易、销售、交换的事物:神圣性,这个宛如宇宙的东西,破碎了,与自身分离。在失去其有机存在(这种有机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等同或包含它)时,它异化了,它变得能与自身对立。神圣性的退化与其说在于其表征的物质性,不如说在于表征它的事物的分离状态、碎片化状态、可操作的流动性——勋章、护身符、图像。不应该撕裂长袍,不应该碎片化神圣之物,因为它本质上是宇宙和关键点(points-clefs)的网络,是中心的织物,这些中心在统一性—多元性(unité-pluralité)的结构中相互沟通,相互呼应,形成一种交流的多样性。
为了据为己有而从网络中分离出一个节点,,就等于摧毁了它作为节点的存在。碎片化的织物不再是织物,就像单个分子不能独自成为晶体一样,它需要同类的其他分子与之一起形成一个无限的、在每个网眼中永远重新开始的网状结构。神圣的时间本身就是网状的。它的结构是递归的(itération):一个神圣时刻,献祭的时刻,就像一个延伸向过去和未来的网络的时间网眼;在这一时刻中回响(réverbère)着所有曾经存在的其他时刻的记忆,它也是所有将要存在的时刻的预告。所有这些时刻通过时间相互沟通,像网眼一样穿越时间延展。当下的献祭回响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献祭:它是过去献祭的反映和未来献祭的预示,遵循着一种时间性和永恒性的形式,这就是永恒回归。在作为时间维度的神圣性中,一次献祭与另一次献祭的关系比与刚刚流逝的世俗时刻更近,即使这次献祭是在历史时间中一千年前完成的。神圣之物不会老化;它在时间上与自身沟通。它也不是古老的,因为它在每个实现自身的时刻中都是当下的。在空间上,神圣之物在神圣性网络中与自身相近。在大洋中央,在一艘船的甲板之间,伴随着机器的噪音和海浪的摇晃的宗教献祭,与世界上同一时刻存在着同样献祭的所有其他地方相连,按照神圣性的维度,它与这些地方比与任何事物都更近。神圣之物与自身存在着沟通。正是这种沟通在神圣之物被客体化、与某个事物或存在物混淆时被打破。
同样地,当事物在时间上(通过制造的结束和陷入可售性状态这个断裂)和空间上(通过将制成品与那些能让它获得永久再生、维持其完整功能意义的条件隔离开来的分离)被孤立时,技术的退化就发生了。技术性在将自身事物(s'objectivant)时退化,这是因为事物作为封闭的东西,一旦不再被维系在构成它的技术性网络中,就会变得古老化和退化。技术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它只有在网络中,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才能完整且持久地存在。时间上的网络化由事物的重新把握构成,在这些重新把握中,事物在其初始制造的相同条件下被重新实现、革新、更新。空间上的网络化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技术性不能被包含在单个事物中;一个事物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运作,在一个使它获得关键点意义的网络中运作时,才是技术性的;就其本身而言,作为事物,它只拥有技术性的潜在特征(caractères virtuels),这些特征只有在与系统组合的主动关系中才能实现。技术性是覆盖世界的功能组合(ensemble fonctionnel)的一个特征,事物在其中获得意义,与其他事物一起发挥作用。
2. 神圣性与技术性的同构性
真正的技术性是事物网络的特征,而不是单个事物的特征。严格地说,一辆汽车不是一个技术物,而是由公路网络、加油站网络、提供零部件和进行必要调整的服务站网络所构成的技术组合的一个要素。润滑台和汽车是互补的现实,不能孤立地思考其中之一;道路和信号装置网络也是如此。米尔恰·伊利亚德关于意象和符号所确认的内容也可以用来描述构成网络的这个技术性组合:存在着一个多元决定的现实,它不能仅仅在单一形式下被理解,也就是说,不能被客体化,否则就会失去其意义。一辆汽车只是复杂现实的一种形式,这种现实还必须从服务站、高速公路、制造工厂、汽车站、交通管理机构等形式来把握。同样地,一架飞机本身并不足够:它必须参照机场、航空无线电导航网络、燃料供应系统来思考。只要听听一架飞行中的飞机的无线电通话,就能理解它在活动期间如何持续与固定设施保持联系:从比利时飞来,经过马赛上空时,飞行员询问机场站是否能在布拉柴维尔加满燃料;几分钟后,通过地面赫兹电台传来回复。当一种新型技术物出现时,它会在一段时间内借用已有网络作为活动基础:最早的飞机使用营地或道路作为跑道;但一种特定类型的技术性只能以网络形式发展,而且是选择性网络,包含其通信途径和设施。表面上看似自由和孤立的火箭和卫星需要非常强大且数量众多的设施。发射一颗人造卫星需要覆盖整个地球的观测站网络,甚至赫兹无线电指令站的合作,这实现了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网络之间可能产生扰动(interférences),妨碍特定技术组合的具体化。例如,按照等高线布设的公路网络,具有缓坡和众多弯道,符合缓慢牵引负载的条件,如马拉货车。这个网络的存在便利了最早期汽车的使用,但它抑制了适合完善汽车的公路网络的发展;面对弯道这个主要缺点,缓坡的优势是有限的;频繁穿越居民区,这对于需要更换马匹或喂食马匹是有用的,但对于补给自主里程达 500 公里的汽车来说却是一个障碍。对于每个细节都可以做出同样的评论:在老式道路上,弯道坡度与弯曲半径的比例补偿了一个离心力,这个离心力对应的速度对于当前的汽车来说太低了。某种汽车是某种道路的象征(symbole),某种道路是某种汽车的象征。铺石路是马的象征,就像带纹的水泥是飞机的象征,碎石路面是汽车的象征。
真正的技术进步预设网状结构
在某些情况下,从本质上说,技术组合的具体化在人类使用者的尺度和范围之外的事物中进行。如果孤立地考察这个使用物,这个器具,它甚至可能看似在退步,而组合的真实技术性却在增长。一台配备了本地电池和呼叫发电机的旧式电话机,比一台为在中央电池网络上运行并使用拨号盘呼叫而制造的电话机更完备。用两台旧式型号的电话机,可以通过双线路建立通信:它们是完备的。一台使用中央电池和拨号盘的电话机如果与交换机隔离就毫无意义。然而,正是使用物的这种贫化(appauvrissement)使得自动交换机的增长和所有区域性及城际自动呼叫的发展成为可能。旧式电话机只是同类型另一台电话机的象征;新式电话机是整个供电和自动化系统的象征。电话技术性存在于由网络和设备构成的组合中;它不包含在单个事物中;我们甚至可以说,随着整体系统现实性的增加,它越来越少地包含在事物中,事物失去了它的密度、它的内部现实。每个器具作为事物的存在越来越少,作为象征的存在越来越多。即使器具事物完全没有改变,技术性也可以在网络层面上增长。电话技术的进步并不是在用户设备层面实现的;它继续在电信系统中实现,而用户设备并不需要改变。在无线广播和电视领域,发射机网络的完善使得接收机的简化成为可能:使用物不是技术性的容器;它只是网络中的一个点。如果公路网络是为汽车而建,就可以生产几乎不需要悬挂和减震器的汽车。
在铁路领域,现实不是火车,也不是单独的机车。没有网络的火车会被限制为目视行驶,就像战争期间,当信号装置被破坏或不可靠时的情况一样。像闭塞系统这样的装置,让司机能够控制他的列车与同一区段内其他列车的空间关系,增加了铁路组合的技术性,就像雷达和无线电控制增加了航空导航组合的技术性一样,而无需对机车或飞机做任何修改。
此外,技术网络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连接的可能性。如今的航海钟表的精确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们在 19 世纪时必须达到的精确度:船只可以使用无线电时间信号和无线电测向。同样,飞机和船舶之间的信息交换创造了技术网络的新网眼(mailles),特别是在搜寻遇难者的情况下。电话系统到处都带来了频率标准。
最后,电力生产和配送网络,通过大功率互联线路,在技术上拉近了生产点和使用点的距离。如同电话系统的情况一样,这种网络的发展使得使用设备得以简化。一台三相异步电机,比起旧式的通用电机更加集成到网络中,也更加简单、更加坚固,并提供更好的效率。网络技术性的提升表现为集成的使用物的简化,这种简化既是组合向饱和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结果:技术物在基本零部件层面上达到饱和(所有自动电话的拨号盘必须产生相同的矩形电压频率,而发电机可以产生相当不同的频率和电压),在作为集成网络(réseau intégrateur)的组合层面上也达到饱和,在网络的网络层面上更是如此。但人类尺度的使用物并不达到饱和,因为它比零部件更大却比集成网络更小:它既不具体化也不饱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仍然可以屈从于社会心理影响,并且容易被多元决定。在工业物型文化中,直接的技术物只是微弱地渗透着技术性:电话机可以是黑色或白色,可以是壁挂式或台式,而不会改变电话技术的本质技术性。那个可能成为摄影棚配件的电话听筒,用来让明星或商人在艺术镜头前摆姿势,不能被视为代表纯粹状态的技术性。
因此,我们不应该犯这样的智识不公,这将是一个方法论错误,即在技术领域中认为一个孤立的社会心理事物具有代表性,而在神圣性领域则关注其存在的本质层面,也就是网络的完整维度。因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性将显现为纯粹的文明之物,由物质构成,处于感性和实用需求或短暂欲望的层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同样的不公也可能损害神圣性,如果从部分社会心理化的神圣事物或可敬事物出发来分析神圣之物:这就是当人们把神圣性当作迷信来对待时所做的事,将其碎片化为事物,并试图从这些事物出发重构它。把技术性当作纯粹的物质性来对待,把对它的研究当作唯物主义的特征,这就是在隐含地接受与那些只想在神圣性事物中看到迷信证据的人相同的偏见。
原初的仪式化;仪式化与网络化
真正的神圣性与真正的技术性之间存在同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原始技术的研究中推测得出,就像米尔恰·伊利亚德在《铁匠与炼金术士》(Forgerons et alchimistes)一书中所做的研究那样:大量原始技术操作都被仪式化和神圣化,尤其是那些处于可能性和知识极限的操作,比如金属熔炼。动物或人类的献祭经常标记着这些原始技术的关键点和基本时刻,这些时刻同样重要(虽有所不同),就像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将要发生的首次载人航天一样:这也将是一种献祭,它将唤起与数千年前同样类型的情感,就像当时,在那熔炼难以进行之时,中国铁匠的妻子投入高炉之中——于是熔炼得以完成。
仪式化或许比纯粹的神圣性和纯粹的技术性更为原始,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存在着一个原始单一结构的二分现象,这个初始的网状结构分化为神圣性网络和技术性网络。这个假设认为,从原始网状结构出发,通过二分现象产生了平行的生成,我们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三部分已经提出过这一假设。它预设了对感知和行动结构的预先分析,这种分析在世界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关键点,是对格式塔理论最后阶段的延伸。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原始时期技术性和神圣性的联系,来为这种通过相位差生成的学说提供部分证明:技术面对神圣性并非中性:它们要么是神圣性的交叉点,要么是被排斥和拒绝的事物:铁匠被宣布为禁忌,或者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常见的基本技术,比如农业,都有其显著时刻的时间网络,这些时刻成为仪式化和献祭的契机:古罗马向神明奉献初收获物,春天祭祀牲畜。在中央高原地区的乡村,收获季结束的节日在 8 月 15 日举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用田野鲜花装饰餐桌的日子。年复一年,8 月 15 日彼此呼应。另一个节日是圣诞节;圣诞节也在时间中彼此呼应。植树在降临期进行,圣诞节是植物新年的时间关键点,就像 8 月 15 日是收获结束的关键点,在新的耕作之前,在新的播种之前。在这些时间的基本关键点上,人们回忆家庭和村庄的生死(这是家庭神圣性),并通过家庭仪式来尊崇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在圣母像下放置麦穗,为圣婴耶稣点亮守夜灯。
神圣性网络和技术性网络的重合不仅存在于古老的时间结构中,也存在于空间结构中。十字路口、海滩、山顶这些关键点在比技术和神圣这两个分化类别更原始的模式中就呼唤着仪式化。全面性的和日常的人类行动在将某些点神圣化或技术化之前,就在世界中寻找这些参照点。十字路口是选择、停留、相遇、危险或救援之地,是一个显著点,是约会、分离或谋杀之所。一个十字路口与远处的另一个十字路口比起来,要比与附近的一段普通道路更为相似,这是因为十字路口是行程中的多重决定点,是行动路径网络的节点,并通过象征性对应关系呼应着所有其他道路上的所有其他十字路口。行动对自身产生往复共振,这种共振不是直接和抽象的,而是通过显著时刻和地点的具体形式来实现的。在行动中,仪式化等同于其所展开的环境中的网络化:它是行动相对于自身的内部共振条件,是其有机性的结构。
神圣与技术的古老重合
从行动的仪式化结构出发,技术和神圣的空间网络与时间网络可能有着共同的生成。这种共同生成留下了痕迹。对海上水手来说危险的同一个海角,自然地竖立起了灯塔和保护神的雕像。因为海角,就像十字路口一样,既能救人也能害人,是旅程改变方向之处;它同时带来拯救和毁灭,具有决定的力量。当越过海角时,行动在自身中获得新的力量并得到重生:人们向众神献祭。说「恐惧首先在世上创造了众神」(primus in orbe deos fecit timor)并不完全准确;恐惧与众神同时出现,但不是恐惧创造了众神;恐惧出现在行动的关键点上,在选择、危险、重生、新的出发或灾难的时刻,也就是说,在行动具体化、凝聚为一些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时刻与姿态之时。恐惧或希望在人身上出现的条件,召唤着人之外的神圣性。但不是主观状态通过向外投射而创造了神圣性,也不是神圣性通过内在化而导致了主观状态。在某些地区,我们在道路的十字路口看到十字架。这些十字架构造了古老的仪式化,特别是葬礼的仪式化。在每个十字架前,抬棺者都要停顿,人们要祈祷。有时会有更古老的仪式介入。在中央高原布里乌德附近,在送葬队伍第一次停留的十字路口,人们不仅要诵经,还要在十字架脚下打碎守夜时盛放圣水和黄杨枝的玻璃杯。诚然,可以说在只有抬棺者而没有车辆的时代,这些停顿是必需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停顿或更换抬棺者并不是在任意地点进行的:这些因实际需要(疲劳)而进行的更换并不规则地分布在不同间隔上,以便与由十字架标记的路程结构相重合。神圣性与行动的这种相互性还体现在,在连续且没有十字路口的道路上,十字架被放置在显著之处,特别是在山丘顶端。
当行动回到自身,进行自我控制,自我重叠,通过多重决定而凝聚以从自身重生时,仪式化就出现了,它是技术性和神圣性的共同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所有真正具有孕育性的、危及人类生命的、受制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行动类型而言,神圣性和技术性至少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部分重合。在古罗马宗教中,神圣性通过基本行动的仪式化与技术性重合:耕作、播种、收获。在房屋本身,被神圣化的是那些关键点:门槛、门、门枢、炉灶。在船上,是船首和船尾。因此,很难说古老的仪式化是偏向技术性还是偏向神圣性;实际上,它们属于一个比分离状态下的技术或神圣更为原始的范畴。赫尔墨斯,界石和石堆之神,在山地牧场转场和放牧的仪式中具有其完整的意义:石堆是山地牧人的基本向导,就像十字路口是有规划道路的常住区域中旅行者的向导一样。后来,赫尔墨斯成为十字路口之神和花园的保护神;在古典罗马时期,他的角色退化了,因为行动的基本路线已经改变。阳具生育力的象征主义,在公畜引领畜群的游牧文明中是根本性的,但在以土地(雌性类型)生育力为主导的农业文明中意义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再与行动和孕育性情境相连,与赫尔墨斯相关的神圣性,这种古老的神圣性,变得封闭,孤立,转向批判,后来催生了密教主义。
向众神献祭的时刻并非任意的:它们对应着行动的基本时刻,就像圣礼对应着个体生命的基本时刻,标志着生命的阶段。
一种特殊的仪式化模式,结合了技术性和神圣性,体现在技术人员和工匠共同体对新成员施加的考验中。技术操作作为一种过渡仪式,被仪式化为一种献祭。它的完成关系到个人整个职业和社会命运;它不仅是一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庆典。因此,它构成了一个具有孕育性的操作,可能是危险的。在古老的劳动概念中,存在着某种神圣性的负荷,弥漫在努力、痛苦而有效地自我改造的感受中;劳动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也是一种让人参与到超越个人和生产事物的现实中的努力。当前的宗教更多地使劳动精神化了,但也在同样程度上部分地使其去神圣化,通过使神圣和技术这两个范畴相互疏远,并赋予精神性一种比操作性更具沉思性(contemplative)的意义。
神圣与技术的当前重合
正是通过情境的孕育性,神圣与技术的当前重合与过去的重合联系在一起。对于大型船舶和客轮来说,船只的命名仪式是社会性和世俗性的仪式,但对于那些日常面对海洋、吨位小、安全设备少的渔船来说,这种仪式就远非如此。正是这些渔船选择圣者或圣母玛利亚作为神圣的守护者。这种同名性(éponymie)在祝圣(consécration)中展现出神圣性的直接面向。在船东将圣者雕像嵌入船首的古老习俗与当前的同名祝圣仪式之间存在着连续性。除了圣者的神圣性,还有被祝圣的地点本身的神圣性,比如圣玛丽海滨。当沿海电台呼叫海上的拖网渔船时,人们仿佛听到一段悠长而单调的连祷文(litanie),其中交织着传说、岛屿和村庄的名字,以及宗教回忆。
诚然,有人可能说这是一种遗留现象,并援引渔民群体相对封闭的特点。然而,农业机械(拖拉机)的祝福仪式也已经出现。这些机器是新的,这样的仪式不能仅仅用传统的遗留来解释:确实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动机,导致人们将象征和具体化某种特定工作情境的基本技术物神圣化。
最近,教皇将电视(作为技术和艺术)奉献(consacré)给了圣克莱尔。
最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宗教形式的神圣性接受借用技术信息传播网络(无线广播和电视)来接触孤立的信徒。诚然,宗教神圣性与技术网络化只是部分重合,而且被有意地限制:电视弥撒只被视为真实献祭的反映,而不是完全参与的手段。然而,反映已经是一种可能参与的开端。当借用技术网络使宗教神圣性行为获得了一种否则无法获得的普遍性和同时性维度时,一种虚拟的重合就变得可感。这种神圣性行为的新形式并不取代教区参与的地方性行为;它在使命上是普世性的,传播至整个地球。由于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无法都聚集在罗马,教皇在 1 月 1 日主持的弥撒通过欧洲电视网播出,使这个在中心之中心完成的神圣性行为获得了一种辐射力,这在技术上与其神圣性维度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性以纯粹状态发挥作用,摆脱了其非本质的特征:观众成为参与者,图像不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个象征;它可能是贫乏的,不稳定的,可能要经受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清晰度变化,却不会停止传递其本质信息。1961 年 1 月 1 日,在法国网络上,来自罗马的图像起初不太稳定,然后完全消失,而声音连接仍然存在。在图像几分钟后以完全稳定的状态重新出现之前,法国广播电视台并没有像在艺术或纪录片节目的一般情况下那样,插入道歉说明;这是因为神圣性反映的传输不是一场表演;图像可能因传输困难而大大降低质量,却不会失去其基本特征:标准已经不同;在这里,技术行为是重大的,因为使其成为可能的结构是真正网状的。相反,当电视播放电影或表演时,每个地区发射台都可以自主运行而不会使节目失去其意义或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运行只是避免增加演播室的实用手段;因此它发挥的是次要作用,而当网络是一种参与工具时,这个角色就变得重要了。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技术性和宗教神圣性之间存在着一道文化障碍。电视摄像机和技术人员进入了圣地,但制度仍然是分离的;技术姿态和宗教姿态趋同而不重合,由于这种断裂而存在某种不适。需要一个为拍摄而建造的小教堂,以自主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控制和发射装置,才能实现技术姿态和神圣性姿态的重合。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无线电发射可以等同于钟声的声音信息。钟楼与教堂的本质联系并不比发射天线更紧密;它只是对应着一种更原始的信息传输方式。功能的相似性(将机械或电磁辐射能量传播到远处)导致了物质结构的相似性,因此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同构性:任何钟楼都可以不经改动就成为无线电发射天线的载体,就好像它本来就是为此而建造的一样。
诚然,技术性和神圣性的二元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以一种令人联想到战斗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福维耶山就是一个直接的象征,大教堂和天文台并列其上。这两座建筑的并列并不和谐;这个地点的唯一性似乎应该呼唤建筑的唯一性,而不是一种不谐调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也表现出来。同样,在皮拉山顶,我们可以看到相距十五米的一个巨大十字架和一座高耸的电视发射塔。在塔和十字架之间有一个观察台。这样的相遇源于地理结构使技术起源的动机和推动人类寻求与世界相连的神圣性的动机趋于汇聚。排斥的不是物质结构,也不是动机本身,而是这些结构和动机在其中表现和制度化的社会群体。与宗教神圣性发生冲突的不是电视的技术性,而是作为具有权利、风格和准则的制度的电视社会群体的封闭性与作为制度的信徒群体和神职人员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技术性和神圣性被包裹在一种社会的、尤其是社会心理的外壳中,这种外壳使它们异化,因此使它们相互疏远。源自技术性的威望与源自神圣性的威望作为被累积因果过程放大的社会心理建构而相互对立。当电视群体自我电视化(se télévise lui-même),或以自身为参照进行电视化,当神圣性群体自我神圣化时,这些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群体的自我在其自我意识中被放大和往复共振:技术显现和神圣显现(hiérophanie)消失了,让位于群体的社会心理表现。职业群体将自己呈现为它所掌握的技术或它所传递的神圣性的拥有者、所有者甚至立法者;它通过将技术性和神圣性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变成一个事物而使其异化。听法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似乎图像分析和传输的真实和绝对的技术图式已经永远具体化为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认为自己拥有专有知识,因为它垄断了合法使用权。同样,听着地球各处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似乎整个世界的神圣性已经具体化为他们作为当前和地方代表的唯一形式。
在这些占有(capture)和挪用(appropriation)的社会心理现象中存在着阻碍技术性价值与神圣性价值接近的根本障碍:在其社会角色中感受技术性意义和神圣性意义的并非同一批人,这是由于将神圣性意义与沉思生活联系起来的社会源头的文化障碍。神圣性与精确科学的相遇由于这个共同预设而顺利进行:像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这样的哲学为神圣性和可理解性找到了共同原则(例如创造者在组织自然时遵循的途径简单性原则)。但是,正是这同一个预设(présupposition)使得神圣性和技术性的相遇变得更加困难。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劳动而不是技术性与神圣性相遇:人们谈论劳动的道德美德,将劳动视为一种禁欲、一种净化手段,甚至是成圣的途径。某些宗教修会将体力劳动作为一种修行来实践。也出现过工人神父。然而,技术努力被搁置在一边,因为它既不是纯粹的沉思,也不是纯粹的劳动应用。如果保持对立沉思和操作的二元预设,就无法恰当地理解技术性。技术努力同时具有沉思性和操作性。当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工人神父,而是精通技术的神父时,技术性的意义才能与真正的神圣性的意义产生共鸣。
神圣性与技术性在未来可能的相遇:文化的统一性
同构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技术性和神圣性可能既不会混同,也不会相互替代。但由于它们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质上源于累积因果现象)阻碍了文化(Culture)的统一性存在,并延续了同样被异化的神圣性形式与技术性形式之间的无果冲突,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可能希望发现这两种结构协同作用的条件和意义。
技术性和神圣性是两个维度,在这两个维度上行动超越自身,不局限于自身,不与其自身的此时此地重合。通过技术性,行动分离、凝聚、调动它所组织和使用的世界的诸方面。相反,通过神圣性,行动注入它所渗透的空间和时间之中,既不分离事物,也不调动要素:神圣性使力量以静止的方式沉积在世界中,而技术性则调动和收集它们。尽管这些基本向量相对立,技术性和神圣性都预设了个体(在技术操作中)和群体(在神圣化中)超越其统一性和同一性:它们形成了一个结构的连贯世界。这两种结构类型相遇的必要性在当今显现出来,因为技术的阐发已经发展到群体的维度,而神圣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显现为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问,技术创造和神圣化是否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在手工艺活动的层面上,神圣性和技术性几乎不可能重合,因为技术性是个体或小群体所特有的;神圣性在集体层面上运作,这个层面在规模和分化程度上超过了手工艺小群体的水平;技术性的环境比神圣性的环境更小:相对于技术性这个次要者而言,神圣性显得更为重要;它支配和抑制技术性而无需互惠,因为它占据主导地位;在节假日里,神圣性对技术性施加禁令,并呈现为一种更高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不容质疑的,与技术秩序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
正是神圣性和技术性之间的这种量级秩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休闲(loisir)的社会心理概念的变化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在文艺复兴之前,休闲主要表现为节日时间,也就是因神圣性原因而禁止工作的时间:拉封丹笔下的补鞋匠面对过多的节日而哀叹,诅咒那些他必须通过停止工作来尊敬的圣徒们。直到今天,星期天禁止工作的规定在乡村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解除,比如当天气威胁要求迅速保护收成或收割已经晒干的干草时。神父会在讲坛上宣布这种禁令的解除。与此恰恰相反,在工作的技术环境中,在广泛的关系网络内部,休闲不再显现为对神圣性的尊重姿态,而是作为一项劳动权利,技术人员的权利,有时甚至是提高效率、安全性或结果质量的手段:休闲通过技术内部的理由来证成自身;形成了一种休息、放松、休闲的技术性,就好像对于那些生活围绕技术活动组织的人类群体来说,主导的、最为分化的主要形式如今是技术性而不是神圣性。这里涉及的是价值体系的问题。技术性和神圣性通过休闲而相互沟通,休闲在它们之间起中介作用并将它们隔离;休闲时间包含着神圣性庆典的时刻,后者就这样插入到技术性时间内部开辟的暗区中;在同样程度上,技术性的时间是世俗的时间,是工作日时间;节日时间在技术时间与神圣时间之间造成的时间性分离使它们相互平衡,并使它们像两种彼此制衡的力量一样对立;相对于彼此,它们就像格式塔理论中的图形与背景;没有任何单一视角能让我们同时把握它们,因为不存在稳定的中间项。休闲是神圣性与技术性之间的无人地带,而不是提供共同视角的共同领地。不存在单一的休闲形式,而是两种难以相容的形式:神圣性的休闲,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光晕,禁止技术性并将其推出神圣时间的界限之外,就像人们将世俗现实推出临近庙宇的区域一样;以及技术性的休闲,被构想为工作中的人的完整活动的功能之一。还不存在休闲的单义概念,因为休闲时而显现为神圣性最为世俗的方面,时而显现为劳动的神圣权利之一,与劳动的技术性水平成正比。
我们可以认为,重建文化的统一维度性需要对休闲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休闲的社会心理现实进行调整,使其接近古老的积极的闲暇 (scholè)概念。这个完全积极的、高度主动的概念强调一种无私性、自由性、自发性的面向,这种面向可能是神圣性和技术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共同点,或者至少构成一个对称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可以把握神圣性和技术性这两种对立而互补的结构。直到今天,尽管有弗里德曼(Friedmann)或迪马泽迪耶(Dumazedier)这样的有趣研究,似乎还没有人能找到关于休闲作为文化面向的现实的完整分析,这恰恰是因为,按照我们在此提出的理论,休闲必须被理解为技术性和神圣性之间的中介项,作为一种中心行动形式,技术姿态和神圣化姿态从这种形式中产生相位差。而艺术是休闲作为行动的基本范畴之一,技术性与神圣性的关系必须通过审美范畴这个中介项来研究。根据这里提出的理论,正是在艺术中实现和具体化了神圣性和技术性的同构关系,这赋予了艺术一种中介和交流的功能,这种功能对文化的统一性极为有用。
技术价值普遍性感知的到来;百科全书主义的意义
当技术性的意义形成为一个连贯的统一体时,它就与神圣性的意义相对立,也就是说,在法国,这发生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所体现的思潮中。百科全书精神首先是一个支持技术性的辩护。这是它带来的最新颖和最连贯的东西;对批判精神的辩护,对17世纪所谓的「既定等级」(grandeurs d'établissement)的攻击在18世纪中期并不新鲜;如果《百科全书》只是一本关于自由或奇迹与轻信的单独文章或论文集,它就算不了什么。一部作品具有社会心理影响力,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累积因果过程。《百科全书》第一次在一个此前一直保持非往复共振状态的现实层面上建立了这个过程,因为这个现实在每个行会中都是分散的、孤立的和封闭的。技术现实成为理性教学和表征的事物(通过力学作为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数字和几何语言)是新颖的。诚然,在《百科全书》中仍然保留着各种手艺的绘画性特征,以及每个职业的社会心理面向。在插图卷中,我们经常看到工具和机器的第一个总体视图呈现在乡村、资产阶级或城市景观前,例如「制塞工匠」(bouchonnier)或「天平/铸币工匠」(balancier)的插图;但在这种将技术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并开启人文地理视角的构图之后,一幅技术总图,然后是越来越精确和详细的分析图深入探索了形式和功能的秘密,直到机器和装置的核心;富有暗示性的绘画性让位于几何的坚实性,让位于测量的严谨性。技术显现式的启蒙不仅是一种揭示,而且从词源学意义上说,是一种向着实在内部的运动,越来越近地观察实在,在其结构和功能的内在性中越来越本质地理解它。但在这种向着实在内部的进程中保持不变的,是技术物的庄严风格和主导地位。当技术物在其初始的具体视觉中被把握时,它相对于世界和人类群体在其整体性中是什么,在其最终的机械细节中仍然是什么。事物对自身是同质的,对其每个部分是同质的,具有恒定和无处不在的尊严。部分被对待得与整体一样好,事物的整体被对待得与围绕它并构成我们今天所称的其关联环境的世界一样好。风车就是这样:第一幅图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整体,耸立在乡间,它的翅膀剪影映衬在动荡的云层上,它的基座融入被人类活动的劳作土地之巅,那里布满道路的痕迹。这种将天空(能量的环境)与大地(人类劳动和生活的环境)连接起来的高耸垂直性,已经是一个技术性的隐含图式:风车是中心、通道、连接线、交流系统,是最难以触摸但也是最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捕获器,这种力量与帆一起,使新大陆的发现成为可能:正是这种能量形式,在过去是最绝对的,文艺复兴时期寄望于它有朝一日能够「直达天象」(jusque ès signes célestes),如拉伯雷在赞美庞大固埃草(Pantagruélion)时所说。在这第一幅展示完整且与世界融合的图式的图版之后,接下来的图版给出了各种中介物(轴、齿轮、轴杆),能量通过它们传递到磨盘:这里展示的不是配件,严格说来也不是简单的细节,而是这条连接风的运动与人类获取面包的劳动之间的链条的基本环节。灯笼齿轮(lanterne)与翅膀轴或其帆布一样重要,因为其运作是一个连锁(concaténation)。这里不再有高贵的部分或卑贱的部分,严格说来,整体与部分之间也没有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完整的、具体的风车是一条链条,技术显现就是这条链条所有环节的完整呈现。这样一条链条建立起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劳动、发明、消费活动之间的交流,从而建立起价值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笛卡尔式的知识已经用因果链条的方法处理了一定数量的现实和问题,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人类的还是自然的。人们习惯于认为笛卡尔方法的第二和第三规则是受到数学中方程式列举和求解的启发。但也许更恰当的是,将它们视为从理性技术学中提取的连锁图式的抽象表述和概括,这种图式适用于所有发生因果转移的情况。推理是用长长的理性链条构建的,这些理性链条实现了一种「证据的传输」(transport d'évidence),就像一台简单的机器是用长长的齿轮、滑轮或接头链条构建的,这些链条实现了因果的转移并保持运动,正如一个构建良好的推理中保持着证据一样。笛卡尔将连锁图式应用于静态现实,这些现实过去被视为形式和质料的组合;当墙体的每一层都像第一层靠在坚实不移的岩石上那样靠在前一层上时,房屋就是稳固的。墙体是一个从岩石到屋顶传递不动性的转移系统,是链条的反面,因为链条承受拉伸,而墙体承受压缩。临时道德准则(morale par provision)更像是一个博学建筑师的规范而非数学方法:它们实际上是发现行为自我规范性(auto-normativité)的规则。而这种自我规范性恰恰是建构性技术性的特征,它在起点选择的方向上展开,没有任何先前的决定因素。技术性是自我构成的,就像迷失在森林中的旅人最初选择一个方向一样。在走动的姿态之前,没有规范,所有方向的所有脚步都既是等概率的也是等价的。但一旦迈出一步,它就成为下一步的规范,因为下一步相对于它是累积性的,所有朝同一方向迈出的步伐都叠加起来,引向森林的边缘。
在其绝对起源处,走动的行为不包含任何指向性的极性,任何外部规范,任何对可见目标的参照。旅人不了解森林的形状,因为他还没有穿越过它。规范是行为的衍生物,而不是一个需要实现的预先潜在性。任何行为,在其绝对起源处都是无规范的,它以自生的方式获得价值,因为它持续进行并因此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就像正在升高的墙一样。墙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建造;但一旦一块石头被放置,它就为下一块石头定义了规范。笛卡尔的政治道德本身就参照了这种内部因果转移的自我规范性,这种转移在虚拟上调动了被视为静态的整体。如果笛卡尔责备那些在精神上不断对「这些大型实体」(ces grands corps)——也就是制度——进行「某种改革」的人,那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可能扰乱平衡。不仅仅是要试图使整体形式符合这样或那样的原则;每个要素都是一个静态运作的环节,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嵌入整体之中。笛卡尔首次将文艺复兴纯粹理性技术中包含的规范性和心智图式转化为哲学并传递下来。依我们看,笛卡尔式的慷慨(générosité cartésienne)表达了对技术姿态中所包含的创造力的意识觉醒,这种技术姿态在其具有建构性的程度上是自我规范的。当涉及延长生命、治愈疾病或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时,笛卡尔所表现和确认的对科学知识的信心,建立在理性表征和计算在机器和建筑物构造中的有效性实例之上。哈维(Harvey)的发现让笛卡尔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生命有机体的运作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与机器相比,这使得科学知识能够把握这类现实,而这类现实在此之前一直是通过形式、质料、倾向和印记种类(espèce impresse)等概念来思考的。笛卡尔的连续性,真空的不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断言:它是一个同时具有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的公理,这个公理奠定了这种思想的基础,而这种思想的基本图式与完成建构性操作的纯粹技术性的图式相重合。
然而,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主义延伸了笛卡尔的机械论并使之倍增,赋予它一种在笛卡尔那里几乎不存在的美学转向。《百科全书》的技术显现也许没有给笛卡尔的工作增添新的智识图式,但它们带来了参与的条件,使灵感从个人传递给公众。在 17 世纪,人们可以欣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而不理解它的全部意义。只要公众还在嘲笑「那个吓人的长望远镜」,一些智者可能会欣赏「微粒」(petits corps)理论,但技术作为价值源泉降临的集体条件尚未实现,因为技术显现还不存在。相反,在 18 世纪,物理实验室成为社交沙龙的附属;长望远镜不再被限制在阁楼里:在被《论彗星对话》(Entretiens sur les comètes)为它们开路之后,它们又成为《论世界多元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的引路人;多样的情感性(affectivité)和情绪性(émotivité)为技术工具和事物带来了它们的辐射力量和集体参与维度,特别是当这些事物让人与非常规的量级秩序发生联系时,无论是在无限大还是无限小的方向上,或者与迄今为止仍然难以触及和神秘的力量和现实发生联系。避雷针是一项实践意义有限、理论意义几乎为零的发明。然而,这项发明的社会心理光晕是巨大的,因为它建立了与闪电的联系,与变成电火花的天火的联系,将其同静电机的火花等同起来,这种等同部分是错误的,因为人们忽视了电离现象。通过假定闪电和电火花之间的类比,对一种远远超出人类力量的现象的建构性理解,在避雷针中找到了其对应物和验证,这个技术物不是用来产生闪电,而是用来捕捉闪电,并通过将其导入地面来强加一个特定的路径。这确实是一个将人类环境与气象环境联系起来的技术链条,就像风车将推动云层移动的难以触及的能量与人手收获的小麦被碾磨的磨石联系起来一样。技术的连锁(concaténation)保证了现实的同质性。风和闪电与构成人类直接环境的现实属于同一类型;它们不仅以相同的方式运作,而且能够抵达这个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意义,在其中发挥作用。技术物使先前分离的、质的不同的现实秩序相互沟通,而这些秩序有时是客观神圣性的隐含范式(paradigmes)。避雷针的发明在迷信信念的层面上展现了一种去神圣化的情感力量。
作为超自然力量和人类生活层级之间的中介,技术物自然保留了一部分最近被人性化的超自然的威望:正是这种威望在《百科全书》中可以感受到,它赋予其技术显现行为如此巨大的辐射力量:这些技术显现部分地是神圣显现,但神圣显现的要素已经审美化,变得隐含。它以前浪漫主义(pré-romantique)的形式存在于《百科全书》中,如风推动着云朵在风车帆板背后消失于地平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百科全书》的技术学范畴看作一个顶点,同时也是一个过渡时刻:它们诞生于宇宙超自然的仍然活跃的威能(prestige)与新技术物正在显现的已经可触及的力量的相遇,这些技术物正在显现出与宇宙力量相当的尺度:古老的和崭新的在一个美学范畴中融合。
与此同时,技术物正在发展:但它还没有跨越工业物生产的门槛,它仍然限于个人或手工艺的建造和使用方式:它不比人更大,不支配人,并给人以可塑、可用、易于建造的印象:工业物网络尚未形成;晦暗的社会现实还没有像 19 世纪那样被技术的到来所搅动。
因此,作为封闭群体的行会,以其明确的仪式,其某些贡献能够直接进入这种普遍化的技术显现的心智范畴:共济会的图式、符号和象征包含了大量的工具或技术物。百科全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各种手艺的永恒颂扬,它恰到好处地使这些手艺去神圣化,使它们得以开放并相互遇合、趋同,但仍然保留了对人类天才力量的信念。在每种手艺中获得的人类建构力量的经验,在技术颂扬中得到普遍化,成为对多样且无限进步的信念。
因此,我们可以说百科全书主义包含着一种非常显著但脆弱和过渡性的技术显现努力:使其成为可能的美学和情感范畴无法持续到工业物时期,因为它们建立在手工艺制度与技术物的理性概念的交叉点上。然而,理性概念本身包含着工业物发展的力量和技术网络化的能力,这使技术变得比人类群体庞大得多。百科全书主义标志着一个特权时刻:技术现实的量级,从前比人小且可操作,是内在性的范例,由人建造并可随时轻易地被人修改,但正因如此力量微弱,现在已经增长并变得足够强大,能够使人类的量级秩序与昔日超自然的现实建立连续性关系;但这个已经成为机器的事物,尽管它从前是工具,仍然保持着某种工具的性质,仍然可以被人操作,安置在某个村庄,某个集镇,如同一个地方性的现实。后来,在 19 世纪,技术物跨越了门槛:它们比人更大并决定着人,对人施加的作用可以与古老的超自然现实,风和闪电相比。在 18 世纪,正在成长的技术物恰好处于人的层级,在几十年间完全人性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作为人文主义的基础,然后超越人类,在新的神话中找到位置,比如马克思主义将机器视为资本,本质上将其视为生产工具,这种操作被纳入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开发之中。
自 18 世纪欧洲百科全书精神的显现以来,再也没有任何普遍技术学(technologie générale)作为构建文化的宏大事业的基础重新出现:19 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运动,像 17 世纪大多数作者的理性主义一样,再次转向科学。但一个不同于 18 世纪百科全书主义的类似思想运动,有可能从诸如控制论这样的灵感源泉发展起来,控制论是一种覆盖复杂领域的纯粹技术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百科全书主义的倾向。
然而,除了严格意义上的表征内容,除了认知的阐发之外,这种技术显现意识觉醒最明显的社会心理标志,是这种技术物的出现通过其在广大公众中被体验和感受到的美学范畴而实现;我们已经提到了《百科全书》的图版,作为图形符号;但我们也应该想到 18 世纪的自动机械、气压计、物理仪器,它们通过制造者工艺本身的完美而获得文化目的和意义:它们展现了技术精神的胜利,这种精神确信其力量,为其手段感到欢欣,并且在粗糙的铸造就足够的地方普遍化了测量的精确性、表面的平整度、曲线的规则性。一个简单的支架或配重块都要经过车床加工,就好像在建构作品的过程中,闲暇本身以完美的实现形式物质化了。我们 19 世纪的物理学著作仍然保留着这些器具和机器的图像,它们是艺术品,提供了启蒙世纪生活之优雅(douceur de vivre)的技术对应物。在这之后到来了一个牺牲了作品中闲暇的内在性、同时也放弃了技术显现的铁器时代(Âge de Fer),直到圣西门的追随者们在一条新的道路上重新发现它们,这条道路更直接地与地理世界相连,就像加拉比高架桥那样,像机器一样建造的艺术作品(ouvrages d'art)。
18 世纪百科全书主义中具体化的思想运动,处在两个较少纯粹技术显现而更严格科学的阶段之间,即 17 世纪的机械论时期和实证主义时期。17 世纪的机械论表达了对技术建构性的意识觉醒,这时技术还是个体操作者的事物。诚然,笛卡尔已经完全认识到未来科学研究的集体性特征,并向王公们请求资助以便组建和指导一个包含任务分工的团队。但在 17 世纪,技术物的操作仍然是个体的事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事物保持着工具性特征。这种对工具的操作便利性,如同一件趁手的工具,是 18 世纪百科全书主义的心智氛围所预设的。相反,在实证主义中,心智范畴已经改变:人类劳动及其产品超越了个体的规模、其网络的网眼、其量级的层级。个体存在的劳动姿态融入当下和时间的普遍性维度;它在个体与无限超越他的人类之间的团结关系中获得意义,这种超越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这并不是说劳动和技术不具有建构性;但要环视作品已不再可能,它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再也看不到它的基础。实证主义者仍然是建造者,但他并未选择建造的初始时刻,也未自己确定建筑物的位置。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超越他的建造者人类中间进行建造,并在认识到人类生成的历史性的同时认识到他的作品的意义:超越性通过团结纽带重新引入,而不需要保留古老的超自然。
这是因为在奥古斯特·孔德时代,技术性的新维度强加了一个大大超越个体的参照框架。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精确科学带来的潜在普遍性,正在成长的技术在短暂的时期内能够同时呈现由手工艺劳动尺度带来的开放可用性特征,和与所有自然或曾经超自然的现实持续沟通的特征,这使它们与个人或小群体的人类现实同质化。但这种特权的、多重决定的地位,在一个正在增长的量级和另一个正在减小的量级相等的时刻把握到的地位,不可能永久持续。然而,它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非常宝贵,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技术显现平衡实现的条件之一,并强调了对社会心理现象而言,作为参照框架的现实的量级的首要重要性,这个框架是思考的人用来感知其与同类和宇宙关系的维度系统。一些社会学家确认,空间概念的基础应该在人如何建造村庄、帐篷或军营的方式中寻找;同样,时间的结构将是集体仪式和群体事件的结构。然而,这些记忆和空间行动的社会框架,一直被神圣性所渗透或体现着群体结构,直到一个更为宽广的框架在实践和集体现实层面形成为止。但是神圣作为参照框架的首要地位不一定是由于神圣性。它可能是神圣结构在宇宙中占多数的效果,在这个宇宙中,它们比道路、族群界限、海洋、气候都更广阔。如果神圣的网眼是所有网眼中最广阔的,如果神圣性是唯一组织成网络的现实,神圣性就变得占主导地位并提供行动和表征的最终参照框架:它事实上是最高的几何基础,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神圣性,也在于其作为包含所有其他结构的最高结构:这种至高无上与其作为参照系统的特征、作为宇宙性(cosmicité)的特征相关。如果技术性提供了比神圣性更完美和更高的宇宙性,价值和意义就会向它转移:此时是技术性变得多重决定,而神圣性则简化并在其维度力量上变得次要。
技术性和神圣性作为参照系统和信息编码
由于包含着不稳定的古老性与前瞻性冲动的混合物,以及两个相交但朝相反方向演化的参照系统的相遇,百科全书主义的不稳定性促使我们从其社会心理的编码功能的角度来考察技术性和神圣性,这种编码用于解码日常现实,以便认知、解释它并以明确的行动做出回应。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在其表征和操作的功能中,神圣性和技术性发生分歧,即使它们各自网络的网眼是同一量级的。事实上,我们必须在此考虑这些参照和形式化系统的自我维持机制:在神圣性系统和技术性系统中,这些机制并不相同。神圣性并不在其内部拥有使其得以维持的累积因果过程;它从人类动机和信仰的世界中招募力量和能量资源。维持神圣性的积极累积因果通过人类对神圣性的表征而发生。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在《小花集》(Fioretti)中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关于一只拯救了主人并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忠诚的狗。主人将他忠实的动物埋葬在山上,并刻下铭文纪念这一美好的勇敢行为。后来,重新发现的坟墓被认为是一位圣者的陵墓,这个地方变得著名,出现了类似奇迹的超自然现象。如果我们重提这个故事,绝不是为了试图给神圣性的一个次要方面投射一丝荒谬感。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值得称赞,因为他有勇气讲述一个不寻常的事实,而不担心会损害对圣洁性或神圣性的尊重。我们也不是要说神圣化的循环现象不需要一个启动(amorçage)过程,这个启动过程需要极其罕见和典范的条件,比如一位圣人的生平或一只家畜异乎寻常的忠诚:如果超自然存在于神圣化现象中,那是作为启动条件,作为初始的门槛跨越;在这个启动之后,现象自行维持,因为神圣性招募力量,汲取动机,维持一个特殊环境,这个环境使初始条件得以延续,并通过连续的献祭使其复苏,这些献祭就像是对初始冲动、首次跨越门槛、建基之时的回归。正因如此,如果这种持续的神圣化无法招募到足够的能量,它就可能停止启动:德尔斐的神圣性在数个世纪令人惊叹的光芒之后消失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神圣性也是如此。这些神圣性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绝热的(adiabatique):每种神圣性都有其特定的公众,从中招募能量并给予他们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准则、一种行动结构。每个神圣性网络都与某个社会群体、与一个特定的公众形成有机体:它由群体维持,也维持着群体,因为它与群体处于循环因果关系中。那些无法依赖宗教神圣性的群体,因为这种神圣性已经有了其特定公众而对他们不可用,就会给自己创造一种世俗的神圣性(sacralité laïque),比如共和国先贤祠和对祖国的崇拜这种神圣爱的事物。这种神圣性是绝热的,不与宗教神圣性沟通;相遇只能在更古老形式的神圣性基础上进行,比如对死者的崇拜。神圣性在本质上是二元的:相对于它,人要么在内部要么在外部;没有接近性、分数关系、优化梯度,只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法则。神学辩证术(casuistique)通过引入一个连续的价值尺度来使与神圣性的关系技术化,它并不严格尊重这种神圣性,并有使其停止启动的风险。神圣范畴的这种二元特征是一个稳定性条件,但也是可能的交流和图式更新能力的绝对限制:神圣性是僵化和有限的。同样,神圣范畴内部的普世主义倾向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每个神圣性系统都将自身呈现为潜在的普遍性,但实际上它与其他神圣性系统处于竞争之中。这种竞争的回响,反映了人类居住地球上各群体之间的对抗,维持着每个神圣性系统的招募,并确认其稳定性,在为人类群体具体化其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方面找到了一个次要的实践角色;因此,基督教世界既是一个宗教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社会心理概念;它通过一种「否定性的工作」来维持自身并维持组织它的神圣性类型,这种工作预设了基督教世界与按其他类型神圣性组织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对对抗。神圣性网络的多元性是维持神圣性招募的累积因果过程的社会心理特征的直接后果。一个特定的神圣性网络的存在,区别于所有其他网络,是一个参照系统,它为构成这种神圣性的公众的群体确立了一种内部的「普世主义」(œcuménisme),并通过参与的缺失负面地标记了群体外部的族群:外部否定性的存在,在异教徒那里,稳定了神圣性网络并赋予它一种积极的内部普世主义。但这种积极性只是对其他神圣性网络的边界否定性的对应物。内部的积极性和外部的否定性稳定了神圣性的有限宇宙:神圣性只有在多元性体制中才能完全稳定,然而在它所预设的心智范畴中,它又是对唯一性的要求:群体自我赋值(valorise)并将自己视为中心,视为中心的占有者: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神圣性的直接保管者。它倾向于普世主义,但不愿放弃其神圣性模式的特定特征,因为这种神圣性是某种社会心理存在模式所固有的:每个群体都愿意扩张到世界的边界,但不愿放弃任何构成其社会人格的东西,即使在它只代表居住地球的一个部分时。因此,为了普世主义而举行的会议,例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会议,通常以许愿和祈祷无果而终,这让某些参与者说:「自助者天助之。」事实上,除了教条的障碍,还有社会和社会心理的障碍:只有在非常严格的实践条件下,当不同教派面对着紧迫形势和一个完全异质的第三方现实时,它们创造出的特别具有孕育性的情景才能带来真正普世主义萌芽的切身体验。
然而,相反地,技术性拥有真正的普世主义力量,它甚至在其扩张的宇宙性中超越了普世主义。在跨越人类群体的界限之后,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统,其宽广的网眼以其巨大跨度使人类群体的特殊性和神圣性的地域主义相对化。诚然,对世界的普遍性视角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由哲学思维提供了,通过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然后是通过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但是,当这种宇宙性关注仅仅停留在表征层面而不涉及情感和情绪时,要在精神中持续保持这种关注就需要特别的反思努力。然而,技术做到了科学无法实现的事:它们使普通处境中的人能够日常地感知世界——正是这种普通性使得它可以被广泛参与——无需特别的紧张,自然而然地以技术所实现的行为单位作为解码的网眼,作为理解的视野宽度。当古代旅行者缓慢地穿越不同地区的危险而移动时,他确实抵达新的海岸,穿越异邦城市的大门,但他无法感知神圣性形式的相对性,因为他处于客人的处境,几乎是作为恳求者到来,需要他所进入地区的守护神祇。人类时间的昼夜节律、疲劳与休息、危险与救赎、风暴与平静后发现的港湾,其每个单位都比旅程的阶段和对神圣性连续形式的生活遭遇更短;在每次遭遇中,旅行者都被地方形式所支配,无法对其隐含的存在方式保持距离,而这种距离只有在同一生命单位内的同时感知才能给予。同样,在古代,神圣性最彻底相对化的地方是商埠(如米利都、阿格里真托),那里的航运路线带来了许多不同族群的人,携带着他们的习俗和信仰。相反,如今从一个机场飞往另一个机场的人在同一天的时间视野中,通过相同配置的同质性,感知到世界不同地点的多种神圣性形式。神圣性的网眼比技术性的网眼更小,技术性网络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统,将几种非同质的神圣性物种统合在一个单一的感知中。生活条件、安全条件,即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框架由此获得意义的东西,就是技术网络。地方时间是相对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来定义的。无线电导航网络相互连接,相互接力,覆盖全世界。一种事实上的普世主义,跨越国界,存在于技术网络中。航线、无线电话传输和广播环绕着人类居住的地球。而且不仅仅是人类世界(oikouménè),地球之外的宇宙现实也成为行动的环境和支撑。技术姿态指向超越人类世界的界限,瞄准星际空间:普世主义本身已经相对于宇宙性维度而相对化(OZMA计划)。
我们不应该说这种基于技术网络的解码是不真实的,而地方性神圣性才能整合进「符合人的尺度」的具体现实把握中:当技术为人提供现实的视野时,它在某种意义上总是符合人的尺度的;但存在着多种感知和操作的尺度,有些更常见,有些较少见,但都同样客观。步行时,人以某种方式解码世界:感知-行动的网眼(maille perceptivo-active)与碎石、灌木、形成障碍的树根的尺度相当。在汽车中,人看得并不更差,而是以不同的理解视野在观看:行程更长。在飞机中,人看到的也同样具体,但网眼更大。要具体感知地球的曲率,需要在 40 公里的高度。然而地球的曲率和路上的一块石头一样真实:只是它只有对能把握 400 公里范围的观察者才变得具体。步行也同样是抽象的;它忽略了沙粒和小昆虫。步行者看不见它们就走过去,忽视它们,踩碎它们。坐在路上或在地上爬行的儿童感知到步行者所忽视的现实。网络化技术的使用定义了行动的路径和维度,这些路径和维度提供了对人类现实和神圣性的相对化感知。
要感知相对性,人类主体必须处于这样一种情境:他支配着被感知的现实而不依赖于它,这意味着相对的安全性,尤其是当各种所见事物流过时主体的配置和态度的持久性。不安全、孤立,或太长的行程时间会阻碍感知主体的这种稳定性和独立性。技术网络对自身同质,在自身中往复共振,包含着主体并作为其环境、基础、参照系统。乘飞机抵达一个国家并知道几小时或几天后将以同样方式离开的旅行者只是部分地参与这个国家的生活:在他内心持续保持着与网络的关系的持久性;它是转导性地将他与其初始人格联系起来的链条;他的访问是一个延展的停留,但旅程仍然在场。当我们通过无线电波接收到人类世界的回声或反映时,同时保持着将接收机与另一个发射源同调(syntoniser)的可能性,人类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仅仅通过无线电波进行远距离接收这一事实,就构成了前技术宇宙所缺乏的这种相对性和普遍性的基础。
因此,作为社会心理框架的技术性和神圣性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当技术性创造出维度超过最大人类群体的网络时,技术性并不遇到障碍,也不强加一种伪普遍性的扭曲(distorsion de pseudo-universalité)。诚然,并非整个世界都被每个技术网络所解码:一个捕捉无线电波,另一个确保人员运输,第三个负责遥控装置的卫星化(satellisation);但是,正是通过这种专门化,每个网络都具有潜在无限的增长能力,而且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连接。神圣性是整体性的、非特定的、高度多元决定的,但它很快就遇到了其极限,并且在已经被技术视角所限制的人类居住领域中,仍然保持着多元化的彼此不相通的分离形式:神圣性声称具有的唯一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神话性的。
神圣性和技术性的相对量级秩序的逆转(renversement)的结果是,神圣性倾向于占据手工艺技术性(technicité artisanale)留下的空缺。在像美国这样高度技术化的文化中,被信息和通信网络所主导,神圣性成为一个私人事务,受制于选择,受制于个人决定,就像加入某个社团或俱乐部一样:神圣性的多种形式被接受,宽容甚至不再是一种美德:神圣性表现为一种类似于艺术的文化内容;与技术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它似乎缺乏生气和交流的力量。它不再是主要的(majeure),而技术才是主要的。
大规模人类群体层面的技术性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技术网络通过增加其网眼尺度而与国家和大陆群体、世界大国的量级秩序产生扰动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只要这两个量级秩序(技术的和人类的)保持等价,技术现实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类型的技术显现,展示群体的力量和存在;后来,当技术现实的网眼变得比人类群体更大时,它就不再是群体的代表。从 1935 年到 1944 年,最强大和最具威望的技术显现是无线电发射。德国和英国利用无线电发射机进行了部分战争,伴随着干扰和反制发射。希特勒特别理解无线电广播的技术显现意义。欧洲每个国家都想拥有一个长波发射机。老式接收机在长波波段的刻度盘是一堂人文地理和社会心理学课。这种首都的层级展现了某种宇宙性意义:这些大首都同时出现在可以通过直接传播在白天和夜晚接收的波段中。法国发射机在 1944 年被德军摧毁,直到战后许多年才以相同功率重建。巴黎电台仍然铭刻在欧洲历史和技术史中。然而,如今无线电发射的功率不再具有如此大的威望,技术显现的力量已经转移到火箭和人造卫星上;现在是它们成为了群体的代表。在这些技术物中,群体认出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的统一性、凝聚性,就像从前在神圣仪式中一样。在这里很好地显示出了技术性和神圣性的分歧:神圣性因其独特性的意识,通常转向过去;因此神圣显现只能为一个正在扩张的群体提供一个不完善的意识觉醒机会。相反,技术显现不预设任何东西,不指向任何传统或先前的启示;它是自我证成的,并成为一个发现其扩张力量和动态性的群体最恰当的象征。如同神圣显现一样,它补偿了贫穷和苦难,它无限地超越了日常秩序和消费品的秩序。一颗人造卫星没有任何用处。然而,1957 年初秋第一颗卫星发射的反响超过了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如果将第一颗卫星的发射仅仅视为科学的应用,那它只不过是牛顿天体力学的一个说明。事实上,它的速度足够低,不需要用相对论的公式来计算。在科学理论层面上,这颗卫星甚至对我们的祖先也不会教授任何东西。战后立即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恒星物理实验——美军雷达向月球发射电磁波列并接收回波的实验——在公众中只引起了微弱的反响。然而这是一次真正的星体物理实验。但这不是一个技术性姿态。发射卫星是一个姿态;它不仅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个现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现实,就像经过的汽车声或火车的汽笛声一样。它也与轰炸机的飞行和炸弹的坠落同质。但同时它超越并使它们降级,它把所有这些太过平常的现实搁置一边,并作为一个被压抑到无意义中的宇宙的显著点而显现。在一段时间里,它类似于一颗星体:它通过显现自身而登上王座。这个威望性的姿态将所有消费品都推向庸俗或荒谬。它显现为某种禁欲、某种相对于可售性和消费品的超脱的结果。
技术性姿态在外表上呈现出与神圣性显现的仪式化和庄严性相似的方面,因为它对大规模群体履行着等价的显现功能。国家首脑被迫进行技术显现,他们的形象与最新的技术物联系在一起:喷气式飞机、原子弹、火箭、卫星。发射炸弹或火箭包含了一个「倒计时」,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程度不亚于宗教献祭的准备。技术性姿态的失败——火箭坠落在基地附近或失去控制——产生的集体效应与罗马人时代神圣的鸡不愿进食,或被献祭的公牛带着可怕的伤口连同祭司的斧头一起逃离祭坛时一样令人尴尬。发射火箭、发射卫星扮演着与神宴(lectisternes)和百牲祭(hécatombes)相同的角色:作为现代集体献祭,它们回应着一种紧张感的存在,一种被集体感受到的焦虑。它们作为姿态而存在,先于成为实验或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岛原子弹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显现,而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它产生的社会心理轨迹与第一颗卫星的相同:时尚、玩具、新词汇,通过光晕效应使威望辐射到整个相关科学和技术领域。
这些新仪式的祭司(le sacrificateur)是穿白大褂的人;他的信仰是研究。像神父一样,他是禁欲的,有时特立独行,超出常人。像神父一样,他形成了与社会其他部分区分开来的群体。
然而,即使技术显现取代了神圣显现,它们也不是严格类比的。它们展现了大规模群体,但并非所有技术人员都完全被某种形式的技术性所包裹。在技术性姿态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种科学的光晕,技术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一个学者。即使在合同下工作时,学者型技术人员仍然与其作品的社会内部意义保持着一定距离。即使在最直接具有技术显现性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术会议和国际会议:正是这种通过技术人员和学者之间的国际交流而表现出的真正普世主义维度,拯救了技术性免于重现神圣性范畴的唯一性危险。一个技术物,即使是最近发明的结果,也只是在短时间内是唯一的,而且与其说是因为其本质,不如说是因为缺乏其他范例。当技术完善时,技术性的秘密性逐渐退化,在当前的技术性中,它构成了一个表面多于实质、非本质的和古老心理的范畴:在技术领域中,秘密的概念对应着生产的手工艺状态;它与标准化以及交换和分配途径的网络化相反。相反,神圣性致力于唯一和不可替代。对它来说,规范已经给出,只能丧失:它投射出一个世界历史,这是一个退化的、失去意义的历史。相反,技术性预设规范从未被给出,而是有待发现。唯一性不可能存在,因为唯一性是已经给出的、不应失去的东西。技术性包含着一种基于等价性的多元性力量,它发展出一个包含无限多个全都是积极的程度的价值模型,就像研究的连续阶段一样。神圣性只有两个价值,神圣的和世俗的,神圣的在场或缺席。
结论
作为文化基础的技术性与神圣性的汇聚在审美作品的层面上是可能的,审美作品表达了人类力量和权能的当前状态,处于从过去带来的唯一性与面向未来开放的技术现实的网络化力量之间。对唯一性的指涉体现在审美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中,对创造性的指涉也在其中呈现,因为它展现了一种人类力量。但是使技术性和神圣性汇聚的审美范畴并非通常的、可从世界中分离的审美范畴。它是一种对现存实在的整体性和组织的关切,按照实在的线条和力量,为了依照这个唯一世界的唯一性而增添由技术创造性带来的多元决定性:在这种整体性的美学中,存在着对神圣性的感知,也就是对先于技术性而被给予的世界的唯一性的感知,这是建构性的基础,是完整自然的开放系统。神圣性是对所给予之物及其完整性价值的意识,无论这个所给予之物是整个宇宙、地球,还是仅仅一个个体,动物、人或植物:当我们在其真实整体性中考虑每个存在物时,每个存在物都具有一种唯一性并与其他存在物分离:相对于它而言,所有其他存在物都是世俗的。每个存在物都可以这样被把握,每个存在物都是可以被祝圣的,每个存在物都是自身的圣所:审美的目光祝圣存在物,将其建立为自身的圣所,通过观照而非使用来尊重它:神圣性赋予审美姿态以其观照的力量。技术性赋予它操作的力量和通过可能的增殖而实现的交流开放性;作为对完整性的尊重的神圣性与技术操作是相容的,但只有当一个共同的价值将它们统一起来,与它们的两种结构同构时才能如此。这个价值无法在伦理学中找到,因为伦理学深深渗透着每个群体特有的文化性,因此无法以普遍的方式参与。兼容关系必须在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层面上寻求,而不是在一个已经历史化的人类公理系统中寻求。如果这种发现是可能的,它将为一种文化提供基础,这种文化将使审美范畴重获它在希腊人那里占据的中心地位,这远远超出了一切属于愉悦秩序的东西,甚至超出了被理解为分离活动、艺术家之物的艺术。这种审美范畴的扩展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显现,那时出现了像达芬奇这样的工程师-建筑师-艺术家,将技术发明与审美创造结合在一起。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些尝试朝着发现古老神圣性与最新技术性共同规范的方向发展:这是勒·柯布西耶在里昂附近图雷特修建的修道院的一个方面。但距离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这样的作品本质上给人一种技巧性和大胆性的印象。如果技术性和神圣性可能通过艺术相遇,那是在广大网络的层面上: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概念,特别是在其消极方面,将技术图式化和对神圣的直觉的范畴统一起来。这是一种消极美学,能够感知组织和发展过程中的畸形性(monstruosité);与畸形性意识相对应的积极范畴是功能优化,在存在物的组织中寻求最高的形式水平。然而,在人类劳动的建构性所产生的作品中,并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动态形式,总是存在着某种消极的东西,一个方面使得构成的存在物与自身对立并在其运作过程中自我毁灭:存在物永远不是完全具体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总是畸形的。对存在物的隐含畸形学(tératologie)研究统一了神圣性的直觉和技术的操作规范性。它超越了相对于已给定的、局域的、因而是绝热的心理社会存在方式的伦理学。
因此,最近《罗马观察报》针对在博洛尼亚进行的一项实验提出了反对,这项实验是关于人类胚胎在体外受精后的体外发育: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神圣性的授权代表在这里表现为自然的捍卫者,面对的是博洛尼亚生物学家们的技术性姿态:神圣性捍卫自然对抗技术,尽管神圣性知道如何反对作为世俗现实的自然。当只存在世俗和神圣这两个秩序时,神圣性反对自然,就像完美的秩序反对可能的畸形,反对原罪或现实之罪,反对恶的倾向,反对这个「罪恶的温床」,这个特别存在于欲望中的邪恶行为的潜在储备。但是当技术性,在科学的推动和引导下,引发产生怪物的机会时,自然,被认为具有较小的畸形生成能力,就成为了神圣性对抗技术性的堡垒。让·罗斯坦关于博洛尼亚实验的判断直接指向了一个事实,即那些组织实验的人制造了一个怪物:他们「走得太远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第 28 天停止胚胎发育,原因是它呈现出异常特征。最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博洛尼亚的科学家本人在停止实验时,服从了一个并非严格科学的命令;他本可以让发育继续进行,以便观察会出现什么类型的怪物以及它将如何分化。这个畸形性的概念,作为一种超越伦理的消极美学的基础——因为它不是绝热的,而是转导的——是神圣性代表者的判断和源自技术性的判断的共同因素。
通过深化对神圣性的直觉和技术性的规范,我们无疑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参照,即避免被理解为存在物内部功能矛盾的畸形性。一个古老的圣经禁令如:「不可用母羊的奶煮其羔羊」在畸形学意义的宇宙中呈现出一种意义:母亲的奶旨在哺育幼崽,它不是用于这种毁灭行为的。正是在对功能的深度感知层面上,神圣性发现了其避免畸形性的力量和职责。这种规范性的功能内在源泉并不依赖于一个被接收和启示的法则,即使它通过教条表现为如此。同样地,它也不严格限于特定的公众,不限于一个封闭的人类群体:它是神圣性中能够在群体间传播的东西,有时会带着原始群体的神话学的死重,但允许按照某些价值——功能性的价值——来参与,并走向与技术内在规范性的相遇。
在神圣性和技术性之间存在着一片无人区(no man's land),正是在这片无人区中,一种规范性必须显现出来,作为一种文化统一性的基础,这种统一性适合于大多数人类群体当前的社会心理生活条件。事实上,正是在这片无人区中,最具极化性、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得以建立,它们的建立没有积极的规范。然而,它们引发价值判断,引起丑闻或赞叹:一种社会心理生活是存在的,但它并未形式化。最近,法国媒体报道了一个遭受严重激素失调困扰的年轻农民的案例。这种失调导致肥胖,使任何职业活动和正常生活都无法进行。这个年轻人通过严格的饮食和强效药物治疗,成功地恢复了一段时间的正常。但如果没有一系列针对内分泌腺的手术,他就无法最终痊愈。这个治疗过程漫长,费用昂贵,为了能够接受治疗,这个年轻人决定出售他的一只眼睛。这就引发了丑闻:一个生命存在为了恢复其内分泌腺——机体的一部分——的正常运作,却必须放弃其机体另一个子系统的完整性,这是畸形的。这个有偿摘除眼球的手术,作为对内分泌系统改善的补偿,在机体完整功能性的层面上是直接且绝对畸形的。它清除了手术的任何技术性意义:对腺体进行手术的姿态被摘除眼球这个制约性姿态变得荒谬。这是功能整体中的一个异化案例,它表明一个纯粹操作性的姿态,如手术姿态,是低于技术性的:它不具备适合于其所操作的整个现实的规范性。这个案例等同于体外培育然后因变得畸形而被销毁的胚胎的案例。仅仅是它可以被不同方式审视这一事实就表明,在技术和神圣性之间存在着一块中性地带,一种规范性必须在其中诞生。可售性的动机是异化的,因为它是片段性的:腺体手术的可售性与眼球摘除的反向可售性之间不存在任何真实的互补性,即使一个手术的花费正是另一个手术带来的收益:结果是一个较小的存在,相对于其本质而言是机体功能性的减少,支配它的所有工作和思想的整体都是畸形学的。
在同样程度上并以同样方式,一种新的规范性正在通过丑闻感在神圣性和技术性之间诞生,这发生在镇压和司法领域,更普遍地说是在政治、社会或种族冲突领域。纯粹的法律主义和司法主义显示出其概念和操作上的不足:「叛乱者」「违法者」「罪犯」「有罪者」「抗命者」等概念定义了一种法律状态并允许合法性嵌入实在之中,但这种合法性本身相对于情境的功能整体而言是相位错位的。罗马的法律惩罚概念——「向某人给予惩罚」(poenas dare alicui)——是等价于一种转置的可售性,与前述案例中为了获得一个内分泌腺而摘除一只眼睛的个体有机体的可售性一样具有异化性。一种尚未概念化但已被体验和感受到的有机统一性被发现了,它显示了「向某人给予惩罚」和各种牺牲性赎罪过程的虚妄性,正是这些做法为法律制度中的死刑和集体领域中的镇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战争、司法、族群冲突这些现象同时具有神圣性和技术性的双重特征,但问题在于:它们所具有的那种牺牲性的、神话性的神圣性,与其操作层面的技术性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造成了一道巨大的裂隙,正是它创造了对规范性的呼唤。这种二元论例如表现在警察和司法之间的距离:警察可以使用所有审讯手段,即使它们违背人的完整性并与司法规范相对立;司法知道这一点并接受它,以一种不是法律规范的实用效用的名义。在战争中或在未被承认为战争的种族对抗中,在激励斗争的宗教或世俗神圣性理想与专门行动的技术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外交、宣传、情报部门行动、酷刑、灭绝、压力集团行动。即使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否定性的工作」,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混合了神圣性和技术性而不使其相容、不使其统一的活动和制度所代表的努力、痛苦、生命、被压垮的可能性之总和,这种工作表现出极低的效率。这些活动和制度是畸形学的,因为它们降低了它们所作用的现实层次,而不是使其与自身相容。在司法领域,对建设性效率低下的意识开始形成,通过少年犯罪或以精神异化为理由的治疗等范畴,人们经常采用规避司法程序的旁路手段:人们试图扩展这些范畴,特别是通过「青年成人」(jeune adulte)的概念。但这些规避传统司法程序的旁路,尽管暂时发挥着积极作用,却取代和推迟了对法律范畴的重铸,这种重铸本应不是从边界,而是从主动的中心出发,通过神圣性感和技术性感的趋同来实现。最近的作者,特别是德·格雷夫(De Greeff),已经意识到了司法中技术性和神圣性之间存在的这种裂隙:他们倾向于一种发生学的观点:据德·格雷夫说,如果在犯罪者的婴儿室里审判他——也就是说,带着延续其发展的认知和情感视角——他永远不会被定罪。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规范领域中,在技术性和神圣性之间的这片无人区中出现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建构性。它不像效率那样受限,而是将效率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系统中,并符合对神圣之物追求的无限特征;建构性是自我规范的和自我构成的;它隐含着神圣性和技术性共同的公理系统。这种新的公理系统是如今实现最完整的事实上的普世主义的系统;它开始表现为科学、技术、外交领域的共同规范;它介入文化交流。
然而,「建构性」(constructivité)、「发展」(développement)的发生学规范性参照的是同时具有定量和定性的有机性标准,包含累积性增长的方面和形式分化、组织的方面。
当前这种似乎必须在分离神圣性和技术性的中性区域中诞生的规范性的方向,指向理解和体验每个人类或自然现实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方式:神圣性的目光在存在物中,例如在个体中,把握到一个不可分割和同质的统一体,其中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就好像整体是不可分析的。对人类个体的这种神圣化催生了人格的概念。相反,技术的目光把握存在物各个不同部分的潜在多样性,因为操作性的关切使存在物,即使是个体的存在物,成为一个待完成的现实:尽管有机团结性存在,其不同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分离的。当神圣性的观照考虑个体的行为时,它将其判断为完全善或完全恶;它不在个体中切分部分或区域;斯宾诺莎式的「就其而言」(quatenus)不是源自神圣性的概念。相反,在技术性做出的价值判断中,存在着对可能的片段性干预的隐含假设的参照,这种干预旨在修复、改善或优化存在物。从技术角度看到的个体存在物不是完全善或完全恶:它需要在局部进行修复;它被认知为召唤修复姿态的东西。神圣性的干预是一种献祭,也就是一种无需详细分析就作用于整个个体的嬗变操作,就像荣格所描述的个体化过程,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炼金术士的探索中重新发现了这一过程的意义。个体存在物是按照其整体性,通过其净化或湮灭,进入献祭或在其中发挥作用:神圣性蕴含着一种全有或全无的逻辑和价值论。相反,技术性假设存在物的存在和生成具有部分片段性的状态。正是借助这种区分,我们才能把握同时包含技术性和神圣性的制度性范畴(如司法)的内部连贯性的缺失。惩罚、刑罚、罪责、责任等概念源自神圣性的整体性特征;相反,技术态度假设存在物可以分解为子系统,并可以通过对这些子系统(恐惧、痛苦、疲劳、兴趣、错误、影响)的分离和特定行动来改变:「心理学」的使用是为了揭露或瓦解的目的而实施的人格碎片化手段,而罪责概念则假设人格的统一性;然而,在这个领域中,手段的技术性与目的的神圣性之间的摇摆产生了巨大的不适:技术性分解实在(将个体分解为子系统,将群体分解为个体);神圣性设想甚至创造整体——个体层面上的人格或群体层面上的社会——人格和社会被视为不变的或不可分析的。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死刑这样的惩罚是畸形的,因为它没有优化任何东西,它完全是破坏性的,其做法是因为一个子系统在可能是偶然的条件下以被认为应受谴责的方式运作,就判处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分化的神经系统的所有子系统走向湮灭;它与一种古老心理的破坏性神圣性系统相关,这个系统奠定了「给予惩罚」的基础,并假设对一个存在物的湮灭是一个积极工作的开端,因此构成了一种现实的位移而不是破坏。破坏性惩罚只有在一种类似于炼金术或古代献祭的魔法和神圣系统中才是连贯的,这种系统将一个存在物的生命能量位移到另一个存在物身上。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如同一位法国法医所强调的,死刑只能被视为一个个体的过早死亡。直到今天,在法律价值领域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严格连贯的中间项,这也许表明在一个将技术性和神圣性综合起来的文化中,这个领域不可能拥有完全的自主性:健康规范和发展规范的关切不能缺席于法律范畴。正是在规范趋同的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给予我们所称的消极美学范畴以意义,这个范畴包含畸形性和功能优化这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