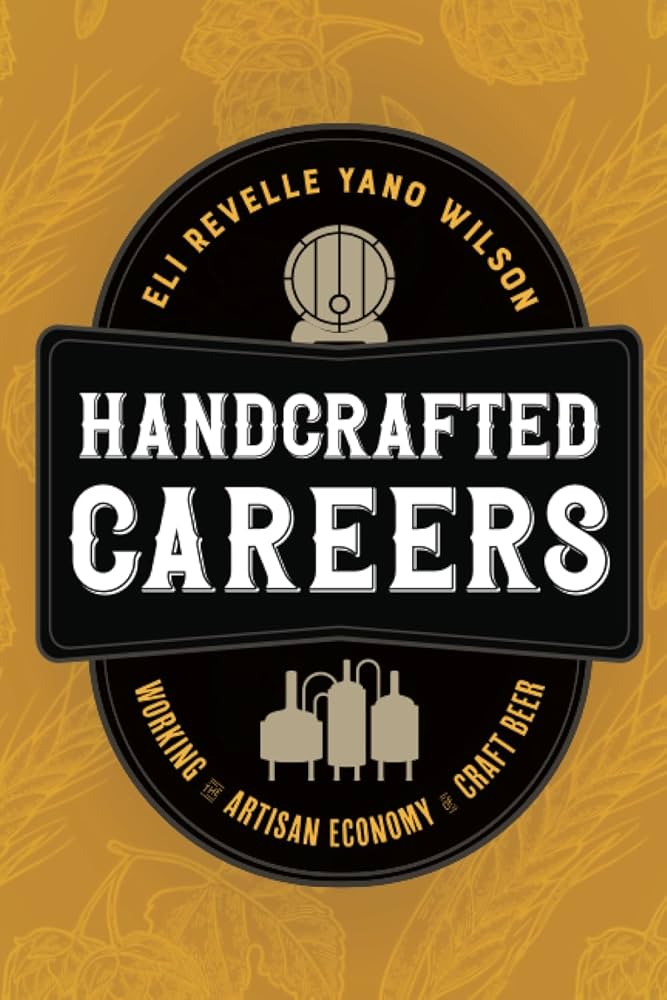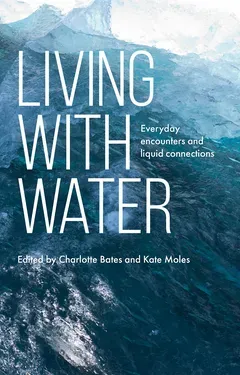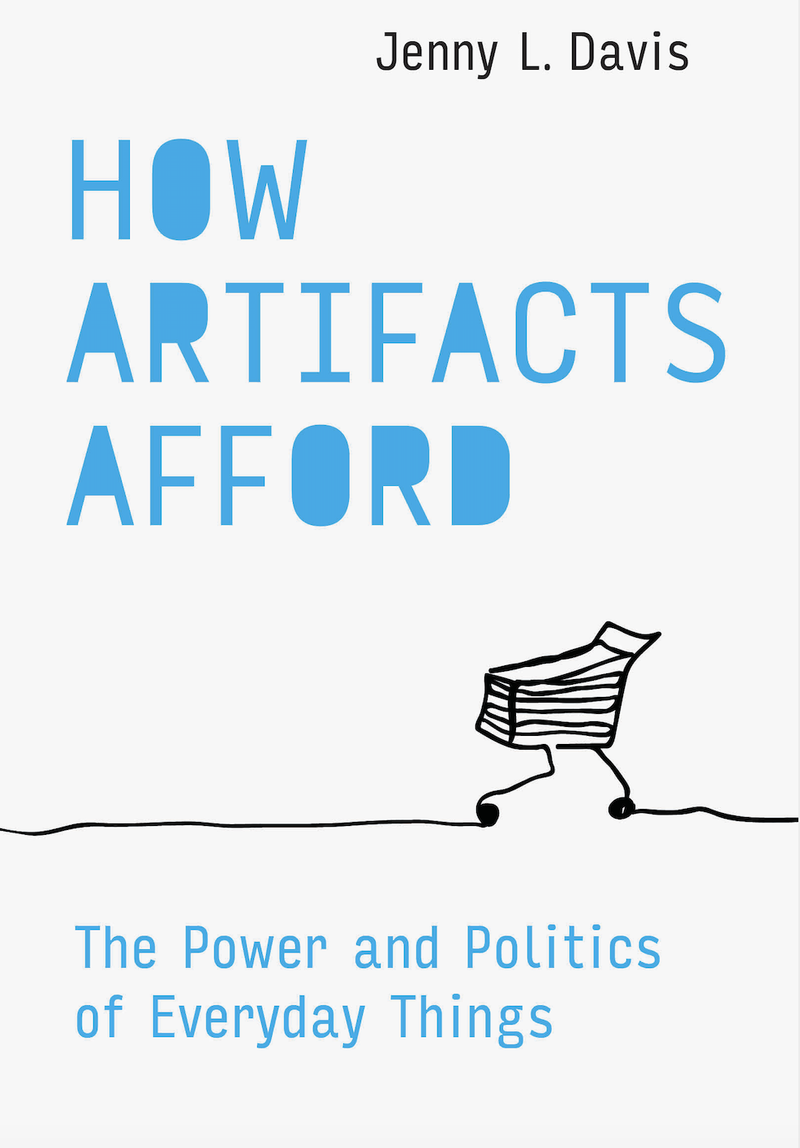城堡中的K
「我们不喜欢这样。」「怎么会喜欢呢,」K说,「你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可是只能这样做。」——卡夫卡《城堡》[1]
在所有对PKD的回忆中,有两段话往往占据中心:其一是《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一书扉页上叶芝的诗:「而我仍梦到他踏着草地,在露水中飘飘荡荡行走,让我的欢歌轻易刺透。」其二则是雷德利•斯科特在《银翼杀手》中添加的台词:「所有这些瞬间都将随时间逝去。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2]」
一如两段引文所呈现的那样,如果说《仿生人》一书的基调是对往昔的怀念及与其相伴的孤独,那么在《银翼杀手》中,怀旧的泪水却只能为绵延的雨所洗刷,孤独的身体将走入坟墓,最后留下一片崭新的大地。可以说,两部作品虽然呈现角度不同,但却保有着同样的怀旧、恋乡与孤独感,也正是这种感受,将迪克笔下那个阴冷朦胧的世界与早期科幻作家们所构筑的各类乌托邦(《乌有乡消息》)、反乌托邦(《1984》《美丽新世界》)和奇幻冒险(《地心历险记》)区分开来。
事实上,尽管迪克往往被放置在从反乌托邦到赛博朋克的系谱中进行考察,被认定为前者的继承人与后者的开创者,然而倘若抛开「科技」「集权社会」等设定,其作品在行文风格与内在主题上都与这一系谱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反而更接近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纯文学作品。这种风格与内核的亲缘关系直接源于迪克个人的文学旨趣。在迪克的传记(《The Search for Philip K. Dick》)中,迪克的第三任妻子安妮就曾回忆起两人第一次见面后,迪克执意要借给她的三册书:卡夫卡的《城堡》、黑塞的《悉达多》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3]。
在卡夫卡的K与迪克的K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高堡奇人》直接借用了《城堡》的意象与集权社会的设置;《流吧!我的眼泪》中一觉醒来就失去了所有个人资料的杰森仿佛是《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再世;《仿生人》中的里克虽拥有了审判的权力,其实质却也如《审判》中的K一般在不停被「审判」——在其早期的纯文学创作经历中,迪克不仅习得了一种特定的超出类型文学的笔调,更在生活与文本的共鸣中逐渐找到了其科幻创作的母题:对逐渐冰冷、抽象的世界的恐惧与反抗。
这种母题决定了迪克的科幻作品并非充满各类科学设定的硬科幻,也不是横跨各个星域的宏大故事,甚至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只是断片式地聚焦于那些抽象社会中最为具体的人,看他们是如何面对世界的挤压与塑造,是逐渐变形还是与之相对抗。不妨这么说,正是这种出于恐惧之外的「反抗」,使得迪克拥有了不同于纯文学作者的气质;然而也正是在对抗之中生成的「绝望」,使得迪克的作品呈现出一般科幻作品无法达到的深度。
然而与其说迪克的作品在卡夫卡之上生成的一种「反抗」的精神,毋宁说迪克是彻底放弃了与现实世界对抗的可能,将对抗转入了科幻世界之中,将对抗变作一种怀旧恋乡之情:「我想写那些我爱的人,并将他们放入我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世界中,而不是放到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因为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远未达到我的标准。那么,我应当降低我的标准,我应当跟大家合拍,我应当顺从现实。不,我从未顺从过现实。这就是科幻干的事。」[4]
迪克所怀念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温柔的世界,一片可以踩踏的草地,还是一些所爱的人?或许都是。对于迪克来说,未来正是过去的倒影,那个过往的世界中不仅存在着真实的绵羊,还存在着已经逐渐逝去的人性。在这里,迪克不仅与卡夫卡,更与马克思、卢卡奇等人达成了一致:未来的目的正是要从现实中拯救出已经被「异化」的人,即便这种拯救未必能够达成,甚至未来本身成为了「异化」的源泉,但一个替代性的世界终究值得想望,至少其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离」的可能。恰如马克思从伊比鸠鲁处所学到的那样,在冰冷的一切仿佛都已注定的世界中,偏离即是自由——正是通过偏离基线,《仿生人》中的里克才发现了自我。于是,迪克故事中的那些边缘人、瘾君子、失败者,便仿佛成为了后人类图景中的自由女神,召唤着早已逝去的时光。
后人类的守门人
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机可能就是现在。不要等到它所体现的思想列车稳稳地停下来之后,再用炸药来改变它们。——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尽管迪克的作品拥有着卡夫卡式的核心,但类型文学的标签与科幻文学史的塑造却逐渐改变了大众视野中的迪克印象,使其从一个关注现代抽象社会中人性异化的「作家」,转变成了一个聚焦技术发展对人性影响的「科幻作家」。正是科幻作家的这种界分使得迪克的作品与弗诺•文奇的《真实姓名》、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乃至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2001》、斯科特的《异形》《银翼杀手》、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沃卓斯基的《黑客帝国》等并置,其作品中对现代社会抽象化、理性化的隐喻被掩藏,而技术对人与非人的界限的模糊则被凸显——迪克就此成为了「后人类」问题的先声之一。
实际上,迪克等人的科幻作品不仅描绘了「后人类」的状况,更是直接框定了「后人类」的问题域。恰如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如果没有《异形》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没有《神经漫游者》与《攻壳机动队》,那么在人类之后将只剩下一片弥赛亚般的虚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们无法想象一种真实的名为「后人类」的存在。不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术之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概念丛中不断演进并且直接在物质上型塑了「后人类」的诸多技术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后人类」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风中了。
然而塑造了「后人类」问题的诸多历史脉络却也成为了笼罩着问题本身的阴影。如前所述,今日的「后人类」问题更多关注着狭义的技术与人的关系,尤其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赛博身体、数据监控等等方面大展拳脚,仿佛这些问题乃是「后人类」问题的根本所在,人类的确面临着数千年来的大变局。不过倘若深入到科学或是技术领域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那里常见的诸多判断并不成立:今日的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远比不上工业时代与二十世纪之初;今日的创新虽然无所不在,却也都是攀附商业的微小创新,真正改变人类的创造却尚未出现;今日的计算机领域虽然蓬勃发展,但最基础的数学、物理等学科却已遇到了瓶颈,数十年来未出现大的突破性进展。至于科幻作品中常见的「后人类」惶恐,如果是在技术意义上,恐怕离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这绝非悲观的论调,无论是出版于世纪之处的《未来50年》(The Next Fifty Years)还是近来《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对近百位物理学研究者的调查[5]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所谓近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其实只是技术的进步,而并未涉及科学的关键性进展,而越是远离基础科学与技术生产的人群,越容易在商业与媒体的运作之下夸大技术的进步。恰如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知识的未来》中所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类的信息显著地超过了任何关于存在着的非人类系统的信息。」当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不再以外部世界为中心,而更多是关于人类自身。由此所谓的「革命」也不过就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渐进转型进程中的最新进展,这也正是近年来看似日新月异的技术的实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最了解的不是自然,而就是我们自身。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却大都将商业运作下技术进步与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图景相结合,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了一种「后人类」的惶恐。这种错觉一方面来源于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区隔,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缺乏对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的敬畏,并未试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实际进展,反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肌理,急于将表面的状况纳入到其熟悉的问题域(典型如伦理、社会分层与流动、资本主义等)中进行分析,如是得到的多半不是学术分析,而是天方夜谭。
诚然,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当下,想要弥合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或许日益困难,甚至可说是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我们仍需要寻找、培养那些可靠的能够沟通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样一群人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守门人」的职责,守护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此意义上,迪克可以说是最早的「守门人」之一:通过科幻作品的书写,迪克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使得科学与文化、技术与社会之间可以相互沟通,使那些传统的议题可以与新的时代相结合,使得我们有机会把握住技术进步的路径,导向一种真正属于人类的「后人类」未来。
不可遏制的客体
「总有一天,」乔愤怒地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推翻你,推翻你们自动服务机的暴政。人的价值、怜悯和温馨将回归社会。」——PKD《尤比克》
倘若抛开不同领域之间的区隔所导致的误解,在最为宽泛的角度上理解当下知识界对「后人类」的关注,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后人类」问题域的核心乃是一种「对客体的恐惧」。事实上,迪克的科幻作品中最为集中的意象便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摆脱的「客体」,无论那些客体被表达为集权社会、义肢、人工智能还是人造人,这些客体都必然导致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的模糊,进而造成了对身为主体的「我」的压抑。
某种意义上,迪克正是通过科幻小说的方式,洞察了现代性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在齐美尔、胡塞尔与昆德拉的论述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别不过是迪克作品中的「客体」并未有一个稳定的表征,而上述三人则集中地使用了客观文化/主观文化、科学/生活抑或是确定/不确定等范畴[6],希望将概念对中的后者从前者的压抑中解救出来。在此视角下,迪克故事中保有的人本主义理念或是那种怀旧恋乡感便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冰冷而抽象的现代社会的反抗。
然而迪克作品阴冷的基调却又指向了一种拉图尔式的对人/物关系的认识:人越是希望与物划清界限,就越是会与物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有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客体——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最后都成为了窒息个体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么说有些过分抽象的话,那么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话[7]来说,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便是:人类总不愿承认「手机」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时却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的过程。借用拉图尔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从未现代过」,更是「从未成为人类」,如果人类的定义是那个界限分明的主体,那我们早已是后人类了。
以此为入口,回到迪克的小说中,我们将发现,那些主人公们总是在寻找的、渴望的东西——无论是绵羊、历史,还是灵魂、身份——其实质都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真与假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界限意味着确定性,同时意味着意义存在与生成的可能。然而将一切希望寄托给界限的存在,故事便会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宫之中发现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庞然大物,发现自己无法理解世界的存在,从而失去自我——在《仿生人》中,里克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不过在整本书的末尾,当妻子伊兰给里克带回的电子蟾蜍订购电子苍蝇时,迪克已部分地超越了卡夫卡的视野,曾经需要通过无限倒退来找寻的人与仿生人之间的界限被搁置了,在那些模糊的、断片式的场景中,迪克一样发现了美与意义的存在。
在对《仿生人》的评论中,凯瑟琳•海勒将这一故事的结尾看作迪克中期创作中对人/物界限的关键性思考,即从人本主义走向人与物的混合。由于科幻作品的普及,类似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身体改造等等人物混合的赛博格形态在大众文化中已屡见不鲜,甚至早有科幻作品将重心放在「硅基生命」而非「碳基生命」上,视角不可不谓先进。在此意义上,现代科幻既是现代社会的守门人,提醒大众技术的后果;也造成了大众视角的偏移与脱敏,使关于技术的讨论有极端化的趋向。
实际上,在「后人类」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并不是那个长远的未来,而是更为切实的对当下技术进程的控制。不过控制既不意味着彻底杜绝,也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更应是综合考虑技术发展的现状、技术的商业应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上的潜在结果后的关注与行动。不妨这么说,越是在讨论那些看似宏大的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我们越应将目光不断下放,直到看到那些历史地层中的雨露尘埃,那些世间万物的参差多态,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那些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流吧,他的眼泪,这正是迪克故事中的关键所在。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Like tears in rain. ↩︎
《The Search for Philip K. Dick》P27 ↩︎
PKD给短篇小说集《金人》所作前言,翻译引自陈灼。 ↩︎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8/11/diminishing-returns-science/575665/ ↩︎
分别参见《货币哲学》《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小说的艺术》。 ↩︎
出自一次对押井守的采访:「我觉得这已经是现实了。在座的所有人都有手机,我也有,现在只不过是把手机放进大脑里的问题。不管是在衣兜里还是大脑里,反正你离了它就活不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人类必须去适应科技。它也许只是在你的衣兜里,但那实际上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