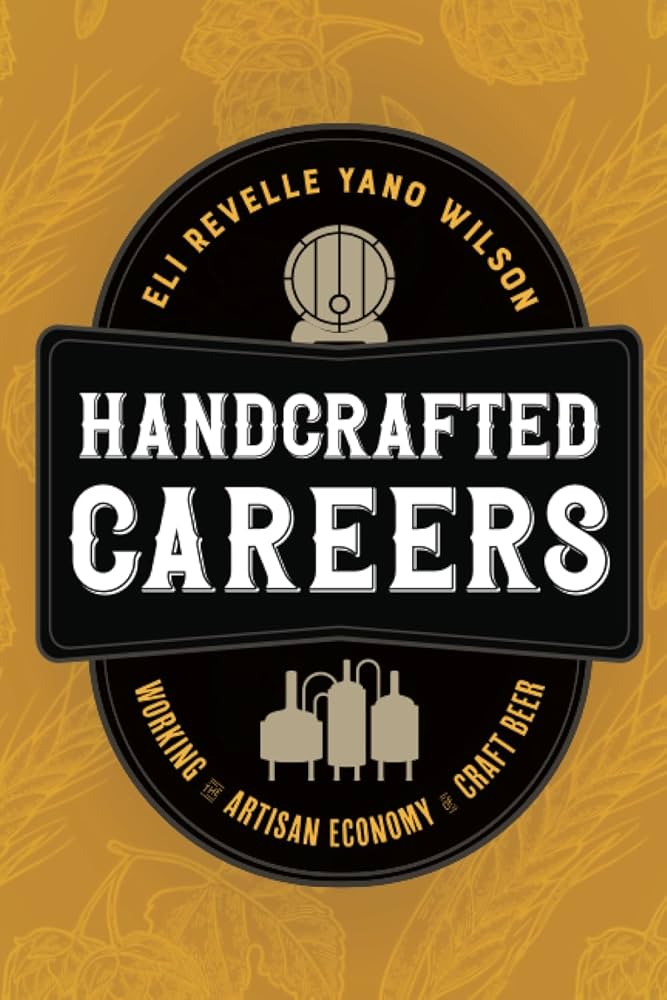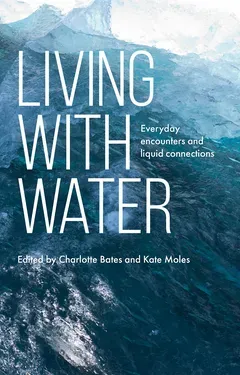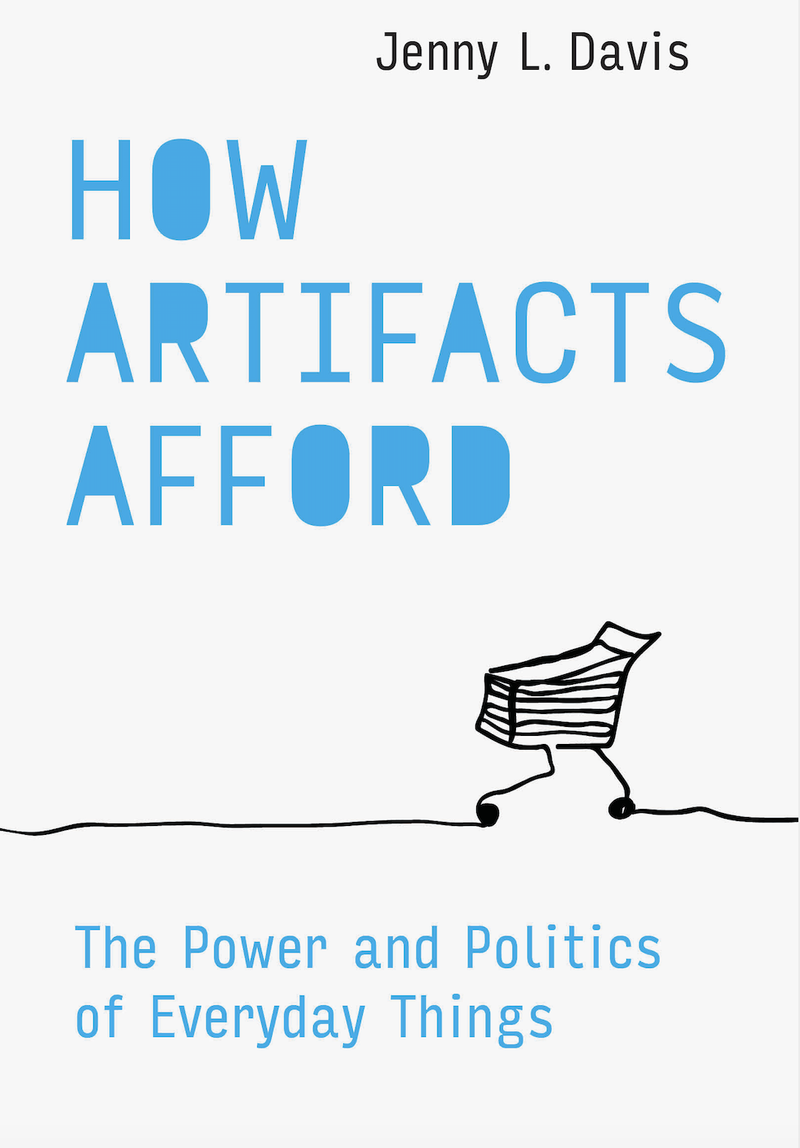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我觉得这已经是现实了。在座的所有人都有手机,我也有,现在只不过是把手机放进大脑里的问题。不管是在衣兜里还是大脑里,反正你离了它就活不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人类必须去适应科技。它也许只是在你的衣兜里,但那实际上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了。」——押井守
消失的身体
当启蒙的光亮划过夜空时,那些点燃火把的哲人或许从未想过,将会有那样一个时代,在那里,人人都成为了自己的未来学家,街头巷尾流窜着关于下个世纪的预言,人们已然相信,现在是属于未来的,而未来则属于技术,与技术同构,甚至就是技术本身。在未来的威慑下,过去不再统摄现在,历史因此失去了效用,启蒙连带着它所发明的「人类」「理性」等诸观念一齐滚进了廉价的碎纸机,人们要做的似乎只是等待,等待未来如期到来——尽管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日期,而自己又是否真的收到了它的邀请。
面对愈发流行的技术/理性崇拜及其附属品,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To Became Posthuman)中,凯瑟琳•海勒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调转了先辈们指向未来的矛头[1],以一项简单的时态变换(Became)预言了在「后人类」论域中去历史化的失败——过去时态同时表达着从人类到后人类这一变迁的历时性(我们早已成为后人类)与偶然性(我们还可能设想/成为另一种后人类)[2]。
概括来说,海勒想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主题:如果没有《异形》与《银翼杀手》,没有《神经漫游者》与《攻壳机动队》,那么在人类之后将只剩下一片弥赛亚般的虚空,除了抽象概念外,我们无法想象一种真实的名为「后人类」的存在。不仅如此,倘若失去了技术之外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概念丛中不断演进并且直接在物质上型塑了「后人类」的诸多技术思潮也未必如期而至,「后人类」本身便就此消散在风中了。
基于技术语境与文化语境的相互交织,海勒在将历史复位的同时,力图同时对抗技术迷狂式的未来妄想[3]与自由人本主义式的田园牧歌[4],将「后人类」的重心从「后」转换到「人类」,构筑起一种开放的、共享的后人类图景[5]。作为对这种图景的佐证(也是唯一的证明),海勒试图讲述三个相互耦合的身体故事:信息如何失去了身体(物质性)、赛博的身体(Cyborg)如何在战后被建构以及人类如何转化成为后人类[6]。三个故事分别涉及到控制论的三次浪潮(技术叙事)、战后科幻小说的发展(文学叙事)与两者交织下的后人类想象[7],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毫无疑问是控制论的发展,而贯穿三个故事始终的则是一种去身体化与去语境化趋势(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从「在场/缺席」向「模式/随机」的转化)。
不过正如海勒所描绘的那样,去身体化与去语境化的趋势很可能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在奠定了人机交互基础(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上,并非仅有维纳(Noebert Wiener)、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等信息实体论[8]者,同时也存在着麦凯伊与库别等强调信息必需要一定载体/语境中才具有意义的与会人。信息实体论最终的胜出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并未能使涵盖语境的信息进入机器系统之中,而落后的技术转化出的工业标准又反过来强化了信息实体论在整个控制论领域的地位,最终型塑出某种仿佛不可抗拒的趋势,循环解构了信息的身体(物质性)。
承接信息实体论的,是六十年代后的第二波控制论浪潮,在这轮讨论中,基于麦卡洛克等人对于青蛙视觉的研究,生理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的认知系统可能并非是在「反映」世界,而是在「建构」世界[9]。从「反映」到「建构」的变化暗示着观察者角色从系统的外部进入到系统之内,甚至成为构造了整个系统的核心——这种角色转变进一步被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米德(Margaret Mead)与福斯特(Heins von Forster)等人逐步发展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反身性」(Reflexive)理论,并在马拉图纳(Humberto Maturana)与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处演化成了一种内部系统为核心的自我组织理论,破坏了世界本身的确定性[10],同时也通过将「自我」(主体性)转化成某种可量化的可生成的产物[11],构筑起了赛博格的理论可能。
不难发现,第二波控制论浪潮(尤其是自我组织理论)本身带有一种保守性质,无论是反身性还是自我组织都天然要求某种「稳定性」,用以维持观察、中止观察或是确保组织系统的有效性[12]。针对这种稳定性,第三波浪潮在自我组织的过程中「增加了一种向上的动力」[13],于是人工生命(AL)得以发生突变、进化,甚至可以完全脱离人的身体想象(碳基),成为以形式(数学本质)为基础的硅基生物(程序生命)[14]。在这里,人工生命、人工智能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定义都被彻底地去物质化了,只需要某种可堪计算的形式构成,一个生命即可诞生[15],而这也就最终打造出了今日大众所见的去身体化的后人类论域。
分裂的写作
整体来看,海勒试图将上述三个故事以一种回旋式的构成分布在全书十一个章节中:去除首尾两章,中间九章大致按ABC/A’B’C’/A’’B’’C’’的顺序进行,其中A是控制论(技术叙事),B是控制论的应用(中介),C则是科幻小说分析(文学叙事)[16],随着ABC的回旋,时间从战前逐步推演到世纪之交,原本模糊的理论视野也逐渐清晰,呈现出了作者的核心意旨,即对后人类论域中的具身体现(embodiment)的倡导。
这种结构上的刻意似乎说明,海勒不仅理解「叙事」对于理论与现实的重要性,并且深谙此道[17], 甚至可以说是乐在其中[18]。不难理解,海勒既然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描述一个堪称史诗般的去身体化的过程,也就不会放弃这种描述(叙事)所带来的批判空间,回归具身体现自是情理之中。然而正如其文风所暗示的那样,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至少掌握了大量后结构主义工具)的海勒一帆风顺地解构了后人类论域的去身体化与去语境化,但却始终未能建构起一个说得上稳定的理论基础——并且更为不幸的是,在相当程度上,海勒或许并未意识到,她这种可以被称为「温和/人道未来主义」的田园诗般的姿态(后人类与人类可以和平共处,同享家园),相当程度上也来源于历史的建构,并且由此陷入了去历史化的自我批评之中[19]。
海勒对于控制论及其应用的叙事抱持着一种福柯式的态度[20],这种态度显然不能支撑她总在每章末尾提出的其实相当缺乏建设性的建设性论述,于是全书中唯一具有建构性的便是其文学叙事的部分。与此同时,海勒并不愿完全转向布迪厄的惯习或是埃利亚斯式的历时性分析[21],而是始终坚持着一种去历史化的话语观念,且认为这种观念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建构起人的身体。这种在自我学科背景与理想理论路径间的游移最终导致了全书末尾出现的堪称致命的尴尬:海勒仅仅解释了「后人类可能不是反人类的」,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精心勾勒另一幅有助于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长期生存的图景」[22],更无法证明这个图景在文学领域以外的真实性。
不妨进一步考虑海勒在书中进行的三处文学叙事:在第十章中,四个文本由于非常直接地对应了四种后人类境况,因此海勒的分析简明扼要,直接从剧情进展到了理论,最后略显无力地支撑起了结论;但对于第五章与第七章,即便我们能自动过滤掉那些由女性主义、后殖民与精神分析等理论构筑起来的大杂烩式的分析[23],并且承认海勒对于《地域边缘》与菲利浦•K•迪克60年代中期作品的分析确实有力地触及到了一些当代后人类图景中的关键问题——我们也很难看出,除了通过叙事的自我增殖来达成论证外,海勒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将一个单纯的故事(文学与技术相耦合)讲得如此繁复[24],并且宛如孤岛一般,与上下文并不构成实际的联系[25]。
如果要以海勒式的风格进行分析,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写作恰恰说明了,海勒其实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整套分析与基于其上的解决方案(「温和/人道未来主义」)建构性,然而这种最基本的确定性却是海勒始终希望维持的,她害怕一切坚固的真如自己暗想的那样烟消云散了,她始终希望保存着一些「人本」的特征,作为一个稳定一切的核心——因此即便她在解构控制论变迁时昂首挺胸地表示自由人本主义已亡,她也并不能真的放弃人与人性,而是转过身去,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的工具箱中抽出一些名为开放与包容的特征,将之重新包装在人性之上,并以文学叙事加以佐证,仿佛祭祀一般召唤着自己希望的未来。
他者的幽灵
如果考虑到18世纪的人类机械论[26]、19世纪的社会机械论乃至20世纪的人类生态学、结构功能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海勒所处理的控制论问题不过是一个漫长的链条上较靠近当下的一环,它可能自柏拉图开始,也可能是围绕着笛卡尔式的循环,但无论如何,海勒所进行的工作甚至其工作形态都并非是开创性的,而是四处弥散着他者的幽灵。
粗略地说,海勒所勾画的线索中最为核心的一条,即是自我界限的逐渐开放[27],而这一过程却早在齐美尔处就得到了说明[28]。类似的,在海勒来看扭转了整个控制论走向的反身性的相关理念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分别在希尔伯特(数学)[29]与米德(社会学)[30]等人的论述中得到相当的呈现。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证明上述观念出现远比我们的说明要早,不过这并不重要,就像海勒解构控制论的去物质化那样,我们仅需要说明,海勒将被建构出的研究方法当作了某种叙事真实,并理所应当地以控制论作为开端展开其论述,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资料取舍上的一些困境,最终使得她倾向于高估控制论在整个后人类进程中的意义。
这种有趣的可能性在相当程度上暗示着,与其将海勒的著作当成某种严格的理论,毋宁将之视作某种不甚光彩的后人类实践。尽管采取了类似的论述方式(祭祀式的召唤),但脱离了六七十年代文化语境,海勒已经失去了马尔库塞式的抵抗能力,而与这一文本也就如她所描绘的后人类那样,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变革的能力与冲动,但所有的变革却都只是在将话语不断进行重复与繁殖而从未介入它本身一直倡导的「具身体现」的领域。对于那些真正需要抵抗的宏大问题[31],这一文本(包括了物质的文本、海勒的个人思想与其中内嵌的科幻小说等多重含义)仅仅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技术、工厂、杀戮、白人男性形象等符号进行多重勾连[32],再从工具箱中挑选最合手的,以抵制其中之一便是变革全部的逻辑展开对这一系列内容的虚假否定,最后通过一项「倡议书」来证实自己的变革性[33]。
如果将海勒所遭遇的分析困境与文本中分析的控制论困境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维纳的自由主体性困境与马图拉纳的组织结构困境等都遭遇了自由主体性与控制论之间的冲突,并且都选择了将控制论隔离在社会领域之外,借此规避其中的道德风险;那么海勒所面临的状况则是在控制论本身都难以得到形式化保障的前提下[34],如何确保后人类相较人类获得了某种人本意义上的解放[35]?如果可以证明上一点,那么如何证明此处的界限处于不停变换中的「后人类」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本质,并且可以被正确的把握?
不难看出,海勒的理论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自由人本主义的结果性预设:当她宣称一个被组合在系统中的人只要能够与系统相结合施展出更多的判断能力(构成一个分布式认知系统)时,这个人即可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后人类[36],她也就默认了对于「人类」这一概念本质来说,认知的价值高于生产/实践,不然就应当是一个分布式生产系统或者一个分布式综合系统;同时她还假定了,这个人应当可以选择是否与系统进行耦合,与何种系统进行耦合,只有如是系统才能是「分布式」的而非「集中式」的。
当我们揭开海勒的理论预设后,我们将发现,与她所宣称的状况截然不同,她所提倡的理论与其说是对自由人本主义的变革,毋宁说是自由人本主义在当代状况下的特殊变种。对「认知/智力」的推崇与对个人自由的基础假定都说明了,海勒并未意识到,她所谓的「后人类」状况并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而应当是一种「后-人类」(post-human)状况[37]。在这一状况下,「后人类」与「人类」甚至「前人类」并存,而真正的「后人类」——不妨直接挪用海勒对自由人本主义的批评——只是那些「有财富、权力和闲暇将他们自身概念化成通过个人力量和选择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的那一小部分人」[38],即便海勒极力否认她描述的状况中存在这种自由意志[39],可是既然她以一项呼吁结束全书,那么她必然承诺了从人类向后人类转化过程中的选择权。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那些没有选择权的人,他们被排除在了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后人类游戏之外,在理论与物质的双重贫困中供养着他者的具身体现[40]。
在这里,人类确实与后人类「共享了这个星球甚至他们自己」[41],但这一切都不再如海勒所勾勒的那般温情脉脉,而是略带嘲讽却又隐然惊悚地向你发问: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
设想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文化悲剧」)、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其共同特征都是在论证技术/理性未来(相当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式的)的缺陷。 ↩︎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P8.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P9.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115.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94.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94.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8. ↩︎
简单说这意味着承认信息可超脱于载体存在。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174.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10.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07. ↩︎
例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07的「裁决程序」,容易得知,「裁决程序」本身必须是稳定而非随机的,不然便无从裁决。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98.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15.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11. ↩︎
详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7-28. ↩︎
另一个例证是书中对瓦雷拉等人著作类似结构的分析说明。例参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204. ↩︎
不然不会如此刻意地在开头与结尾反复提示全书的结构特征。 ↩︎
「文学研究……存在一个重要的盲点……」 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84. ↩︎
从导言与第八章来看,海勒应当相当熟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p274.海勒很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学科背景去进行这种转向,尽管这两种方法在身体理论研究者看来是找回具身体现的较好的理论路径。参见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94. ↩︎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另一问题是书页中俯拾即是的翻译错误。考虑到原文和翻译都有些问题,我宁愿相信,尝试自动过滤并不比尝试读懂显得更「后人类」。 ↩︎
或许还可以暗示自己与某些法国后现代理论叙事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 ↩︎
这两个章节如此密集地聚焦在了女性(女性主义)、性(精神分析)等话题上,可这类话题在此后都并不在讨论中心,除去温情脉脉的召唤外,在此讨论如是内容的意义也未得到充分说明。 ↩︎
代表作为拉·梅特利匿名出版于1748年的《人是机器》(Man a Machine)。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115. ↩︎
「事实上,人方方面面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行为,都处在两个界限之间,这一点决定了人在这世上的定位。」 参见齐美尔《货币哲学》。尽管齐美尔此处所说的是个人的定位与界限的关系,但齐美尔显然也意识到了个人的位置对于自我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 ↩︎
参见塔西奇《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p107. ↩︎
参见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p203. ↩︎
按《雪崩》的描述,涉及到95%的人。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69.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90. ↩︎
典型的如对《雪崩》与《地狱边缘》展开的分析。 ↩︎
尽管海勒似乎仍旧相信控制论的数学前提,只是认为缺少物质的控制论不可能完善,但是控制论的数学失败已被数学家查尔汀在六十年代以「停机概率」问题的形式证明,简单来说,即永远不存在一个能够判断所有「真」的系统/机器,真理性与可论证性并不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是控制论的理论保障。参见塔西奇《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p121。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88. 海勒给出的是某种资本主义式的回答——即算法提高了工作、生活效率。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93. ↩︎
在这里我化用了特斯特对于后-现代性(post-mordenity)的用法。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P388. ↩︎
同上。 ↩︎
例如第三章末尾海勒所说的珍妮特•弗雷德/弗洛伊德。 ↩︎
参见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p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