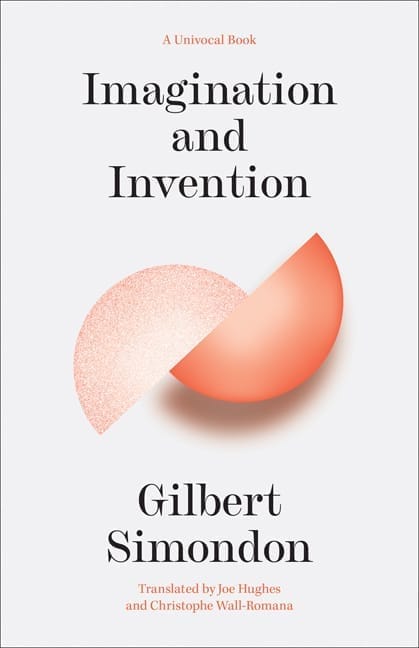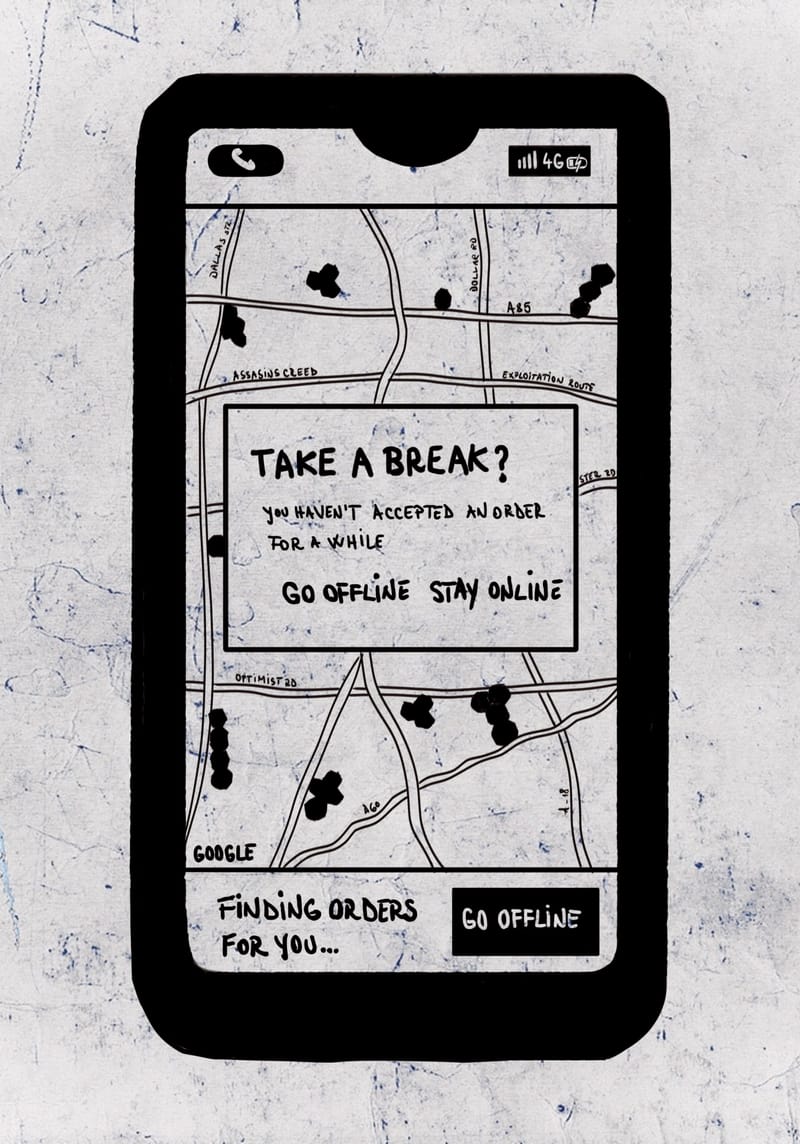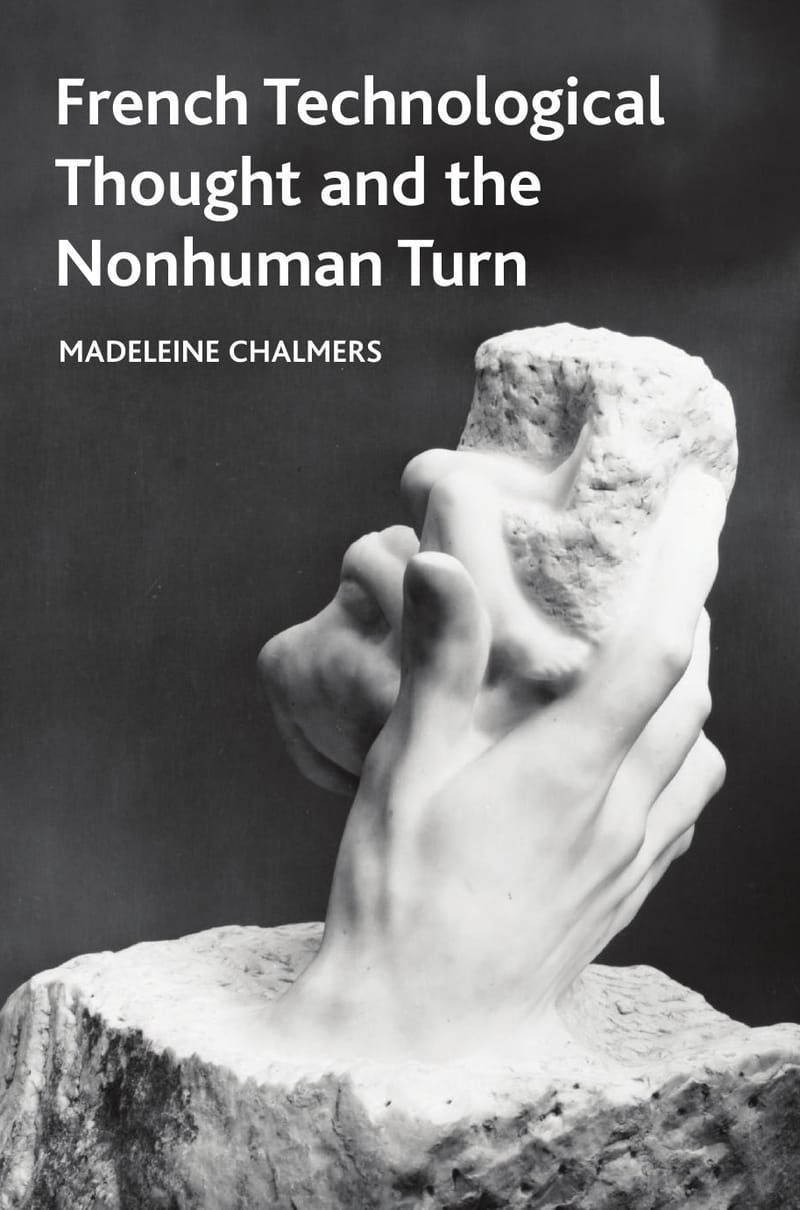结论
回顾
本课程的前三部分研究了意象(image)在直接循环的各阶段中的生成(genesis)。这个循环包括了所考察的心智活动中一个亚个体成分(component)的生长、发展和饱和(saturation)等阶段,它或多或少与有机体或更大有机体中的一个器官的发展过程相类似。最后一部分则试图展示,当该成分达到饱和点时(这个饱和点取决于每个生命体组织信息的能力),会在一个全局性的关键过程中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当其结果为正向时,我们就称之为发明。这种改变同时也是量级(magnitude)的改变,它通过建立亚个体要素(处于符号状态的意象)与超集(super-set)的指导方向之间的互惠关系来实现。在前三个阶段中,这种超集并不是以现实状态存在的,而只是以约束、限制或生命体外部信息源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发明是由内部兼容性的需求所诱发,它通过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确立来实现和表达,而作为其子集的生命体(living being)则被包含在这个系统之中。
从形式上看,发明与环境(milieu)改变相类似(寻找新环境的愿望实际上是发明失败的一种替代),但发明与之前的意象的区别在于它实现了量级的改变;它并不作为心智装备(equipment)的一个成分停留在生命体之内,而是超越了生命体的时空界限,与它所组织的环境建立联系。通过发明而实现的超越个体主体的倾向,实际上已经潜在地(virtually)包含在意象循环的前三个阶段中了;在与事物发生经验之前,运动倾向的放大性投射就已经是一种在世界中展开(deployment)的隐含假设;作为接收偶然信息的主观系统的知觉类别,预设了一种普遍的应用;最后,记忆意象的符号性联结,虽然它以向心的方向表达了主体对构成其历史的诸情境的依附,但它更重要的是为可逆性的运用做准备,这种可逆性将这种联结转化为通向事物的途径。在其生成的这三个阶段中,心智意象都不会被承载它的个体主体所限制。
这种相对的外在性,经由被创造的事物(created objects)在发明中得以实现。这些被创造的事物充当着环境的组织者,它们并非物质化的意象,也不像其他事物一样被任意置于世界之中,仅仅为自然增添一个人工的补充;就其起源而言,它是(并且就其功能而言,它始终是)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一个连接系统,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得以交流的一个双重点。在社会性物种中,这个点是三重的,因为它成为了个体之间关系的通道,组织着它们的互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三重点也是一个社会组织者。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被创造的事物的系统——在两种关系的视角下,一方面是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该系统的运作,自然趋向于成为兼容领地的有组织超集),另一方面是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作为一个功能的超集,可以形成协同组织)——构成了个体的包络(envelope)。
当前提议的含义
首先,值得指出被创造的事物的相对特性;被创造的事物实际上是环境中的一个点,这个点被有机体的定向活动重新组织了。我们既不能将人类的建构性操作与动物的操作对立起来,也不能将制造比有机体更小且由其承载的工具,与在作为有机体环境的领地中建立道路、路径、储藏或界限(这些都大于有机体本身)对立起来。工具和仪器,就像路径和防护一样,都是个体包络的一部分,并中介着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必须从拓扑学的角度来描述这种中介。无论是器械、工具,还是领地的特定结构,承载着发明活动结果的事物都被赋予了连贯性、连续性和内在兼容性,同时也获得了与环境中未经加工的剩余部分以及与有机体的兼容性。这两种外部兼容性——与「野生」环境和生命个体的兼容性——是内在兼容性的结果,正是这种内在兼容性使得单一事物能够同时执行多重功能。一条道路要按照内在兼容性而存在,就必须作为物理事物而具备连贯性和稳定性(不透水性、地面承载力的均匀分布等),对这种内在兼容性的追求首先表现为有意识和有意志的发明的目标:根据所用材料的不同,可能有几种兼容性的方案;罗马道路建立在一个刚性多层系统之上,它的建造方式就像建筑物一样;今天的道路则是相对弹性的构造,但它们必须具有极强的防水性和最佳的排水性能;它们的方案在于表面的柔性连续性,而不是那么注重每个支撑块的坚固性。当它们老化时,罗马道路是一块铺路石一块铺路石地被侵蚀,而现代道路则会在长距离上产生起伏或褶皱。对主体来说,外部兼容性可以概括为对特定流通和运行方式的适用性(马车不能有陡坡但可以有急转弯,载重骡子、快速机动车等也各有特性):这是对生命体的适应特征,无论是直接适应还是通过新的更小的中介(车辆)来适应。对总体环境来说,外部兼容性产生于道路的布局,这种布局要考虑地形的起伏和构成,包括雪崩、泥石流等风险;作为一种再造的表面(resurfacing),道路发展出补充性的中介来连接它与周围的野生环境:桥梁、高架桥、隧道、树篱、防雪崩加固、预防性种植,有时这些中介会延伸到很远的距离,就像前哨站一样。因此,内在兼容性——它使道路成为一个连贯的建构——表现为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双向转移(transfer)系统;当这种兼容性建立起来后,它既使个体能够连续地穿行于环境之中,反过来,它也使工程结构、安全性和防护得以保存和加强。被创造的事物的这种自我构成的特征如此强烈,以至于发明通常是一种以非套套逻辑的方式(non-tautological way)来处理问题,把问题视为已解决;如果一条道路已经建成,那么在几英尺之外建造另一条道路就会容易得多,这要归功于机器、工人和材料运输的便利;解决方案在于将这个「已解决的问题」等同于一系列相互促成的分级操作,直至完工:平整、铺设碎石基础等,直到最后的路面层,而其收尾工作需要一个已经完全平整的路基。被创造的事物被连贯的、相互连接的操作累积组织起来,这使得「野生」环境的量级更接近于个体操作者的量级。因此「被创造的」这一范畴比发明更宽泛,因为只要在个体与环境之间出现了累积性和连贯性的组织效果,带来了一种中间性的中介模式(intermediary mode of mediation),它就会应运而生;但它也能整合发明,这是由于被创造的事物具有内在连贯性和多重兼容性的特征,当能够使用「已解决问题」的方法时,这种特征就能得到最优的发展。被创造的事物的进步在于事物内在兼容性的发展,这扩展了环境与生命体之间耦合的范围:例如,所有作为人类起源的交流手段的被创造的事物,都遵循这种发展,它们源自从前使用的自然路径,但越来越趋向于内在的兼容模式,这使得对自然环境的渗透(penetration)更加广泛和普遍。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考察每个被创造的事物,而应该考察它们所形成的中介宇宙,在其中每个事物都部分地作为其他事物的手段。
如果我们将被创造的事物视为生命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中介,那么在动物物种和人类之间找到发明的联系就不那么困难了;虽然动物中使用工具确实相当罕见,但我们并不必然要将工具的构建和制造视为发明的最重要例证;器械和工具只是被创造的事物的中继,是被创造的事物与创造它的生命体之间的又一层中介。由于大量动物要么具有专门化的器官,要么具有与这些器官相连的专门化的操作模式,考虑到这种预适应,工具性中介就不是必需。操作模式和器官与创造事物的活动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比如筑巢、挖掘巢穴,以及更普遍的领地构建。只要一种确定的活动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s)了自然世界,赋予它一种表达生命体在行为选择模式下存在的拓扑,被创造的事物会存在。简单的视觉或嗅觉标记已经代表了一种连贯的划界,这种划界本身与其他活动(休息、觅食、庇护等)在功能上相连的位置有关。同样,标记在物种内和物种间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了意义。最具体和最完整的被创造的事物(如巢穴和洞穴),既是物种内和物种间社会关系的结合点,也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中介。在某些情况下,被创造的事物具有高度多功能性,例如白蚁丘,除了具有巢穴的一般功能(温度调节)之外,它还通向白蚁工作的事物。被创造的事物首先是一个被组织成领地的现实世界(world as a reality);它也是具体的个体存在的包络,这种包络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某些物种来说,被创造的事物几乎与有机体融为一体,就像珊瑚一样。珊瑚的共骨(coenenchyme)是一个被创造的事物还是一个有机体?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理解了生长功能与创造活动(发明是其中的一个物种)之间的连续性;生长和发明在被创造的事物的网络的生产中趋于一致。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创造事物的当前能力上,人类与最具天赋的动物之间至少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人类中,被创造的事物与自然之间,以及被创造的事物与操作者之间的中介发生了倍增(multiplication);从自然到人类和从人类到自然的双向通道网络显示出无限的吻合(anastomosis)和大量的中继;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的沟通和互动的量级远大于动物领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性白蚁),操作者的活动也无法利用复杂的中介链。在动物物种中,唯一可以看到与人类多重中介相当的等价物的角度是个体的解剖生理专门化(anatomicphysiological specialization),这些个体要么合作工作,要么在其生命过程中连续专门化(蜜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遇到了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和有组织循环的特征,一如我们在心智意象趋向发明的过程中所见。
在被创造事物的分析所提供的这种视角下,心智意象的研究可能成为对更大范围现象研究的一个特例;正是通过发明的最终阶段,心智意象的循环可能揭示它属于自组织活动过程的一般范畴,其中一个在人类社会中的主要方面就是工作的组织。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心智意象最初是如何在运动倾向的向量引导下(这个向量预示着与事物的遭遇),被外感受信息所充实,然后被形式化为现实的符号,以作为有组织的发明的基础。
为此,除了那些壮观的、大规模的重组在社会中传播并成为新的标志性事件的特例之外,还有一个持续的隐性重组网络,它们交织在工作中,但既没有普遍化也没有传播到其预期应用领域之外;然而,这些微小的重组也是发明,分布在任务中的发明的力量,每一个都太微小而无法传播到情境之外,却也可能与一次性组织情境及所有类似情境的大规模发明行为一样重要。在动物创造事物的活动中尤其如此,这种活动在执行过程中细致地调整任务本身以及任务与环境的关系;手工生产也是如此。每个任务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组织行为,如果每个行为的范围都小于任务的维度,那么被创造的事物就本质上依赖于其插入环境的特定条件、其目的以及其实现的特定手段;这些发明不会超出操作者的范围,操作者可能在类似任务的过程中重复它们,但不能将它们形式化为绝对的东西;这就是动物或手工活动的情况,其中发明分布在整个执行过程中。相反,如果发明行为集中在几个任务之上,它就被形式化为可与其执行条件分离的发明,就像在工业工作中一样。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是艺术品与有组织的发明之间的维度适配:被创造的事物在单一行为中被完全组织,没有残余或模糊区域,但这个行为不超出被创造事物的限制,因此它仍就特殊和独特:艺术事物,作为手工制作和工业操作之间的稳定中介,是一个完全组织的事物,在这方面既独异(singular),却也绝对(absolute)。在手工事物中,发明保持在任务执行的限度内,带来部分的组织性联结;在工业事物中,发明超出了任务的执行;在艺术品中,发明和任务的执行同时发生,并具有相同的维度。
因此,对心智意象和发明的研究引导我们走向实践学(praxeology)。根据阿尔弗雷德·埃斯皮纳斯(Alfred Espinas)在1880年发表于《法国与国外哲学评论》(La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上题为《技术的起源》的文章中的定义,实践学是「研究所有生命体中最普遍的形式和最高的行动原则的科学」。实践学连同斯卢茨基(Slutsky),继而是博格丹诺夫(Tectologie,Moscow,1922)的研究,已经朝着经济和人类活动组织的方向发展。霍斯特莱(Hostelet)也确认了这种朝向人类活动研究的趋势,同样还有塔德乌什·普什乔洛夫斯基(Thadée Pszczolowski)在《有效行动原则》(Warsaw,1960)中的研究,这部作品被科塔尔宾斯基(Kotarbinski)在《实践学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raxéologie)中引用。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将人类与动物分开,将功利性行动(utilitarian action)与一般行动分开之后,实践学可以发展成为一般实践学,整合最基本形式的活动研究,这实际上与埃斯皮纳斯的其他研究很相符。在这个节点上,趋向发明的心智意象循环可能显现为生命体活动的一个高级层次,即使在其最原始形式中,这种活动都被视为与环境互动的自动运动(autokinetic)系统。在较低等生命形式中通过运动主动性表现出来的自动运动特征,在具有复杂神经系统的生命形式中则借由功能的自发性来转译,这种自发性在与事物相遇之前就触发了意象循环,并以发明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