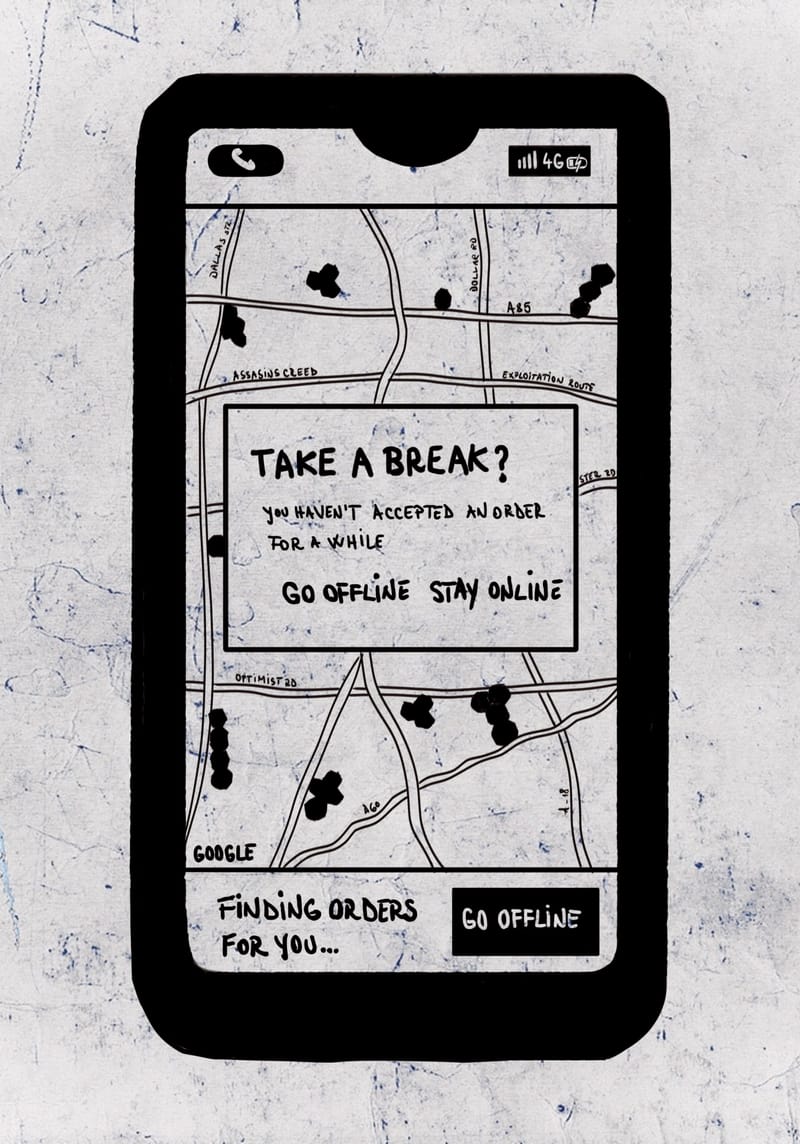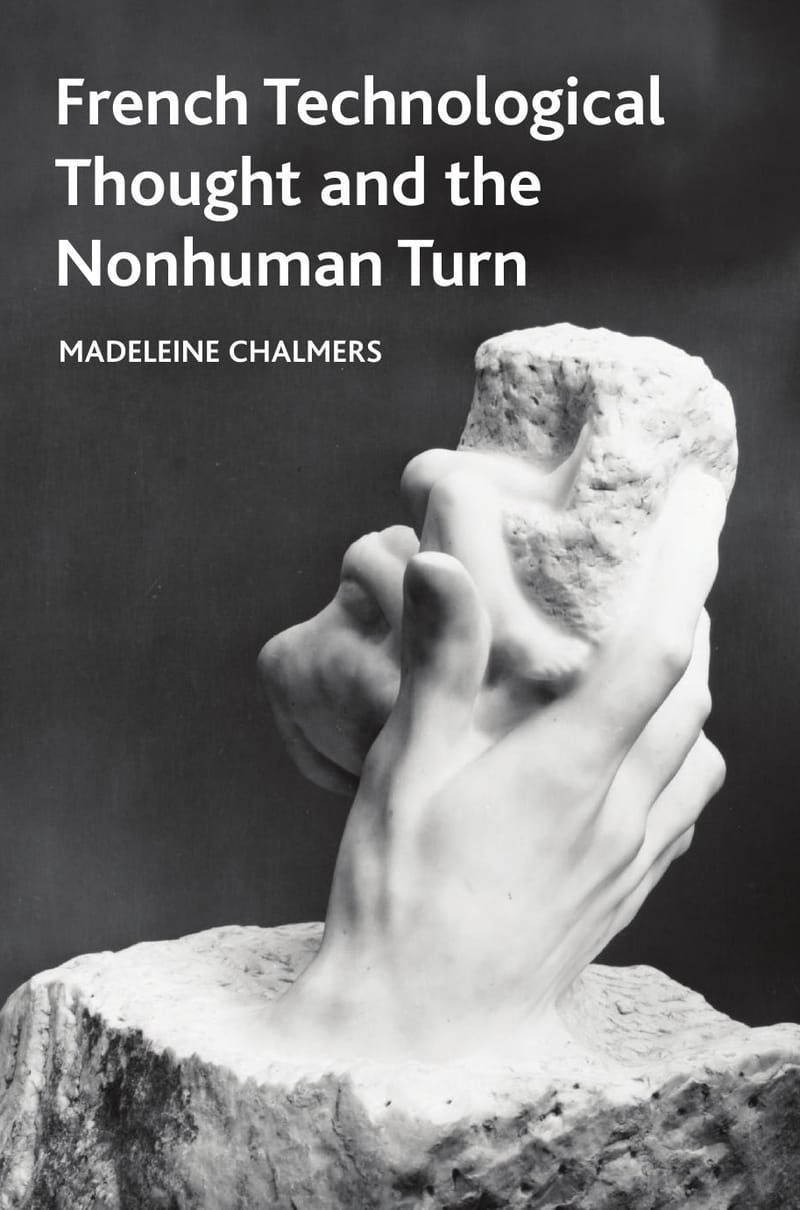翻译自英戈尔德《带着示能理论重返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with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原文是对韦伯·基恩(Webb Keane)另一篇讨论示能的文章的回应,篡改题名为 1979 纯属无聊玩梗,当然也是吉布森代表作的出版年份。翻译出来主要是看一堆讲示能的新书看得头大,在英戈尔德处找找安慰。谁能想到直到今天,英戈尔德还是社会科学中为数不多读懂吉布森意味及其局限的学者。
示能(affordance)概念由心理学家吉布森(J.J. Gibson)提出,是其独特的生态知觉(perception)方法的核心。与主流心理学的认知主义截然相反,吉布森方法的前提是知觉并不源于封闭在身体中的心智的工作,而是来自于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 (不可分割的心智和身体) 与其环境的积极互动。这个有机体通常被假定是某种动物,但对吉布森来说,这个动物是人类还是非人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类和非人类来说,知觉都关乎生存于世(being alive to the world),在其中移动、关注它,并在过城中发现它能提供什么,无论有利还是有害。这些被提供的东西(offerings)就是吉布森所说的环境示能。
示能是延续生命的方式,又或者是是阻碍生命延续的东西,它们是机会与障碍。它们并非知觉的产物,因为对吉布森而言,「知觉」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它不会产生终点。如同生命一样,知觉延绵不绝(carries on):它产生的不是感知物(percepts),而是作为知觉者的人类(perceivers in person)。它调谐了他们的注意力。示能是事物呈现在知觉者面前的方式,不是作为自在之物,封闭和受限,而是作为延续某种生命形式(form of life)的潜能。因此,对示能的感知与在其实现之中行动并未分离,也并非一前一后,而是同一:行动即关注。在对示能的知觉中,按照吉布森的说法,生命与世界进入了一种直接且无中介的关系,正如世界向其生命居住者开放一样。正是在这种开放中,世界成为了环境。
那么,示能理论能给人类学带来什么?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通过吉布森最出色但英年早逝的追随者之一艾萨克·里德(Ed Reed)接触到生态心理学。我对此很感兴趣,深入研究了相关文献,并开始参加将该领域实践者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争论的「事件知觉与行动」(event perception and action)国际会议。尽管他们在反对认知主义的立场上保持一致,但我发现他们内部存在激烈分歧。这种分歧的种子早已在吉布森的开创性著作(Gibson,1979)中播下,他在其中同时提出了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其一,我们可称之为「实在论」立场,认为环境中的事物(object)因其所是而具有示能;也就是说,示能是事物本身的内在属性,不管是否有生命体在那里实现它们。它们为生物在环境中定义了一个生态位(niche);即使移除生物,生态位依然存在。另一个立场,我们可称之为「关系论」,认为示能只有在被某个生物实现的活动中才存在,对该生物而言示能才有意义。没有生物,就没有示能。吉布森想两者兼得,坚持示能既真实、客观、物理,又是环境的属性——这里的环境与物理世界明确对比,只对生活其间的生物才构成一种环境。
对生态人类学背景出身的我来说,我相当理解此种分析。因为在我自己的领域中,我也遇到了一个僵局。这涉及文化在人类适应环境中的作用。环境是一个自然给定的东西吗?是人类居住者通过文化为其设计适应性解决方案的一组客观条件吗?还是说,世界只有在被纳入文化制约的实践范围之内时,才成为人类的环境?适应的条件究竟是在哪一边设定的:自然还是文化?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争论,将物理实在论与文化建构论对立起来。但当我聆听生态心理学家们的争论时,我在想,示能这个概念如果摆脱实在论更为严苛的信条,或许能提供一条出路。
我在 1992 年首次尝试思考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与环境知觉」(Cult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的论文(Ingold,1992)。其论点简而言之,就是对示能采取关系论的进路,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语言来表达人们如何不断地带出(bring forth)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人(environments people),从而摆脱自然这个普遍给定世界与文化建构的多样化世界之间无休止的自我复制二元论。用示能的语言来说,人们的差异不在于获得了多样的概念图式来组织无序的身体感觉原料,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表征,而在于通过实践的知觉与行动技能,对一个世界的特征保持不同程度的调谐(attunement),这个世界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动不断呈现出来。
正如非人类生物一样,人类也能与世界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而无需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范畴来中介。简而言之,文化并不介于人与其环境之间。两者之间空无一物。在那篇文章中,我一时脑热,把话说过了头,认为处理文化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简单地将其从生态学等式(equation)中消除,或者最多将其作为一种次要角色,作为解释而非知觉的媒介。我们在行进中知觉;当我们反思性地回顾自己和他人所作所为时,我们才进行解释。人类或许正是在其解释能力上——在语言和文化的促进下——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现在回想起来,我会用不同方式来表达。也许,与其将文化从知觉中消除,我们应该停止仅仅从表征系统的角度,或从构建表征的图式角度来思考文化。我们习惯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或许更适合被视为由各种知觉和行动技能构成和维系。
一年后(Ingold,1993),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相同的主题,这次是在探讨人类学的另一个长期困境时:通过我们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实践,我们怎么可能与生活经历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们达成对世界的共同知觉?在经典理解中,理解另一种文化的人被视为一种翻译任务:试图在不同的概念世界之间建立连接。要像其他人那样看事物,就意味着要掌握他们的概念。然而,在尚未理解这些概念之前,如何获得这把钥匙呢?你将永远陷入恶性循环。但如果知觉不是关于人们如何用习得的概念组织感官数据,而是关于他们如何在生活实践中关注世界本身,那么就有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意味着要感知他人眼中的世界,我们不再需要进入他们的头脑。只需要加入他/她们,和他/她们一起在世间行动。
因为吉布森的理论告诉我们,知觉是在公共场合而非孤立心智的私密空间中进行。它要求我们与他人一起参与,使我们的动作与他们的动作协调一致,保持注意力,并予以关心。通过这样做,我们带出了一个共同的示能世界。这种共性存在于概念的这一边,如果你愿意的话:它先于表征和解释,并为之提供便利,而不是依赖于它们。这当然也使得田野工作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在差异中的共同。它产生了某种「我们」是谁的感受,作为在共同任务中结合的人们,却不受「我们」和「他们」之间任何范畴性划分的限制。这样一来,与其说是「其他文化」的多重、多样的世界(每个文化内部同质但沿着族群认同的界限彼此对立),示能理论让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世界,哪怕它具有具有无限且不断浮现的差异性(Ingold,即将出版)。
现在,在 25 年后,我们发现韦伯·基恩(Webb Keane)重新回到了同样的问题:首先,如何解决物理实在论与文化建构论之间的二分;其次,如何定义「我们」是谁,而无需将我们范畴性地对立于「他们」。我只能欢迎他在示能视角中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可能性。他显然不了解我早先在同样方向上将示能思维引入人类学的努力,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事实是这些努力都石沉大海。没有人接受。直接知觉的观念,也就是生命体能在不经由符号中介的情况下在环境中找到意义的想法,对那些一直坚持(几乎是作为信仰准则)认为没有符号过程就没有意义的人类学家们来说,显然太过分了。人类学总是想要将在场(presence)隐藏在它的符号之后,将知觉隐藏在解释之后。示能视角则将这种倾向颠倒过来。它断言我们直接知觉事物,知觉它们如何出现并呈现在我们面前,影响我们的活动,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它们留下的符号来知觉。解释是后来的事。
这最终将吉布森的生态知觉方法与另一种在近期人类学中获得更大吸引力的方法区分开来。后一种方法的源头在于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生物符号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时,冯·尤克斯库尔创造了「环界」(Umwelt)一词来描述生命有机体的知觉环境。在动物的环界中,事物会呈现出某些知觉品质(或「音调」),这要归功于它们被纳入动物特有的活动模式或生活方式中(von Uexküll [1934] 2010)。这些音调听起来很像示能。但是有一个区别。因为如果吉布森总是想要在最后诉诸于将示能锚定在环境的物理属性上,冯·尤克斯库尔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音调绝非事物本身的内在属性,而是完全由动物赋予它们的,在动物的环界中才得以显现。吉布森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差异,并急于强调它,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他坚持认为,由环境示能之总和构成的生态位绝不能与「一些动物心理学家所谓的现象环境(phenomenal environment)」或相关物种的「主观世界」混为一谈(1979:129,原文强调)。
再一次,示能问题回到了知觉的公共性质。环界中的动物通过其符号解释世界,栖居在其物种特有的现实泡泡(bubble of reality)中,其他物种无法进入。同样,人类也被认为栖居在其自身的文化世界中。然而,示能是世界沿着这些道路而来的方式,而不是已经消失于不在场或隐藏于视野之外的世界留下的残余痕迹或指示。示能被知觉,而不是被解释或表征。但人类学家们确信意义需要符号,他们更关心将符号过程延伸到非人类世界,而不是考虑对非人类动物来说很管用的直接知觉示能对人类是否同样有效。这类研究最近的例子是一项在厄瓜多尔的鲁纳人(Runa)中进行的研究,其作者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2013)阐述了一个复杂的环境知觉符号理论,却从未提及示能的概念或生态学方法。他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现在是时候扭转这种局面了,我们需要创造一种词汇,让世界重返在场。基恩能在我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吗?我祝他好运。不过他需要做好功课。对于一个以其学科护照让他得以跨越诸多边界为傲的学者来说(27),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将自己的介入呈现为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他不仅似乎对生态心理学这一领域知之甚少——示能概念正是源自于此,并在其中经历了如此广泛的讨论;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在其他学科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包括他提到的人文地理学和考古学,以及他未提及的建筑学和教育学等领域。举例来说,怎么可能把吉布森的整个学术成果仅仅用一篇十五页的概述性文章来代表,完全不引用生态心理学领域的任何其他著作,而且将「人类学领域及其周边」的其他学者的工作仅仅放在脚注中呢?
问题不在于学术优先权或对来源的承认。没有人想要一个枯燥的文献综述,在公开演讲中更是如此。重要的不是你引用谁,而是学术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从其他学科或其他学者那里借鉴想法和概念,看看能把它们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做法很有价值。将它们应用到远离其原初目的的研究领域也无可厚非。但这需要谨慎行事,要尊重先前用法中的深度、复杂性和微妙之处。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被忽视。基恩在前述脚注中声称,他正在将示能概念的范围「扩展到物质环境知觉之外」。我不清楚「非物质环境」(immaterial environment)究竟是什么。如果经验存在于对示能的知觉之中,那么基恩所说的「主观经验的示能」(36)究竟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基恩的论述大部分都让我确信,正如示能视角能让我们超越物理实在与其文化建构之间的二分一样,它也超越了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二分。不过,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基本上,他采取了和吉布森完全一样的做法,试图两者兼得。他正确地指出,并且也符合吉布森的精神,认为感知和回应示能并不依赖于心智表征。但他也坚持认为,这一点也是与吉布森一致,尽管示能是「客观特征」(objective features),但它们只有「相对于某个它们之外的感知实体的属性,并且相对于该实体的活动」才存在(31,原文强调)。因此,示能既是物理实在,又同时是偶联关系(contingently relational)。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在实在论和关系论的本体论之间达成了令人不满意的妥协。在基恩的方法中,示能视角只是遮掩这一问题的创可贴。事实上,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它揭示了吉布森最初的知觉方法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他让知觉者重获生机,成为一个不断移动、主动关注事物、探索其无穷潜能并在此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熟练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环境实际上被固化了:它被描绘成一个由事物构成的环境,每个事物都被固定在僵硬且不变的形式中,变得惰性,准备就绪地等待知觉者登场并揣摩其示能(Ingold 2011:12)。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长期沉迷于吉布森的想法并倡导示能视角之后,我自己近来反而成了一个批评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基恩开始接触示能概念时,我发现自己正在离它而去。因为按照我现在的理解,知觉不仅仅是探索一个已经存在的事物世界,或者探索那些已经——可以说——从形成它们的过程中「析出」(precipitated out)的事物;它还必须关注在形成过程本身的当下时刻中的在场和觉知(aware)。这就是要加入一个「无物的世界」(world without objects),置身于其初现的浪尖之上(Ingold 2015:13-17)。想想世界的流动——风和天气、永远变化的天空、潮汐的转换、河流的奔涌、动物的移动和植物的生长。要打猎捕鱼,要耕种,要扬帆起航,实际上要在陆地或海上进行几乎任何类型的生计活动,都需要调节你的动作和活动的时机,以便抓住那个所有促成你事业成功的力量都处于有利配合的时刻。世界并非总是准备就绪静候;你也必须准备就绪等待世界。这种对称性必须重新建立,而这只能通过将环境和知觉者都重新置入真实时间的流动之中才能实现。古希腊人在他们的恰当时机(kairos)概念中对此有更好的理解,它不仅指必须抓住的时机,还指为此所需的关注和回应能力。这或许接近于基恩所说的示能不属于事物或人,而是属于整个情境(32)。
对我来说,这触及了知觉与想象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对认知主义者而言,两者几乎没有区别:感知物是一个意象,作为一种表征,它与其声称所表征的实在处于隔离的两端。吉布森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坚持认为知觉直接通向真实世界,却使想象在另一端陷入困境:他坚称,想象只是非实在的另一种说法。这是否恰好就是基恩所说的超越物质环境知觉的感知?吉布森会相反地断言,想象是一种用他的话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知觉性的」(1979:256)意识形式。他认为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可以区分知觉性和非知觉性的东西。因为实在是无穷尽的;你越是仔细审视它,你的注意力越是精细调谐,你就会发现得越多。然而,意象则不然。因为无论你如何尝试,你永远不会在其中发现比心智已经放入其中的更多的东西。你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解释来增添内容。因此,知觉之于想象,就如同发现之于解释(Ingold 2012:3)。
但是实在与想象必须如此分离吗?我们难道不能找到一种方式,在一个单一的创造性运动中将它们结合起来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想象:不是将其视为构建意象的能力,或是心智表征的力量,而是更根本地将其视为在一个尚未创造、尚未成形的世界中创造性地生活的方式,这个世界本身正在生长,永远处于形成之中。这就是一个无物的世界。难道我们在行走时,不是不断地让自己冒险向前跌落,朝着虚空向前翻滚,只是通过熟练地调整身体姿势来适应地面的不规则才重新获得立足点吗?想象让我们松脱去跌落;知觉恢复我们的抓握,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行。一者是向往(aspirational),一者是把握(prehensile)。正是在它们的交替中,所有的生命得以延续。就像行走的例子一样,栖居于一个无物的世界中,在知觉与想象中,就是从内部参与世界自我创造的过程,参与其自我生成。这不也是人类学的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