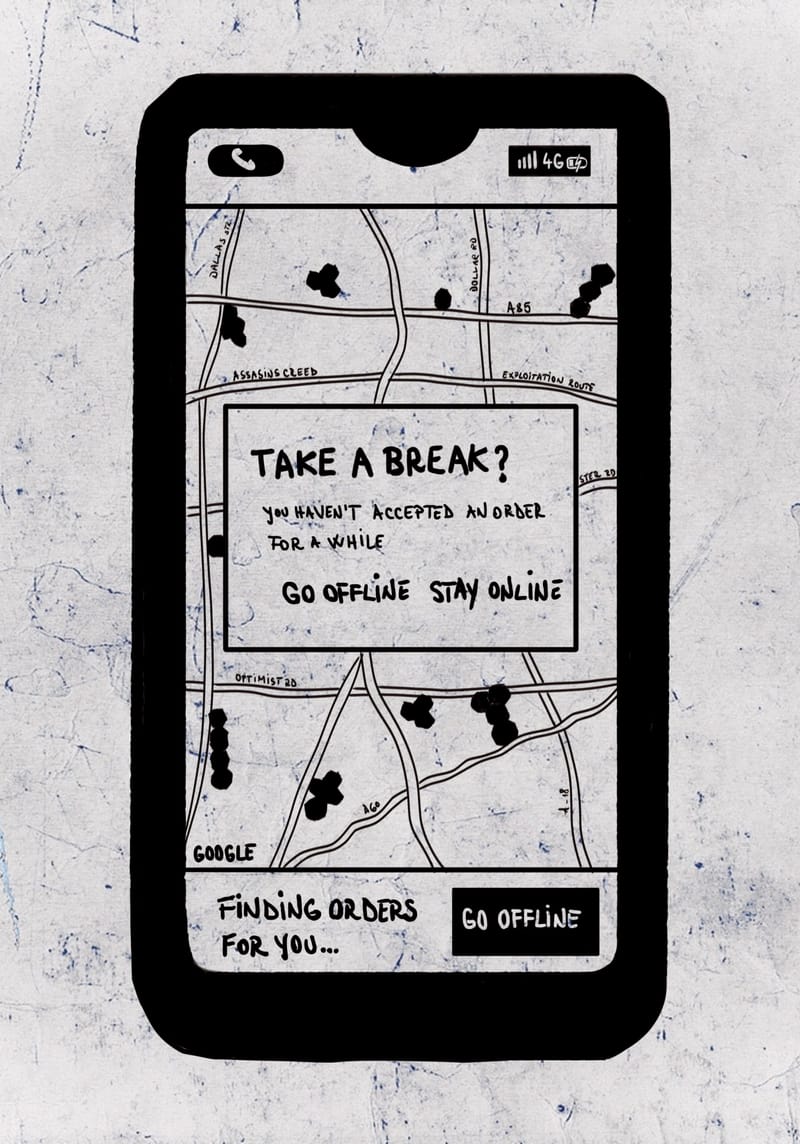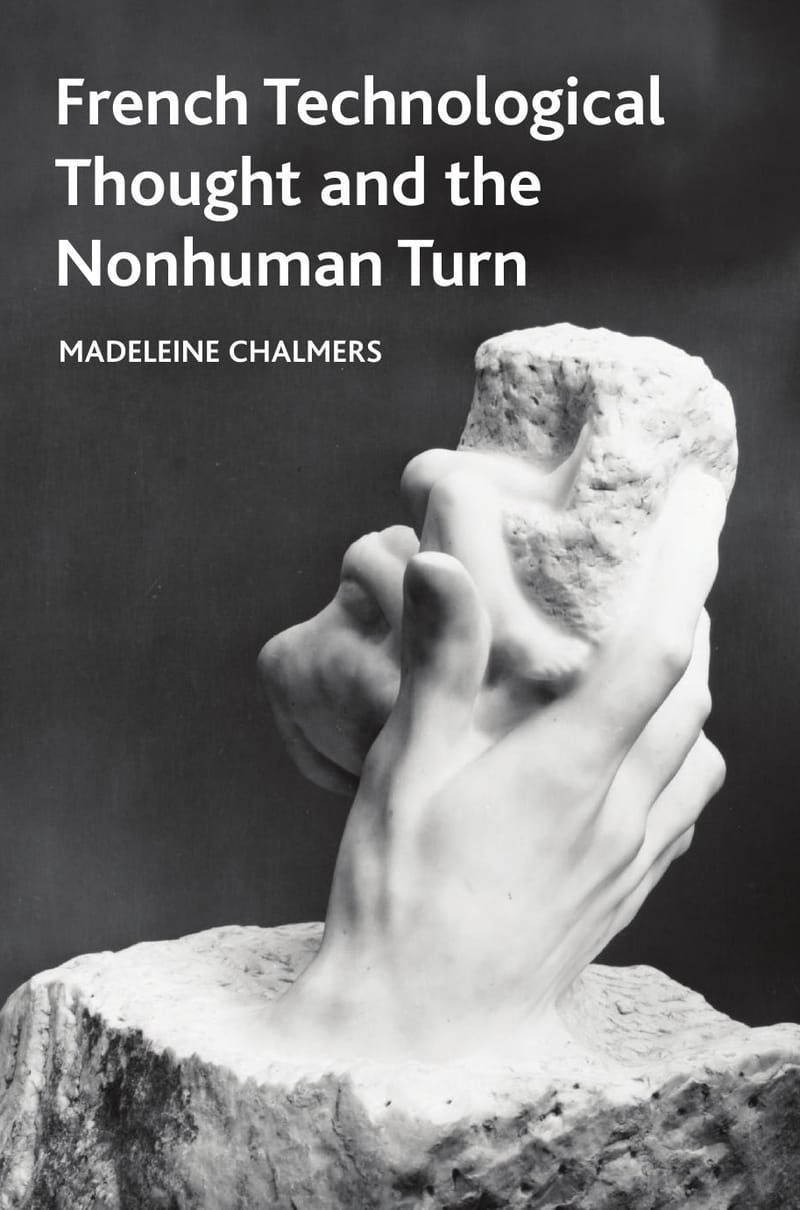翻译自 Ian Bogost. Alien Phenomenology. 中译本待出。
新墨西哥州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各种古怪东西。
天气晴朗(clear)时,每天傍晚总有一阵子,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以东的桑迪亚山脉(Sandia Mountains)上会滴下同名水果的汁液,它们迅速成熟,直到黄昏将它们吞噬。山脉南麓,苹果树取代了西瓜。在那里,在被掏空的曼萨诺山(Manzano Mountain)中,美国武装部队特种武器司令部(U.S. Armed Forces Special Weapons Command)一度藏有这个国家最大的国内核(nuclear)武器库,截至千年之交,约有2450枚弹头。
桑迪亚向南一百英里是三位一体核试验遗址(Trinity Site)。1944年夏天,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那里用美元打赌,赌一个内爆式的钚装置是否有可能点燃大气层。今天,该遗址在四月和十月的第一个周六向公众开放。家庭大篷车从索科罗(Socorro)和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等周边城市开来,人们在这里野餐,在烧烤牛肉的同时,也被辐射所穿透。
在桑格里克利斯托山区(Sangre de Cristos)的南部边缘,黄昏时分流下的不是甘露而是血液——「神枪手」山脊(Sharpshooter's Ridge)下埋藏着另一种军火:1862年格洛列塔山口战役(Battle of Glorieta Pass)中联邦军所使用的滑膛枪(buck-and-ball muskets)的鹿弹(buckshot)。
山脉、水果、大气效应、核弹头、三明治、汽车、历史事件、遗迹。这是关于世界的小型样本,那个在我之下、之上、周身、后面和前面的,那个被忽视的世界的小型样本;也是簿册上登记着的,关于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些许条目。
可要是没了外星人,新墨西哥州的目录就算不上完整。<1>在那颗将会点燃郊区的火球发射时,奥本海默引用了《薄伽梵歌》中的咒语。短短两年之后,据罗斯威尔陆军机场(Roswell Army Air Field)的工作人员说,他/她们找到了一个坠毁的飞碟,还有其人形乘客的尸体。随后的报道和阴谋论往往认为,这些飞行器、尸体和残骸中「没有任何部分来自地球」,即便如此,遗留下的每个部分仍能被恰当地指认为航天器、设备或入侵者。
外星人在罗斯威尔寻找我们。我们也在索科洛以西寻找它们。在那里,在圣奥古斯丁盆地(San Agustin Basin)的荒凉平原上,坐落着二十七个甚大天线阵(Very Large Array,VLA)。它们高达二十五米,像许许多多铁质的火山口一样,指向广阔的蓝天。天体物理学的各种实验(包括研究黑洞、超新星和邻近星系)都会用到VLA天线,每到这时,VLA天线就会像热带鱼群一样连在一起。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仪器的主要目的是让「搜寻地外文明」(SETI,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这样的组织能够偶尔用之。射电望远镜聆听天空;SETI收集并分析数据,满怀希望地寻找暗示外星生命存在的电磁透射(electromagnetic transmissions)。这是被称为「天体生物学」(astrobiology)的领域,一个在研究界独一无二的领域,因为它没有任何确凿的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在埋藏着鹿弹的格洛列塔山口的东北方,经过绘出「基督之血」的山峰,越过滑雪胜地、嬉皮士飞地和名人们的牧场,在拉顿—克莱顿(Raton-Clayton)火山场内,数百个火山渣锥(volcanic scoria cones)的尸体无声地嘲笑着滑膛枪和钚那愚昧的时髦感,毕竟自上次喷发以来的五万年里,它们从未改变。
向南去,穿过火山场的表亲——卡里索索—马尔帕斯(Carrizozo Malpais)的熔岩流——越过三位一体核试验遗址,白沙国家公园(White Sand)的石膏沙丘随风而动。像是齐泽克式的白日梦般,它们形成了绵延275平方英里的海岸,却从未触及大海。这里曾是另一种研究宇宙的工具——航天飞机——的备用着陆点。只在1982年3月30日时,航天飞机在此着陆过一次。清理工作太过繁重,<2>美国宇航局(NASA)被迫从哥伦比亚号(Columbia)机体的每一个缝隙中取出石膏,就像保姆努力打理一个在海滩上闹了一天的大胖小子。二十一年后,当宇宙飞船在德克萨斯上空悄然破碎时,白沙国家公园的石膏仍在移动,无处可去。
径直向西,在多纳安娜县(Doña Ana County),炎热、干燥的阳光增加了小村哈奇(Hatch)周围生长的绿色辣椒作物中的辣椒素水平。辣椒在通风的钢筒中翻滚,在敞开的烘烤架上噼啪作响。终于,它们的表皮起泡、变褐,随后变黑。剥开辣椒皮,露出鲜绿的果肉,仿佛打开了基督之山(mountain-Christ)的创口。辣椒覆盖着一盘盘安其拉达(enchilada),正如灌木掩护着它们在高原沙漠(high desert)中数百平方英里的家。
事物的状态(The State of Things)
为什么我们给予死去的内战士兵、有罪的(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椭圆头的人形外星人和太空智慧种族的信赖,要远胜过火山渣锥、黑曜石碎片、石膏晶体、辣椒或丙烷火焰?当我们将这些事物迎进学术、诗歌、科学和商业领域时,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们与人类生产力、文化和政治的关联。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发明的小型监狱中,与我们有关的一切都是肉的存在(fleshy being),是我们的亲属,还有我们用来填充(stuff)自己的东西(stuff)。文化、美食、经验、表达、政治、论战:人性的筛子滤过了一切存在,丰富的事物世界宛如米糠一般,被如此彻底、直接、高效地丢弃,以至于我们从未留意。何以至此?为什么当下的「事物」(things)常常意味着观念,而东西(stuff)却极少如此。简单考察近来的哲学就能发现我们自负的根源。
想想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先验观念论的遗产。我们从康德的遗赠中承袭来的观点是如此盛行(prevalent),以至于它们就像山脉、石膏和西瓜一样,既无人察觉,也无人问津。
这个立场认为,存有(Being)只为主体而存在。在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主观观念论中,客体只是感知它们的人心智中的一束感觉数据。在黑格尔(G.W.F. Hegel)的绝对观念论中,<3>对世界的最佳描述就是它在自我意识的心智前展现的样子。对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来说,客体在人的意识之外,但它们的存有只存在于人的理解之中。对雅克・德里达来说,事物从未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只是在特定的脉络中,无限地分殊并延宕它们朝向个体的通道(access)。正如前文的目录只列出了新墨西哥州炎热阳光所炙烤的事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也只是一个小型样本,是从漫长得多的现代哲学史中撷取的只言片语。
所有这些运动都将存有看成某种「通道」问题,以及人类如何通向存有的问题。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创造了相关论(correlationism)一词来描述如下观点:存有只作为一种心智与世界之间的相关(correlate)而存在。如果事物存在,它就只为我们而存在。梅亚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相关论者不能接受「事件Y发生在人类出现前X年」这样的陈述。
不,他只会补充上——或许只是自言自语,不过他肯定会这样做——某些类似于简单附注的东西,且内容总是一样的。他会将这个附注审慎地补充在那个陈述的前面:对人类而言(甚而, 对科学家而言),事件Y发生于人类出现的X年前。
在相关论者看来,人类和世界密不可分,一方永远无法离开另一方而存在。梅亚苏的斥责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对现代性的批判相似:理论试图将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人类,一半是自然。人们承认人类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却只允许自然或物质世界保持单一。
2007年,金匠学院(Goldsmith’s College)举办了一次题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研讨会。此后,梅亚苏就与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三人一同,被初步安置在「思辨实在论」的哲学招牌下。然而这个标题无助于统合四位思想家从新物质主义(neomaterialism)到新虚无主义(neonihilism)的不同立场。与其说思辨实在论者享有共同的立场,不如说他们在对抗共同的敌人:从康德的腐朽中渗出的人类通道之传统。即便与康德那声名狼藉的内向性有关的故事都有过分夸大之嫌,<4>它们也足以孕育出一种讽刺:「哲学作为通道」(philosophy-as-access)的盲目状态之所以出现,离不开一个从未远离普鲁士小镇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人的影响。两个多世纪以来,哲学一直安静腼腆、沉默寡言,堪称隐士。
逃离心灵监狱的阴暗长廊,迈向物质世界的繁茂草原,思辨实在论必须兑现其称号中的第一个术语:形而上学无需从经验、物理、数学、形式逻辑甚至理性(或是其他任何事物)中寻求验证。实在论者之思辨的成功入侵,同时终结了超验的洞察与主观的禁锢之统治。
这只是一个起点,一段前奏:今天,要继续做一个哲学家,就要拒绝相关论。要成为一个思辨实在论者,就必须放弃这样的信念:人类通道位居存有中心,像一个本体论的钟表匠一般组织并调节着存有。在比喻与事实的双重意义上,思辨实在论是一桩哲学事件,而非某种哲学立场:它为认识论大潮的衰退时刻命名,揭示了它们遮蔽已久的实在论的斑斓外壳。正如宇宙学理论中的「大爆炸」(Big Bang),被称为思辨实在论的哲学事件开启了一种境况,其中蕴含着许多新机遇,能够展现诸种通道哲学的古雅(quaintness)。
思辨实在论肯定会开枝散叶,但在反相关论四骑士所提供的立场中,哈曼与我适性最佳。与其他人不同,哈曼最明确地接受了万物之中的存有的多样丛结。现实被重申,人类被允许生活其间,与海胆、葛藤、安其拉达、类星体还有特斯拉线圈相伴。
哈曼以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为原材料,构建了他所谓的「客体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快速过一遍:海德格尔提出,事物不可能被理解为其所是。相反,事物与目的有关,在此状况下,谈论作为事物的口琴或塔可就成了问题;东西被脉络化时变得上手(zuzuhanden);被剥离脉络时又变得在手(vorhanden)。海德格尔最喜欢的案例是锤子(它可以用来锤钉子),<5>一种我们在追求更大的筹划(比如盖房子)时会忽视的事物——除非它坏了或是变得抽象。
哈曼认为,这种「工具—存在」(tool-being)是所有客体的真理,而不只是此在(Dasein)的真理:锤子、人类、俳句和热狗对彼此来说既在手又上手,完全无异于它们之于我们。某些事物在退隐(recede)——总是隐藏、内置、不可通达。他提出,客体不仅通过人的使用,也通过任何形式的使用(包括一个客体与另一客体间的所有关系)从而发生关联。哈曼的立场还隐含着对科学自然主义的反驳:事物不只是它们最基本的成分,无论是夸克还是神经元。相反,无论其大小、尺度或秩序,所有东西都享受着平等的存有。
如果说本体论是对存在的哲学研究,那么哈曼就带来了一种「客体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称OOO,读得时髦些就是「triple O」)。 OOO将事物置于存有中心。我们人类并非哲学旨趣的唯一要素。OOO主张,没有什么事物具有特殊地位,一切事物都平等存在——例如黄瓜、棉花、倭瓜、DVD播放器和沙石。在当代思想中,事物往往被视为越来越小的比特的集合(科学自然主义),不然就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的建构(社会相对主义)。OOO在两者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吸引人们关注各种尺度的事物(从原子到羊驼,从比特到金丝雀)并思考它们的本质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它们与我们的关系)。
你或许注意到了OOO的「客体」和其他哲学概念——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中的「事态」(occasion)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network theory)中的「行动者」(actors)——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比较颇有价值,也确有总结该立场的捷径,即引述哈曼对李・布拉弗(Lee Braver)的实在论类型的非正式补充:「人/世界的关系只是任意两个实体间关系的特例。」——怀特海和拉图尔都将轻松通过以上检验。
可OOO仍与过程哲学或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同。对怀特海来说,实体并不持续存在,而是不断地相互让位——形而上学相当于变化、动态和流动等属性,经由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或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它们在欧陆哲学中或许更为人所知。<6>「经验」的连续的现实事态相当于一种侵蚀,将客体蚀解为更基本的成分,使之立即消亡。我想避免这样。与怀特海不同,拉图尔允许事物在所有尺度上的无争议地存在。但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网络中,事物处在运动之中的时刻远比静止的时刻多。因此,被强调的不再是实体本身,而是它们的耦合与解耦。结盟(alliance)占据了舞台中央,而事物则被移到侧翼。正如拉图尔所言,「行动者们伫立不动的时间还不够拍一张合影。」可它们就在那儿,与此同时,它们也被组构进网络之中,或是从网络之中解离。火山渣锥和绿辣椒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它们也参与到板块构造、安其拉达、旅游业或消化吸收等等系统之中。
从文化理论而非哲学的角度来看,OOO一脉的思辨实在论或许与一些更常见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如后人类主义)相似。例如,环境哲学认为,人类之于生态学,恰如男人之于女权主义或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之于种族。诸如戴夫・福尔曼(Dave Forman)这样的活动家则主张森林和野生动物应当与人类地位平等。
但后人类进路仍将人类(humanity)看作主要行动者。要么是我们的未来存续激发了对环境的关注,要么是像葛藤和灰熊这样的自然造物被抬升到与人类相同的地位。从约翰・穆尔(John Muir)到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每一种生态整体论(environmental holism)的构想中,对地球来说,所有生命(beings)都拥有同等的绝对价值和道德权利——只要它们仍是活生生的造物。一种存在的类型——生命——仍然构成了思想和行动的参照点。用拉图尔的话说,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宣称要捍卫为自然而自然——而且不把自然作为人类自我中心论的替代品——然而在每一个例证中,它给自己所分配的这个任务却是由人类所实施的,并且是由一小撮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所认证的,他们健康、幸福、快乐或有良心」。 拉图尔看到的并非单一的自然(nature),而是多重的自然(natures),每种自然既处在作为整体的自然之中,又保有自己的特性。然而,即使对拉图尔来说,分析仍服务于人类政治的旨趣(即上引书目的副标题所说「如何将科学带入民主」)。<7>
生态学话语中的另一种视角,大概更接近记者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的《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一书。韦斯曼记录了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后会发生的事。地铁被淹没;管道冷却开裂;昆虫和风雨缓慢吞噬房屋的木制框架;桥梁和摩天大楼的钢柱腐蚀弯曲。客体导向的立场认为,不必等到人类狂欢般的消失之时,我们现在就可以关注塑料、木材和钢铁。
和环境哲学一样,动物研究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却又止步于狗、猪、鸟等等「熟悉的」行为体(actant)——由于在形式和行为上与人类相似而被常规化(routinized)的实体——的单一领域。正如理查德・纳什(Richard Nash)和罗恩・布罗格里奥(Ron Broglio)所说,「动物研究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转向......描述特定的人类和特定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两者自身所嵌入的文化加以重视。」再一次,对造物的注视源自人类主体间性的有利位置,而非笼罩着真正实在(really real)的怪异而阴暗的迷雾。
我们或许还会质疑动物研究武断的特异性(specificity)。为什么是树木和海龟,而不是矿物或茎、叶多肉植物?正如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在批评动物研究所表现出的动物中心主义(zoocentrism)时所说:「那么植物、真菌、原生生物、细菌和其他生物呢?」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o)尝试以植物的眼光看待世界,它赋予了马铃薯和大麻(至少与狗和乌鸦一样多的)主体性。但他也试图规定苹果或马铃薯的价格,只为了动员它们批评人类的园艺学、营养学和工业主义实践。这种批评服务于它所推崇的生物多样性的合作实践,可作为一种价值,「生物多样性」的明确目的恰恰是要延长人类的生命和福祉。总而言之,后人类主义还不够后人类。
说明白些,我们不必为了采取客体导向的立场而贬低人类——毕竟我们自己与滑膛枪鹿弹、石膏还有航天飞机一样,都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不能再声称,我们的存在是特殊的存在般的(as existence)存在。<8>即使人类也拥有一种看似独特的能力,足以搅动整个世界,或至少是我们的一隅之地(尽管这个假设也相当宏大,因为与人类发生互动的只是整个宇宙的纤毫),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所有客体无限地退隐到自身之中」的观念,那么人类的知觉就成了客体可能生成关联的众多方式之一。要把事物放在新形而上学的中心,我们还得承认,事物并不只为我们而存在。
作为提示符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Prompt)
我很幸运。作为计算媒体,特别是电子游戏的创造者和批评者,我更多从无生命(inanimacy)而非生命的角度来理解事物的形而上学。这种视角富有成效,因为常伴我左右的事物——它们隐秘的维度——既不会眨动水灵灵的眼睛,也不会被宏量营养素(macronutrients)所满足。计算机或许会便利工作和娱乐,却不会将早晨的清香送进人们的鼻孔,也不会用夜里的呼噜声打乱人们的脚步。不像红木、地衣和蝾螈,计算机没有勃勃生机。它们是具有巫术力量的塑料和金属尸体。
但是,任何曾经组装、修理、编程或以其他方式操作过计算装置的人都知道,这类设备中确实有一个奇怪而独特的世界在搅动。在玻璃与铝制成的外骨骼后头,一个小小的、私密的宇宙在咯咯作响。计算机由模制的塑料按键和控制器、电机驱动的磁盘驱动器、硅晶片、塑料排线以及许多比特的数据组成。它们同样由编译成字节码或蚀刻在硅片上的子程序和中间件的库、与绝缘导线相接的阴极射线管或液晶显示器,以及执行从地址总线中进出的机器指令的微处理器构成。我想知道那个秘密的宇宙中发生了什么,这份好奇丝毫不弱于我对已经消逝的、属于非洲大象和鹿角珊瑚的世界的兴趣。成为一台计算机、一个微处理器或一条排线可能是什么样子?
的确,计算机常常需要人类的经验和知觉。人类操作者查看屏幕上渲染出的文字和图像,<9>对鼠标施加物理力,将内存条插进主板上的插槽。但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计算机要想为我们所操作,首先需要大量为自己而发生的交互。作为操作者或工程师,我们也许能够描述这些客体和组合如何运作。可它们经验了什么?适合它们的现象学是何种形态?简言之,成为一个事物可能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一台微型计算机、一座山脉、一个射电天文台、一件热核武器或一种辣椒素,而不违背事物自身的愿望,什么进路可能派上用场?
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也许是个办法,可这一领域仍在分析中心保留了一些人类行动者——通常是一位科学家或是工程师。拉图尔就犯了这个毛病,哪怕是他自己对待行为体的哲学进路,也在「不可化约论」(Irreductions)中,在恰当的时候,愉快地括出(bracket)了人类行动者。或许更重要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被用于启发对科学——作为一种需要警惕与批判的人类的自负——的研究。科学研究或许值得追求,尽管如此,它却几乎没有涉及锥形瓶(Erlenmeyer flasks)或胶轮路轨系统中的列车的内在世界。
类似的麻烦也困扰着生机论(vitalist)和泛心论(panpsychist)等进路。它们允诺各种物质行为与人类所思所感的「亲缘性」(akinness),却也过于关注人与物的相似而非差别。怀特海仔细区分摄入(prehension)与意识,同时仍设法将实体看作「经验的搏动」。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颇有助益地将这一立场简写为泛经验论(panexperientialism)而非泛心论,前者比后者更符合我的想法。
恰如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所言,生机论是一种妥协,一种不精确地将「活」的性质投射到万物之上的妥协。由此,莫顿建议用网络(mesh)而非自然来描述「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的相互联结」。但要认真对待这种相互联结,我们必须正视它。哲学的主题不能再局限于人类和影响人类的事物。它必须涵盖万物。不像野猪和黑松露,硅制微处理器和数据排线怪异而普通,令人陌生却又是人造,能够活动却从未活着<10>——它们更像是猫咪或是石灰岩矿床。 在泛经验网络的世界里,事物要如何拥有经验?
哈曼的答案是「替代因果」。事物从未真正地相互作用,而是以一种与意识无关的概念性的方式(fashion)融合或联结。我们仍不知道事物相互作用的途径,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某种代理(proxy)打破了鸿沟,融合(fuse)了客体,却没有将它们真正融为一体(fusing)。哈曼打了个拼图的比方:「拼图并未模仿原本的图像,而是用裂缝和策略性的重叠来构筑谜题,这些裂缝和重叠会为一切事物带来新的视角。」通过追踪裂缝,我们理解关系。
但是什么之间的裂缝?在将替代因果付诸实践之前,我们必须停下来问一问,首先,什么是存有?我们在可能经验(possible experience)的网络中发现了什么?什么是事物,什么样的事物存在?
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
简而言之,所有事物都平等地存在,其存在却并不等同。火葬堆不同于非洲食蚁兽;海贝壳不等于英式橄榄球。这两对事物既不能化约为人类的遭遇,也不能化约为另一对事物。
这条准则看起来像是同义反复——或只是个噱头。它定不是哲学中惯用的那种限定条件、论证充分且自缚手脚(hand-wrung)的本体论立场。但为使事物的奇特花园绽放,这种极端的取舍实属必要。一切思辨必然是思想实验,不妨也如此看待它:如果我们舍弃所有标准,简单地认为万物都存在,甚至连不存在的事物也存在,那会怎样?再进一步,如果我们认为,在现存的事物中,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异于其他,那又如何?独角兽和联合收割机,红色和甲醇,夸克和波纹铁,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和消化不良——万事万物平等齐观,存在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谈不上哪个更基本或更原始。
无需多言,点到为止。即便如此,做些初步澄清也是应有之义。这种本体论不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式的一元论;存在并非独异(singular)且不可改变。它也不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式的原子论;<11>存在不由大小相等、性质相同的基本元素组成。它亦不是深邃不明的不确定性,像是列维纳斯(Levinase)的「有」(il y a)或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的「阿派朗」(apeiron)。相反,事物之所是(be)可以丰富且多样、特异而具体,同时其存有(being)仍保持一致。
列维・布莱恩特(Levi Bryant)称之为「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他从曼纽尔 · 德兰达(Manuel DeLanda)处借来了这个词。德兰达的「平本体论」强调存在完全由个体——而非种或属,举个例子——构成。布莱恩特的用法有所不同:他的平本体论赋予所有客体相同的本体论地位。于布莱恩特(亦如拉图尔),「客体」一词囊括众多:有形和无形的实体都算在内,无论它们是物件(material object)、抽象概念(abstraction)、意向对象(objects of intention),还是任何其他东西——夸克、哈利・波特、主题演讲、单一麦芽威士忌、路虎、荔枝、风流韵事、解引用的指针、《情境》(The Situation)的迈克・索伦蒂诺 (Mike Sorrentino)、玻色子、园艺家、莫桑比克、《超级马力欧兄弟》——没有谁比谁更「实在」。
借着这个奇特而反直觉的词组,布莱恩特到达了本体论的底部。「世界不存在」,他如是说。自然,如果万物的存在都如我方才所说,那么就需要特别注意关于「不存在」的陈述。布莱恩特想说什么?没有事物属于你(no ur-thing),没有任何容器、器皿、概念位于存有之上,以至于它可以整体地、无疑地包括存有的所有方面:「并不存在某个『超级客体』(super-object)……能将所有客体聚集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那么,何时有了「世界」或「宇宙」?它们是概念,人类行动者调用它们,试图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容纳并解释事物。作为一种为哲学、科学或虚构服务的概念,「世界」的存在既不比沥青密封涂层多,也不比苹果马提尼少。但作为一种在物理定律或上帝的意志下,统一并容纳其内部的一切的调节力量,「宇宙」对事物特征的描述,并不比其他力量更真确、更统一。它只是与甜瓜和唇膏相伴的另一种存有。
在前作中,我曾将布莱恩特意义上的「世界」等观念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原则称为「系统运作」(system operation)。系统运作是「试图从其整体性中寻求现象、行为或状态之解释的总括性(totalizing)结构。」<12>它们倾向于设想某种终极的、整体的、决定性的解释,来说明并解释存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两种系统运作占主导地位:科学自然主义和社会相对主义。第一种源于德谟克利特,或间接得自伊比鸠鲁(Epicurus)。科学自然主义认为,某种基本的、物质性的天穹(firmament)维持并进而解释了所有东西。这一领域的细节并不特别重要——粒子物理学、遗传学、脑化学,随便什么都好。不管是什么种类(sort)的东西,对科学自然主义者来说,总有某样(some)东西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其他东西。此外,这些基本客体的本质及其在铸造世界时的作用,总能通过科学的过程被发现、记录和固化。尽管有库恩(Kuhn)式的范式转移,科学自然主义仍假定,通过科学的坚持,对现实的探索将逐渐累积、不断进步。
这个时代的第二种(本体论层面的)系统运作,即社会相对主义,源于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主义的传统。对于社会相对主义者来说,凡存在,即可用人类社会的诡计(machinations)——尤其是复杂的、演化的文化和语言之形式——来解释。社会相对主义者提出,一切事物都通过概念化来存在;它们其实只是人类文化生产圣殿中的结构。对于社会相对主义者来说,科学自然主义的确定性总会被以下事实损害,即科学本身位于文化之中——不仅是大写的文化,也是存在于特定时间和地点,并作出特定假设的,特异的文化时刻。
科学自然主义和社会相对主义的智识冲突由来已久。众所周知,C. P. 斯诺(C. P. Snow)将两个领域间的距离称为「两种文化问题」(two cultures problem),暗示两种立场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前者坚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真正的知识独立于历史或语境,后者则指出,由于忽略了历史和语境的偶变性,单一的解释面临着种种危险。
不用放大镜也能看出,这两种立场本是一路货色。<13>对科学自然主义者来说,世界为人类的探索与开发而存在。对文化相对主义者来说,人类创造并重制了世界。长久以来,双方就如何处理世间知识——要么是实验,要么是批判——争论不休,这只是在遮蔽真正的问题。
换言之,两种视角都体现了相关论的自负。科学家相信人类生活之外的现实,但对现实的挖掘却是为了人类的开发。科学过程凝聚着人类才智,比起现实本身,它更关心现实的可发现性。同样,人文主义者也不相信世界,除非是作为一种依人类文化之旨趣而建立的结构。像是科学家的镜像,人文主义者大多试图挖掘文化的特定形式,至于挖掘的方式,往往是暗示必须通过抵抗或革命的抽象概念来克服文化的某些方面。「看看我!」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都在叫喊,「看我发现了什么!」
再以计算机为例,选个著名的案例:「图灵测试」。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密码学家和计算机架构师之一——阿兰・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挑战。图灵的名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以一个问题开篇,此后六十年中,这个问题一直活跃在人工智能领域中:「机器能思考吗?」完全可以就此打住,停在这第一句话上,因为它已经包含了单一的人类—世界之相关(correlate)。甚至不需要知道挑战的细节是什么,目标就已给定:将机器行为和人类行为关联,如此就可以从一方的角度来判断另一方是否成功。
然而,图灵很快就解释说,这个问题并不令人满意,他计划用另一个问题来代替它。原来,与他同名的测试(后来其他人如是命名)是一个常见的室内游戏的变体:对话者试图通过提出简单的问题——如 「请X告诉我他或她的头发长度?」——来猜测派对上两位隐藏客人的性别。作为人类,玩家们可以出奇制胜,用骗术愚弄对话者。如果计算机能骗过人类,<14>那么这个结果就圆满地取代了原来的问题:「机器能思考吗?」
这个策略看起来有些愚蠢,却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传承已久的圣杯。毕竟,机器是愚蠢的、没有感觉的客体,只有在人类操作者或程序员的推动下才能发挥作用、解决任务——当然,都是造福人类社会的任务。在图灵提出相关设想并不幸逝世后,短短几年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就出现了,它的名字就是一种承诺,它将效忠于人类之相关:一台计算机做的事情越是智能——这就是说,越对人类有益,或越能被人类识别为智能活动——它就越是有用。图灵测试既服务于科学的虚构,也充当着科学的目标;既呈现为《星际迷航》中的LCARS,它可以理解、推理,并通过语言与人类建立联系,也启发着罗布纳奖 (Loebner Prize),一项自1991年以来每年举办的比赛,实施原版的图灵测试,并为表现最佳者颁奖。科学假定计算机的本质与人类经验的本质相关。发现计算的真正本质也就是发现人类理性的真正本质。
大多数对图灵测试的反驳都涉及到人类理解和经验的基本原则。最著名的反驳是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房间」(Chinese Room)思想实验。 塞尔设想了一个操作员,像是一台机器般操纵着从门下递进递出的汉字。这个人虽然不懂中文,却能按照程序的指示做出连贯的回答。即使由此产生的回答能够被母语为中文者所理解,塞尔仍认为,不能说执行这些程序的机器具有「思想」「头脑」或是 「智慧」。
在一个略显不同的批评中,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提出,图灵的个性使他倾向于把世界当作一个待解的谜题,但悲剧的是,他也因此「对说和做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霍奇斯将图灵对机器智能的兴趣转化为一种体贴的洞察,以进入到作为个体的图灵那困顿重重的个人生活中<15>——这些困顿包括他在1950年代时因为是同性恋而受到迫害,随后自杀。霍奇斯说:「涉及性、社会、政治或秘密的问题将表明,能够限制人们可能会说什么的因素,并非解谜的智能,而是对可以做的事情的约束。」。
塞尔的反驳批评了「强人工智能」的功能论,认为它误解了人类心灵的本质,误解了拥有心灵和模拟心灵之间的区别。霍奇斯的反驳着眼于激发计算系统的动机,而非系统本身,他的结论是,图灵测试的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智能机器的概念)仅仅象征着某个特定的人类对一个一般性问题的好奇。
在以上两种批评中,计算的概念都与人类的理解、经验和知识密不可分。这一进路不无道理:人类之所以创造并操纵机器,主要是为了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可即使在图灵测试这个简单的案例中,计算机中起作用的无数其他因素仍被忽略了。例如,对计算的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批评都并未考虑,机器的运作是否可能独立于它所模拟或努力实现的人类智能。工程师或许会对计算机系统的结构和行为感兴趣,希望优化或改进它,却很少想要理解机器本身,就好像它是一株毛茛或一块舒芙蕾。然而,同万物一般,计算机有其独特的存在,值得我们反思和敬畏,它的能力确实超出了我们促动它的目的。
作为例证,图灵的计算机实验说明,对相关论的拒绝,颠覆了支撑人文主义与科学的单一的人类—世界之相关。但反对人类—世界之相关并不意味着拒绝人类或他/她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后人类主义提了太久「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不管是通过替代或附加的技术,还是通过更新的、更温顺的对人类身份的文化理解。真正的后人类主义既不会将人类(humanity)延展到一个共生的、幻想的未来中,也不会通过反人类的虚无主义来拒绝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相反,正如布莱恩特所言<16>,在后人类主义的本体论中,「人类不再是存有的君主,而是跻身诸存有之列,卷入(entangled)诸存有之中,与其他存有相互纠缠(implicated)。」
布莱恩特指出,平本体论可以统一两个世界,将人类与非人类合成一个共同的集体。平本体论之「平」,在于它不区分存在的事物类型,而是平等对待所有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布莱恩特将他的OOO理论命名为「客体的民主」。不论是烤辣椒(capsaicin pepper)起泡的表皮,还是它注定要浇上的安其拉达的烹饪史,平本体论都抱有同等的兴趣。
想想图灵,如何才能将计算机平本体论化呢?一般意义上,它不能通过基于符号逻辑的「计算」的广泛定义甚至诸如图灵机这样的抽象来完成。相反,「计算」(或其他任何事物)的本体论必须特异(specific)而开放(open-ended),如是才能不那么容易落入系统运作性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之陷阱。我将选取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例子:1982年为雅达利视频计算机系统(VCS,Video Computer System)改编的 E.T. 电子游戏。 E.T. 是什么?平本体论需要的答案多种多样:
E.T. 是由6502个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的8kb(千字节),人类可以把它看作是ROM的十六进制转储。每一个值都对应着一个处理器的操作,其中有些还会取出操作数。例如,十六进制的$69就是加值的操作码。
打包好的ROM其实只是游戏汇编代码的重格式化版本, E.T.也是它的源代码,是运行游戏的机器操作码的一系列人类可读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人类稍微可读的)助记符。例如,源代码中使用了助记符「ADC」来代替十六进制值的$69。
E.T. 是射频(RF)调制的频率:「电视接口适配器」(TIA)是一种定制的图形和声音芯片,当用户输入和程序频率改变了TIA上的存储器映射寄存器(MMR,memory-mapped registers)中的数据,就产生了这种频率。<17>TIA将数据转换为无线电频,并将其发送到电视的阴极射线管和扬声器。
E.T. 是掩膜只读存储器(mask ROM),后者是一种集成电路的类型,其上的储存器被硬连线到一块蚀刻好的圆晶上。这种ROM的掩膜版制作成本很高,但量产成本很低。
E.T. 是用螺丝固定在一起的模压塑料卡带,上面覆盖着粘上去的胶印标签。里面装着一个掩膜ROM,它的两侧是一个控制杆和一根弹簧,当雅达利VCS控制台启动时,芯片的触点就会露出。
E.T. 是消费品,一种包装在盒子里的产品,用于零售,附有印好的说明书和包装纸盒,挂在挂钩上或放在架子上。
E.T. 是产生某种体验的规则或机制系统,这个系统大致对应以下故事:一群孩子试图保护一个流落在地球上的外星植物学家,使他免受政府和科学的暴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排外式的好奇。
E.T. 是互动体验,玩家可以单独参与,也可以环聚在电视机前一同分享。
E.T. 是可以被拥有、保护、授权、出售和侵犯的知识产权单元。
E.T. 是收藏品,一种可以用来交换或展示的绝版或「稀缺」物品。
E.T. 是描述1983年电子游戏大萧条的标志,这次市场崩盘部分归咎于低质量的「铲件」(E.T.常被引作主要案例)。就此而言,「E.T.」这个标志不仅代表着一个虚构的外星植物学家,还意味着极端的失败,以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游戏」:阿拉莫戈多堆填区中著名的游戏垃圾场,导致大崩溃的复杂而贪婪的文化和设计约束,还有此后过于简单化的找替罪羊的过程——换言之,「E.T.」是雅达利的「滑铁卢」。
所有这些类型的存有都同时存在,却又相互独立。没有唯一「真实的」E.T.,无论是作为叙事的结构<18>、人物和事件,还是产生它的代码,或是卡带—机器—播放器—市场的组合,亦或是介于几者之间的任何事物。拉图尔称之为「不可化约论」:「没有事物可以被化约成其他事物」,即使某一事物的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其他事物的转化。
拉图尔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是指在人类或非人类的网络中,行动者相互行事、进入或退出关系。我的「单元运作」(unit operation)概念——后文将回到这一概念——提供了另一种模型:一个单元由一组其他单元(同样是人或非人)组成,无论规模。这将允许我们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斯库拉 (Scylla)和科学化约主义的卡律布狄斯 (Charybdis)之间游刃有余:就「计算」这类研究主题来说,前者是对媒介研究或社会科学分析的常见批评,后者则是形式或物质分析的共同问题。 E.T. 永远不是刚才提及的事物之一,也不是所有这些事物的集合。吊诡的是,平本体论允许它两者皆是,或一无所是。我们可以区分「作为代码的程序」和「作为游玩的游戏」的本体论地位,而不需要求助于游戏的观念性概念,无论是作为形式、类型还是先验。平本体论的力量源于其不慎。它拒绝区分,欢迎一切进入存有的殿堂。
小本体论(Tiny Ontology)
平本体论是种观念,是各种形而上学立场都可以采用的价值。我拥护这一原则,但我也希望继续拓展它。存有既多样又统一(unitary)。我们要如何描述它?
我欣赏拉图尔的答案,他把所有事物都置于关系网络之中。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对拉图尔来说,存有似乎过多地归因于关系,因此,相互作用位于事物存有之外而非之内。另外,「网络」是一个过于规范化的结构,一个由秩序和先定(predefinition)驱动的结构。为了保存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一种慷慨的努力或许会将「网络」替换为拉图尔后来提出的「纠葛」(imbroglio)——「永远不清楚谁和什么在(其中)行动」。 拉图尔原本举过一个「纠葛」的例子,可它却不幸地被人类的知识所束缚,例如阅读报纸就将我们卷入到不同场域和区域的纠缠之中,它们相互联结却也交杂(hybridize)。<19>(拉图尔说:「交杂的(报纸)文章勾勒出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技术、虚构等方面的难题……每一天,所有文化和所有自然都会被重新搅拌……然而,似乎无人为此而困扰。」)但就我的口味来说,「纠葛」还是太过形式化也太过组织化。纠葛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窘境(predicament),当然,也是种混乱(muddle),只不过是戴着单片眼睛的混乱。
作为替代,也许我们可以采纳行动者网络理论家约翰・罗(John Law)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罗氏讲了个故事,他帮助开展一项研究计划,旨在调查一家医院信托基金对酒精引起的肝病患者的管理情况。研究者很快发现,宛如处在官僚主义的状况中,这家基金的组织丛结(complexity)相当可观。在部分案例中,市中心的咨询中心建议病人前往治疗项目,但他们必须先行预约。然而医院里许多人并不这么看待咨询中心,他们认为咨询中心是一个不需预约的治疗场所。罗氏实在地总结到,这种情况是一团「乱麻」(mess)。
罗氏将「乱麻」提升为一个方法论层次的概念,一个抵制整齐、成堆的连贯(coherence)分析之创造的概念。相反,有必要追求「非连贯」。罗氏说:「谈论「乱麻」就有这类问题:它是那些执着于把事情弄得整齐的人所使用的贬义词。我自己更倾向于放松边界控制,允许非连贯显现。或者说,要开始思考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使之显现。」
请注意罗氏的「乱麻」与结构主义进路的形式论之区别:它既不是某种包罗万象、解释一切事物的系统运作,也不是一套文化习俗,更不是为了在光洁的桦木地板上举行一场特别精心安排的狂欢而制定的规章制度清单。它对诸事物(而不只是参与活动的人类行动者)进行松散而快速的结构化处理,不论它们是什么。
一团乱麻不是一「堆」(pile),后者即便处在碍手碍脚的不便境地中,也能保持整齐连贯。一团乱麻不是某种更高层次的优雅之物。它不是一个智力项目,需要由身穿马甲核保人加以评估并管理其风险。一团乱麻是一搓(strew)不合宜,甚或令人厌恶的事物。一团乱麻是一场事故。<20>一团乱麻是你在不想找到之地找到的事物。我们避之若浼,可它就在那里,我们必须处理。
抛开其美学吸引,我发现「乱麻」之所求和「纠葛」相去不远。如果说网络太过有序,那么乱麻就太过无序。与平本体论一样,它把事物铺开以接近它们。它为存有的大量散布描绘了一幅即便不算骇人,也多少有些棘手的图景,却没有提供任何能将它们统一起来的共同基础。此外,即便只看隐喻,乱麻也沾染着相关论的色彩:一团乱麻是人类行动者无法把握的东西,它们无法被有序地整合进网络。可谁又能说我的乱麻不是火山的网络?谁对现实的构想能够框定其他一切事物的现实?
的确,相关论的问题就是外在现实的问题。科学就像一艘航天器,杰出而疯狂的航行者望着花哨的挡风玻璃,渴望发现并绘制外面的世界。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则反向运作,聪明的时间旅行者加倍回溯,证明外部世界自其伊始就在内部,只是妄想和天真使它看似独立。两种情况都在用三维性的隐喻来描述存有的宫殿:要么是一个可以为人类文化的利益而探索和映射的结构,就像一座大教堂;要么是围绕着这个结构的形状,形状赋予结构以形式,就像一块土地使大教堂最初得以建立。
存有之理论往往宏大,其实不必如此,因为存有相当简单,甚至可以通过卡车司机帽子上的丝网印刷来呈现。我称之为「小本体论」(tiny ontology),正是因为它不需要(也不该需要)一篇论文或一部巨著。并不是说存有的领域很小——恰恰相反,我很快就会解释——而是说,描述存有所需要的基本本体论装置应该尽可能地紧凑而朴素。
对平本体论的二维平面来说,一种替代性的隐喻是无空间的一维。如果任何一个存有不亚于任何其他存有,那么与其将这些存有散布在二维表面上,不如将它们折叠到一个点的无限密度之中。我建议用小本体论的「点」(point)来替代平本体论的「平面」(plane)。<21>它是密集的一「团」(mass),全然囊括万物——即便它无章散布宛若一团乱麻,或是条理组织像是一张网络。
在广义相对论的惯常描述中,黑洞是一个奇点,一个物质达到绝对密度的点。但物理学家尼科德姆・波普瓦夫斯基(Nikodem Popławski)提出,如此巨大的质量(mass)的引力会发生逆转,导致物质再次膨胀。波普瓦夫斯基认为,黑洞可能因此包含了整个宇宙——我们甚至可能生活在某个黑洞中。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因为即使人们能够接近黑洞,由于引力时间膨胀,对观察者来说,时间也会变慢。因此,需要通过「思辨」来考虑存有于奇点之内的意涵。
恰好,哈曼也将事物本身与黑洞作了比较。哈曼说,每个客体「不仅被一个空洞的盾牌保护着,使其免受外部事物的影响,其中还庇护并哺育着一个喷发着的、地狱般的宇宙。」平本体论表明,存有之间并无等级,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存有本身与其他任何客体并无二致。存有的撤离不仅是酸奶或扁桃体或小熊维尼的特征,也是其自身的特征。要对小本体论进行装饰式地(embroiderable)速记,或许可以简单将其读作——是(is)——然而,这只是因为语义的连贯不能包含在单独的「我」(i)之上的小点中。
单元运作(Unit Operations)
存有的一面,是难以理解的密度,是黑洞,在黑洞之外,所有差别都坍缩成了无差别。然而,在另一面,存有又一次膨胀到了价值整个宇宙的东西中。得益于小本体论的结构,这是种分形关系,无限且自相似。集装箱船和货舱、集装箱、液压缸、压载水、扭锁、绑扎杆、船员、船员的针织衫以及编织这些服装的纱线一样,都是一个单元。这艘船建立了一个边界,它所包含的一切事物都撤离到它的内部,构成它的那些个体单元也在这样做,且方式相同、时间同步、处在同样基本的存有层次上。用列维・布莱恩特的说法,这种奇怪的分体论强调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怪异关系。<22>对于OOO来说,「一个客体既是另一客体的一部分,同时其自身又是一个独立的客体。」事物既独立于其构成部分,同时又依附于它们。
因此,一个客体是一个怪异的结构,它可能指向一个「正常的」、中等大小的客体,如烤面包机;也可能描述一个巨大的、无定形的客体,如全球运输物流。蒂莫西・莫顿有句俏皮话说:「客体就像《神秘博士》中的塔迪斯(Tardis),内部大过外部。」事物既普通又奇怪,既大又小,既具体又抽象。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有效地描述它们的特征。
过去,我曾建议用「单元」一词作为客体或事物的同义词和替代品。部分是纯实用主义考虑:我写的是「计算」(computation),而在计算机科学中,对象(object)和面向对象(object-oriented)两个术语有明确的含义,与计算机编程的特定范式有关。当哈曼提出「客体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这个术语来命名一套拒绝优待人类与世界之关系,并由此将之作为唯一关系的立场,他从计算世界中借来了这个短语,并在哲学中赋予它新的生命。我不反对(objection)术语的再利用,但在讨论我感兴趣的领域的特定对象(object)时,「客体」(object)有时会带来混乱。
还有其他避免使用这一术语的原因。首先,客体暗示着主体,而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是相关论的核心。事实上,OOO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主体的概念不相容,问题在于假设只有一种(one)主体——人的主体——具有旨趣或重要性。在修辞上,有充分的理由绕开这一问题。首要的方法就是避免使用客体一词。客体导向的实在论的确聚焦于找回世界中失落的物质,并使之回到哲学探究的中心,但仅是物质性的事物并不能充分体现这种关注。援引小本体论的原则,客体导向思想中的客体包含万事万物,从物理物质(「思乐冰」冰冻饮料)到属性(冰冻性)到市场(便利店行业)到符号(「思乐冰」品牌)再到观念(关于哪里可以找到7-11的最佳猜测)。<23>「存有」的密度让它变得杂乱无章,总是触及其他一切事物,无暇顾及差别化。任何事物都足以加入其中。
说到这里,事物试图用自己替代客体。与客体不同,事物既可具体亦可抽象。然而,「事物」也有一段火药味十足的的哲学史。康德的「物自体」(das Ding an Sich)是不可知的元素,必须通过经验来推断。对海德格尔来说,事物是人类创造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客体。在一个典型的词源学分析中,海德格尔指出,Das Ding 原指聚集或组合。海德格尔将这种聚集解释为人类与世界的召集。于海德格尔,当客体从使用——当然是人的使用——中的存在的背景中脱颖而出时,客体就成了事物。对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来说,「事物」(Thing)是失落的客体,是主体中缺席的东西。雅克・拉康将弗洛伊德对「事物」(Thing)的神经元理解转化为符号学理解:「事物」(the Thing)是意指(signification)之链上切下的能指,拉康后来称之为「小客体」(objet a)。哈曼交换使用这些词(「客体,工具—存在,实质或事物」),但「客体」仍然是其最爱——或许是为了部分回应事物的哲学史。
也有一些事物延伸到了批评理论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比尔・布朗(Bill Brown)提出的「事物理论」(thing theory),可类比叙事理论或文化理论。布朗做出了些成果(他引用了弗朗西斯・蓬热——那位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关于「火」「雨」「橘子」和「香烟」的诗句),但是,与前辈海德格尔一样,评论家对 「事物」的兴趣仍出于对人的关注:原来布朗是打算用事物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无生命的客体如何构成人的主体」。一方面,事物提供了遮蔽客体的有用方式,使我们想起它从其他事物中撤离。但另一方面,这种撤离的主体常常是我们,以至于对事物的依赖往往带着沉重的包袱。
困扰事物的最后一个边界问题:具体性(concreteness)。当烤辣椒(capsaicin pepper)的皮在旋转烘烤机火热的钢铁格栅上起泡、摩擦时,它与其容器(vessel)的相遇,既不可否认的亲近与熟悉,却又遥远而异样。当人类小贩转动滚筒<24>,或是将它放在附近一辆红色皮卡翻下的尾门上时,滚筒、把手、尾门、沥青、胡椒、金属、丙烷,都与他(也与彼此)保持距离。但在此场景中,另一种事物也将产生距离:那些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即胡椒和钢铁、尾门和Levi's 501s、沥青和皮卡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作为客体的事物,也包括它们的抽象甚至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发生得又快又热,事物的小小宇宙持续地碰撞、摩擦,像聚合物般相互链接。
看起来,「事物」(thing)太急于将诸事物固定下来,以满足小本体论。一个事物不仅是人类的事物,也是许多其他事物(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事物。然而,一个事物仍旧统一(unitary),即便它发现自己正改变并凝聚成存有内部不同时刻的种种构型。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诸客体或诸事物的名称,单元(unit)颇有助益。它是个暧昧的术语,对它所命名的事物之本质无动于衷。它孤立、统一且特异,而不是简单的整体之部分,或是如原子般,在本体论上基本且不可分割。正如我在别处所说,「单元」在系统论与复杂性理论中已有先例,也应用于生物学、控制论、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社会理论,以及无数试图将现象解释为系统中相互关联的部分的自主行动所产生的效果的其他领域。与直觉相反,系统和单元同时代表了三件事情:首先,单元孤立而独特;其次,单元围绕(enclose)着系统(整个宇宙的价值);再次,单元会成为另一系统——通常是许多其他系统——的部分,因为它在系统周围推挤(jostle)。
这些单元之系统(systems of units)因意外/事故而断断续续地结合在一起。我借用「运作」(operation)一词来描述单元的行为与互动方式。在系统论中,运作是「一个基本过程,它接受一个或多个输入,并对其进行转换」。任何一种功能都可以理解为运作:泡茶、脱皮、光合作用产糖、点燃压缩燃料。过去,我主要用「单元运作」(unit operation)来描述符号系统——尤其是计算性意指(signification)的独特属性<25>,因为这种表达总依赖于程序性行为。但是就哲学论,单元运作是个更具普遍性的概念,足以描述任何系统。的确,正如哈曼从计算中借来「客体导向」一词,我也从化学工程中偷出了「单元运作」,它原本是指一个过程中的诸步骤(提取、均化、蒸馏、冷冻等等)。
单元揭示了存有的一项特性,即事物、客体之咬合(occlude)。小本体论的密度与凝结也有闪烁(flip)的面向:某物总是别的某物;某一机制中的齿轮,是另一组构中的关系,又是另一整体中的部分。在黑洞般的存有之密度内,事物经受着膨胀。宇宙大爆炸在本体论上的等价物,存在于每一客体之中。存有在膨胀。
在我原初的单元运作理论中,我用阿兰・巴迪欧的集合论本体论(set theoretical ontology)来哲学地描述这一膨胀。巴迪欧采用了格奥尔格・康托尔的集合概念,一种通过列举其成员来描述总体的方法,例如这样:{a,b,c}。任何一个集合的子集{a,b}或{b,c},都包含了该集合总成员中较小的数量。通过将无限表示为集合,康托尔建立了一种超限(transfinity)理论:无限集是一个对应于所有自然数的集合,但一个无限集所有可能的子集的集合似乎是一个「更大的」无限。
围绕康托尔关于超限数(transfinity numbers)的见解,巴迪欧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对巴迪欧来说,存有就是成员资格(membership):「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元素(To exist is to be an element of)。」为使成员资格具有本体论意义,必须存在某种过程,以便将诸存有从有效的诸超限子集中独立出来,用彼得 · 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的话说,就是将他们「一化」(one-ify)。这个编造新的多重性的过程,巴迪欧称作「计数为一」(count-as-one[compte-pour-un])。至于这种姿态的输出,即「一个以特定方式构型的集合」,被称为「情势」(situation)。
哪怕巴迪欧操着一口数学黑话,构型(configuration)仍可帮助我们理解小本体论。如果一切事物都同时且平等地存在,没有任何差别,那么,诸单元感知、关联、考虑、回应、取消的过程,或其他任何相互咬合——即单元运作发生的方式——的过程,都是构型性的过程。在此<26>,巴迪欧的「计数为一」提供了有益的类比,说明存有一面的黑洞密度如何膨胀进存有另一面的无限部署(arrangement)之中。存有的东西(stuff of being)与物质、关系和概念相推挤(jostle),因此持续地变动并重新部署自身,也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中重新定位。
可以这样想:集合为存有提供了爆炸式的图景。在单元密度闪烁(flip)的一面,它像黑洞中包含着的宇宙一般膨胀。这种膨胀被编入集合,一种对单元成分的结构化描述,类似一张海报,呼唤着大型机械(集装箱船或巨型喷气式飞机)中的许多机制。
然而,巴迪欧的本体论有一个问题,使我无法全盘采用它:谁来计数?巴迪欧留下的答案暧昧不明,他将存有等同于数学的无结构的非人格性。可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在哲学史中,一位先验行动者或人类自身,总是对存有的孤傲(aloofness)不屑一顾。鉴于集合论是一种源于人类的、对成员资格概念的符号化抽象(即使它向往普遍性),鉴于巴迪欧所举出的计数为一的例子几乎都是人类的经验(政治、艺术、爱情、诗歌),不可能将「计数为一」看作朝向单元的一步。
相反,考虑这个简单的宣言:单元运作(units operate)。也就是说,事物不断地在自身内部策动(machinate)并相互咬合,行动并对属性与状态作出反应,与此同时还保持着某种秘密。阿方索・林吉斯(Alphonso Lingis)将这些行为称作「结构起事物之知觉的命令」:「将坚韧的外壳、密集的暗黄色与松散的内部果肉凝结为西柚的内在秩序(inner ordinance)」或是「芒果、柳树或一块光滑的石头的内在准则(inner formula)」 这些事物的内在秩序或准则会撤离;它们没有被把握,即便它们命令般地安排知觉。
这种运作的尺度多种多样:细胞进食并分裂,以重新填充器官,使血液循环到举起墨西哥卷饼的身体四肢。联合收割机上的旋转喂料器收集谷物,将它们推过车辆的切割器,送到螺旋推运器上,再运进机器的脱粒滚筒中。<27>虚构的阿尔达(Arda)语言的语文学构成了中土历史和传说的基础,它们被J・R・R・托尔金记录在《霍比特人》、《指环王》和《精灵宝钻》等文学作品中,这又为粉丝对这些世界的解释提供了依据。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各单元彼此分享,通过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行动与姿态相咬合,它们联合聚集,复又退隐。
如果坚持巴迪欧的数学隐喻,一个集合的成员描述了它们的构型,却没有描述它们的行为。我们可以采用巴迪欧的「事件」(event)概念来描述事物之行动(doing)的特点,但对巴迪欧来说,事件并非司空见惯的事项(affairs)。相反,它们是全局性的变化(这是另一个相信集合只能为人类所构型的理由)。集合成员最简单的行动仍然没有被说明。由此观之,显然,计数为一的方法最初并未处理集合成员之间平凡的相互作用。巴迪欧的本体论似乎无法描述事物的普通存有,而只局限于人类变化的非凡存有。
在《单元运作》中,计数为一并非单元运作的模型或类比,而是一个相关的观念。问题在于:事物不只是它们所做的事,事物确实在做事(do indeed do thing)。且事物做事的方式(way things do)值得被哲学地思考。单元是孤立的诸实体,一起被困在其他单元中,不适地彼此擦肩而过,却永远不会重叠。单元从来不是原子,而是集合,是共同作用为一个系统的其他单元的组合(grouping);单元运作总是分形。这些事物彼此好奇(wonder),却从未得到确认。这就是单元运作的核心:它为说明客体的现象命名。它是一个过程,一类逻辑,或者如果你愿意,一种算法,一个单元试图通过它来理解另一个单元。用巴迪欧的话说,它是情景的意义,而非理解建立起情景的计数为一的意义。用怀特海的话说,它是一种摄受能力。用胡塞尔的话说,它是脱离了意识、思维、意象以及人类推理中其他意外事件的意向活动(noesis)。用林吉斯的话说,它是事物邀请其探索的内在准则。客体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因此每一客体都有其进路,有其意义制造的逻辑,<28>通过这种关系,它们追踪着另一种真实的现实,就像事件的地平线帮助天文学家推断黑洞的性质。「单元运作」为客体感知并参与(engage)其世界的逻辑命名。
思辨(Speculation)
思辨实在论对人类—世界之相关的拒斥诱惑着我。可问题依旧存在:即使拒绝相关论,认为它公然地、自私地以人类为中心,我们又要如何面对那些事物,如果它们同时也是人类制作或使用的复杂结构或系统?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我们该如何努力理解世界上特定(particular)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之外进行,即使我们可能是其原因、主体或受益者?我们应如何理解绿辣椒或集成电路,既将事物留给它们自身,又保留事物与它者(我们也在其中)之间的互动?
哈曼如此作答:我们对事物的观念确实在场,但事物本身仍在无限撤离。梅亚苏的答案些许不同:事物在数学上可思,即便其不可感。这些回答难以在实践中应用。但与形而上学家来往,人们又能指望什么?抛开花哨的一面,思辨实在论仍是第一性原理的哲学。它们仍未关注特定的实现(implementations),哪怕它们仍能与之相容。然而,如果它的目标是纠正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那么一种超越第一性原理、进入形而上学「实践」(practice)的延展,仍能为思辨实在论带来助益。
也许我所寻求的是理论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辨实在论(pragmatic speculative realism),比詹姆斯式的实用主义更软:一种应用的思辨实在论,从客体导向的工程学到本体论的物理学。这种方法将鼓励对现实的物质客体及其关系,进行实质性的哲学处理。若是认真对待思辨论(speculativism),为什么哲学不能像思辨小说或魔幻现实主义那样,寻求(muster)一种具体的基础?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提倡对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可能世界进行思辨,但这种思辨与现实世界的耦合,<29>应超过「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一词寻常所指。同样,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或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魔幻现实主义表明,壮观(spectacular)即实在,至少它确实包括着文化的诸多方面。在此状况下,哲学家的抽象化倾向让位于小说家的特异化倾向。其结果是某些特定的事物,它们的枝干在概念性的天穹中摇曳。
在特定的时间,对任意给定客体,存有领域中仅有某些部分显明。对乌冬面来说,汤碗的存有与面馆出售它的商业交易或食客大声吸入它的社会习俗之间并无交集。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比起塑造、煮熟、消费或消化它的人,面条自己所处的交缠(entanglement)中丛结更少。
当我们问起「成为某物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something),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世界之存有的把握。这些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刻画出与客体相关的诸事物,它们不一定显明,甚至未必可知。声称世界只是我们对它的感知或认识——指责这种立场是「朴素实在论」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乌冬面或核弹头的存有之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客体超出(exceed)了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或可能的认识。
事物之所是(That things are)并非某种辩论。某一特定事物的意义,恰恰是另一事物之所是: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某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之意义(significance),依双方的看法而变。由于单元从根本上对彼此的无限中心(infinite centers)一无所知,与之相关的单元运作也就有所不同。一个单元理解另一单元的手段并不普遍,不能通过自然法则、科学真理,甚至它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单元运作需要依据不可能的验证来进行演绎——单元从未将彼此看作其所是,而只是当作一出滑稽戏(burlesque)。在单元运作的基础上开展哲学工作是一种思辨的实践。
「思辨」在哲学中的特殊意义必须被克服。<30>传统上,思辨哲学是指那些不能通过经验或科学来验证的形而上学主张。正是在此,胡子拉碴、穿着凉鞋的哲学中散漫的抽象,在诸如「什么是存有?」或「什么是思想?」这样的问题中扎根。思辨哲学有时与批判哲学相对,因为后者涉及理论的测试和验证。
可是,也存在另一种思辨哲学,它描述存有的本质,而非人类哲学家朝向存在的通路。思辨实在论不仅是将存在与思想相分离的思辨哲学,也是要求事物之思辨(claiming that things speculate)的哲学,甚至还是思辨事物如何思辨(that speculates about how things speculate)的哲学。
思辨是一面镜子,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镜子,一种将世界的真实面貌毫无阻碍、不加变形地映射回来的装置。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故事已然证明,映像的差别足以涵括力量,包括醉人的爱情之力。这一教训不止于神话:从上古到中世纪,镜子都是一种不精确的装置,通常是一个抛光金属的凸面圆盘,映射出足够的光线,让观众对放在它面前的人物有种粗略的感觉。只是一种粗略的感觉:用哈曼的话说,一种表象,一种模仿,一种漫画(caricature)。思辨的窥镜(speculum)不是扁的、平的、真空喷射过一层熔化的铝的玻璃板,它是用金属捶打成的游乐场镜子,它的变形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倒错,一种单元之感觉的倒错。
面对这般古怪,人们必须像狂欢节的报幕员(carnival baker)而非学者一样,通过有根据的猜测来推进下去。思辨不只是诗意,但确有部分如此,确有部分是某种创造性行为,使诸存有诚挚却困惑地注视着彼此。万事万物都如地铁上的人群般,与陌生人挤在一起,不适地亲密接触。
哲学家的工作不仅是记录此种情况(documenting the state),也要在特定的情形下与之搏斗(making an effort to grapple with it)。我们或许会想到海德格尔在科学地思考(thinking scientifically)与本体论地思考(thinking ontologically)之间所作出的区分,可这种概念无法再往前,因为它只限于人类的思考和行动<31>——深思面条碗或联合收割机的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y)并无太多意义。
如果单元运作刻画了客体的逻辑,那么它们就属于现象学——形而上学的领域之一,关注东西如何出现在存在面前——的范畴。与海德格尔不同,埃德蒙德・胡塞尔将感觉理论化为一种一般原则,然而,由于称其为「意识」(consciousness),他又将之投射到人类中心的样式中。可胡塞尔的意识仍是一个过程,它仍能从大脑、微处理器、内燃机和死面的物质意外/事故中抽象出来。意识(或可能取代它的任何术语)把握客体的方式本身(itself)就是思辨的主题。这就是说,考虑两个单元之间的遭遇,每个单元的现实之给定性或其表象,都并未给予我们。用林吉斯的话说,芒果的内在准则永远无法被掌握。
对胡塞尔来说,为了认真考察表象,必须避免常识性的预设。我们无法逃避自己描绘世界的态度,但我们必须将它的有效性「括出」(bracket)。这种括出我们对知觉的自然假设的程序,胡塞尔称作 epoché(έπχή,悬置)。正如丹・扎哈维(Dan Zahavi)所说,悬置「意味着对现实态度的改变,而不是对现实的排除。」
考察与诸存有相交缠的单元运作需要思辨,而思辨则需要某种类似胡塞尔现象学的行动。思辨与悬置相似。它产生了胡塞尔意义上的超越(transcendence):一个具体而独立的概念,它抓住客体那炙热的、无限密集的、熔化的核心,并把它抛射出去。在那里,它成为它自身的单元,用于一套特定互动的,一种新的、创造性的单元运作。可以肯定,这是一种现象学。但这是一种如弹片般炸裂的现象学,它将作为孤独意识的人类留在身后,就像旅行者号飞船在超越太阳系边界的路上,将日球层顶留在身后。
异形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
哈曼用「黑噪音」来描述外围客体的背景噪音:「它不是尖锐、混乱的白噪音,<32>不需要人类心智的塑造,它是沉闷客体的黑色噪音,盘旋在注意力的边缘。」黑色(black)是接近沉默的声波噪音的颜色,能够发出能量尖峰(但只能有些许)。类似,在物理学中,黑体(作为一种物体)会吸收它所遭遇的所有电磁辐射,并散发与其温度相称的光谱。黑体辐射在可见光谱上可视,随着温度升高,从红色到白色。在其他应用场景中,黑体辐射可以用来评估天体性质。特别是黑洞,依靠它所释放的黑体辐射类型即可进行识别。
正如天文学家通过围绕恒星的辐射能量来理解恒星,哲学家也通过追踪客体对周围以太的影响来理解客体。如果客体的黑噪音类似于因量子效应从黑洞中偏折出的霍金辐射,那么或许我们就该在此,在未知的宇宙中,建立起一种方法。
2009年,在一个世纪的射电望远镜实验后,SETI有了新的启示:如果其他世界上存在外星人,它们可能会用Twitter。该组织的「地球发言人」(Earth Speaker)项目邀请网站用户回答如下问题:「如果我们发现地球以外的智能生命,我们是否应该回复,如果是,我们应该说什么?」利用集体智慧的可疑力量,SETI收集了诸多可能的通信,例如「从你的云上下来,喝点龙舌兰……我们可以讨论许多事情。」该网站的研究声明解释称:「比起确立某种统一的『地球消息』(Message from Earth),通过将PI沟通模型(PI’s Dialogic Model )用在星际消息设计上,本项目倾向于帮助人们理解,关于合适的星际消息内容的不同观点。」 「地球发言人」表明,时间并未改变SETI的基本假设:如果宇宙中存在生命,SETI应该能够识别(recognize)其对应者(counterparts)——它们会将诸如VLA这样的射电天文仪器指向它们所在的方向——并理解(understand)其答案。
20世纪80年代,多产的德裔美国哲学家尼古拉斯 · 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反对SETI坚持的观点,即外星生命的迹象与可探测的通信技术类似。雷舍尔认为,外星生命或许如此异样,<33>以至于人类无法理解其科学与技术;我们永远无法将其视作智能。我将雷舍尔的想法推得更远:外星人不只在通信技术上脱离了我们的理解,其「生命」概念本身都有可能与人类不同。外星人或许根本不是生命。正如伯恩哈德・瓦登费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所说,异形/外星人是「经验与感觉的特定范围的不可接近性。」然而,瓦登费尔斯还是跟随胡塞尔,将对异形的经验(Fremderfahrung)描述为主体间性的过程,也就是对他人的经验。可异形并不局限于另一人(person),甚或另一造物(creature)。对它之外的一切来说,异形是任何事物,也是一切事物。
真正的异形,即便完全包围着我们,也在无限地退隐。它并未隐藏在外宇宙的黑暗中,或深海的海陆架内,它就在眼前,无处不在,无所不是。山峰或石膏层、辣椒烤炉或鹿弹、微处理器或ROM芯片,它们与我们的交流,或是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不比雷舍尔的外星生命更多。这一迹象颇具启发,也使人谦卑。思辨实在论的确需要(require)思辨:在全然无法理解的事物构成的奇异世界中,趁着夜色,蜿蜒而行。作为哲学家,我们应当放大事物的黑色噪音,使它们内部的东西的共振频率,以可靠的、令人满意的方式,嗡嗡作响。我们应当写下关于事物的单元运作之过程的思辨性虚构。我们应当用油脂、果汁、火药和石膏弄脏双手。我们应当去每个人都去过,却极少有人逗留的地方。
我将这种实践称为「异形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