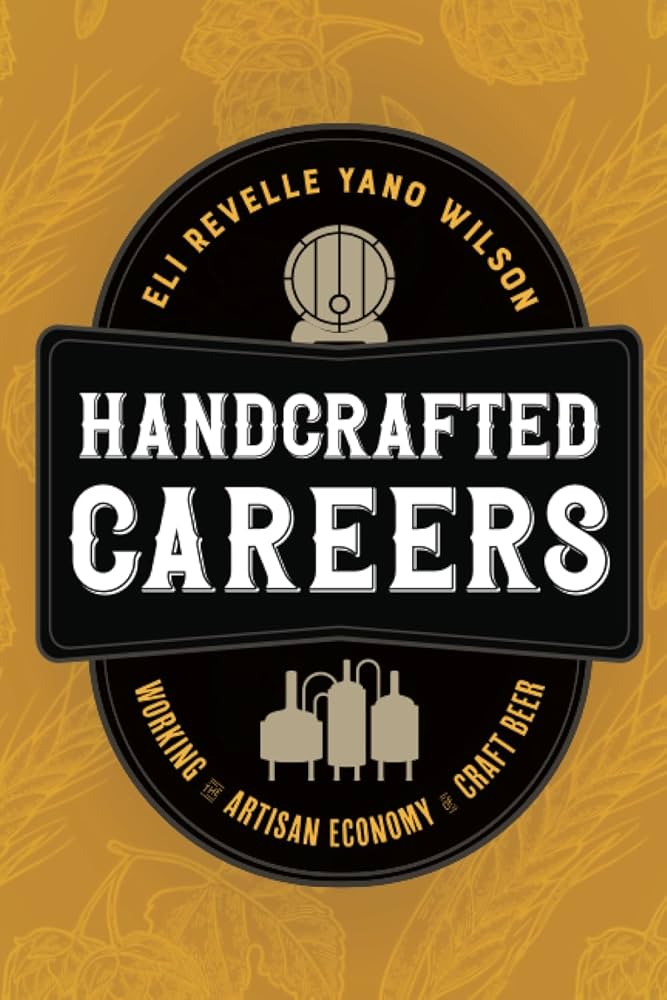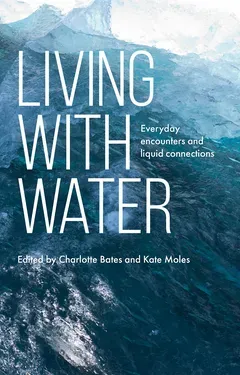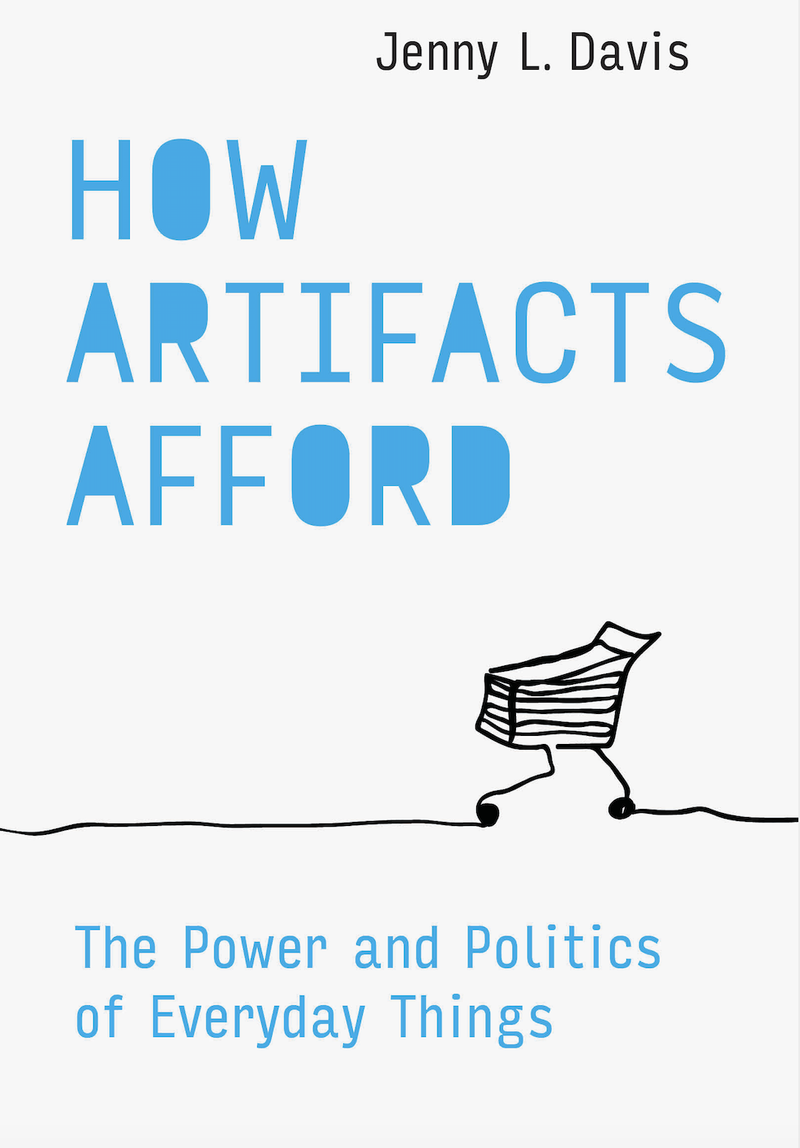行动:妥协的因果
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1]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以一种相当暧昧地姿态面对着个体的能动性问题:一方面,那些脑内残存着「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2]的人们似乎并不能主宰自己的行动,甚至无法对其负责;可另一方面,这出政治笑剧中的主角,路易·波拿巴,却被描述成了一个上蹿下跳的小丑,在各方势力之间游走不定,一步步完成了「蚂蚁变狮子」的壮举。
这种张力最为清晰地体现在马克思为此书第二版撰写的序言之中:「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IV)」在这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会转引的话中,如大多数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试图将个人行动纳入历史图景(阶级斗争)的意愿。然而正如「可能」两个字暗示的那样,在这句话未能表述的部分中,个体(波拿巴)实际上达成了历史提供给它的可能,考虑到这一可能的塑造也并不能脱离更多的个体行动,我们似乎观察到了一种在历史(History)与个体行动之间的不情愿的妥协——历史不得不在自己之中掺入诸多的偶变性以保持自身的客观。
不妨如是理解:在维持宏观历史图景的前提下,个体行动必须经过解释才可被放入历史之中,这种行动越是「反历史」,便越是需要连篇累牍的解释才可能被纳入历史(以防止历史的破碎),而解释的冗长同时便也意味着历史尺度的缩小与偶变性的增加。《雾月十八日》一书所呈现出的正是这样的困境,为了解释那出笑剧为何会发生在历史之中,马克思拆解了整个表演,说明它的舞台、布景、剧本乃至观众都可以被历史地理解,唯独那些表演者们无法呈现为历史(History)的结果,反而被指认为历史(history)的因由。
让我们暂且卸下历史的包袱。《雾月十八日》中呈现出的妥协未尝不能理解为一种因果性的问题,即如何在时空殊异的客观事件序列与个体行动历程[3]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因果关系。不妨将客观事件发生的时间称为「物理时间」,将放置事件序列的时间称为「抽象性时间」。如果说「抽象性时间」尚可被理解为「物理时间」的一种映射,那么个体行动历程所处的「主观时间」则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物理时间」的桎梏。借用孙宇凡的区分,「物理时间」是只有「稍前」和「稍后」两种形式的时间,「抽象性时间」则为「物理时间」提供了一个单一的轴线(这一轴线同时暗示了一种因果关系),而「主观时间」却呈现出一种奥古斯丁式的时间观,被主体认知为「过去、现在、未来」(记忆、注意、期望)的三分[4]。
回到行动历程上,个体的行动所依赖的并非「物理事件」或是「抽象性」时间,而是可以被个人裁剪与选择的过去与未来(记忆与期望)。这些记忆与期望或许与「物理时间」甚至「抽象性时间」有所重叠,但更多时候却是破碎不堪,难以被恰当地放置在「物理时间」或「抽象性时间」之中。
正是这种「主观时间」与「物理时间」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造成了因果推论的困难。对于这一问题,或许成伯清所说的叙事社会学(聆听多重叙事以寻找其核心)是一种解决之道[5],然而这一策略中却隐含着对客观事件序列的否定(「客观事件」被化约成了叙事一种),从而至少与马克思所采用的路径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客观事件与外部历史的存在,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实际引入了一种被吕炳强称之为「士多噶因果性」的因果推论方式,以浅露的客观事件为「果」去推深藏的个体行动历程之「因」,通过带着关于「因」的假设返回个体所处的生命场景之中,将客观的事件序列视作曾经发生的行动序列,尝试证明个体的行动历程「非此不可」[6]。这一证明倘若成立,则客观的时间序列与主观时间轴之间便得以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多种时间性之间的潜在冲突也就得到了调和,因果关系至少在作出一定妥协的基础上得以成立。
事件:后设的定义
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动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7]
通过倒转因果之间的证明过程,马克思成功地在《雾月十八日》中建立起了调和多种时间性、说明历史因果的可能。应星借用苏维尔(Sewell)的术语将这一努力概括为「开创了将结构史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社会学」,而所谓「事件社会学」的关键则在于「把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三个要素折叠到同一时段的事件分析中」[8]。
然而应星为《雾月十八日》所找到的这一理论支点却不甚稳固。孙宇凡在对苏维尔的事件社会学进行评论时指出,苏维尔将事件定义为「日常发生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罕有一类」,但却并未回答所谓的转型性事件究竟从何而来,反而是采取后果式的或功能式的「事件」定义,后置地将「事件」与「日常发生」(happening)相区分。[9]
自然,所谓的后果式或功能式的「事件」定义本质上都聚焦于「事件」对于结构的作用,区别仅在于前者强调「完成状态」,而后者则涵盖了「未完成状态」。由于强调作用的达成,后果式的事件定义并不能支撑起应星所谓「结构、局势与行动者三个要素的折叠」,因为以后果定义的事件无法呈现在行动者的主观时间轴中,而只能被后置地进行定义与理解。相对的,功能式的定义保证了一定的开放性,允许行动者对「事件」的发现在逻辑上不晚于其「发生」,即保证了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事件本身的感知。
然而即便是保有一定开放性的功能性「事件」定义,其中的「事件」都是去时间化的。在「事件」的一面,是行动者在不停地活动着,促使事件发生;与此同时,当我们将一桩事件同其他的「日常发生」区分开时,我们便必须进入结构分析之中,然而行动者并不具有定义结构的能力,于是我们不得不将时间静止,将原本的动态表述转化为静态分析(幻灯片般地切换不同事件节点上的结构图示),使得「事件」重又失去其「具体」的时间性,落入抽象的时间之中。
当马克思宣称四八年的「六月事变」是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时,他就部分取消了「六月事变」的具体性,将之转换成了抽象时间轴上一个已然实现或未能达成的功能。「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10]与这一判断相近,在《雾月十八日》中,正如其所着力批判的资产阶级代议制那样,每一个「事件」都在对抗着它自己,徘徊在历史阴影与个体行动历程之间。
如何在借用「事件」的同时,从抽象性之中拯救出「具体」(embodied)的时间?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设计了一个精巧的答案:假定历史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通过代际传递与个人生命历程进行流转,那么历史将以教育、环境等诸多方式进入个体的生命之中,形成那些「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些情感与观点占据了个体的「心灵」的相当一部分——而个体正是如此的「心灵」的引导下展开行动。这种带有历史印迹的行动同时可以声明对于未来的期望,而这也就赋予了行动者「历史感」,使得他们可以载着回忆、注意与期望,通过行动或是观念自由地定义与改变「事件」,事件由此与个人的行动历程紧密结合。与此同时,渗透在个人信念中的历史印迹也向事件注入了「历史」的力量,使得行动历程与事件可以进一步延展到历史的层面上,关联起马克思最为关注的阶级斗争的主题。
历史:折叠与交错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脑袋。[11]
无论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反复」「再现」(re-present)与「代表」(represent)的问题还是怀特所说的「构成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态的重大运动」[12],在《雾月十八日》中,历史毫无疑问居于论述的中心,行动与事件皆是环绕历史而展开,且其中处处留有历史的阴影。
在《雾月十八日》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之本质是一种目的论的时间,其客观呈现为某种阶段序列,以线性发展或是下降的方式得到表达。然而为了将物理时间或抽象性时间与个人的主观时间相连接,马克思通过引入「先辈的梦魇」将历史固着在了个人的行动中,而这种梦魇精致地呈现为「雾月十八日」与「拿破仑」等符号的再现。
在诸多符号中,有的(如「雾月十八日」)是以修辞的形式被引入论述,有的(如「拿破仑」)则是在论述之中才「被发现」。不同的符号与马克思的整体观察指向了四八年以来的历史与大革命之间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最终呈现为一次拙劣的模仿,历史的笑剧——与大革命的逐渐激进、不断上升之趋势背道而驰,四八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在不断下降中证明资产阶级代议制中所谓的「代表」不过是一种「修辞」的过程。
在今日的研究中,尝试证明大革命与四八年革命之间关联的论述并不罕见。通过揭示四八年革命与大革命之间的代际关联,罗伯特·基尔德即在《革命之子》一文中以历史学的方式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打上了一个精美的注脚。唯一的问题或许是,这篇文章同样也证明了,在参与四八年革命的不同人群中,可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梦魇[13],而这些梦魇未必能够与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相契合。
于是我们得以发现,与马克思所着力说明的资产阶级代议制下虚幻的「代表」如出一辙,在《雾月十八日》中,通过将阶级图景(历史)折叠到个体之上,将历史的分期折叠到事件序列之上,马克思或许同样制造出了一种「代表」的假想,使得读者相信,《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行动历程与事件已经足以响应那个目的论的时间,构成历史的微观形态。
正如「波拿巴」在小农阶级心中激起往昔的回忆那样,当马克思以阶级为轴线描述事件与行动时,个体便背负了历史的重担,每个人不仅拥有了先辈通过生活世界传递给他们的梦魇,还获得了更加宏大的世界历史赋予他们的命运。事实上,个人并非完全能够发现、理解这一命运:无产阶级错过了自己的六月革命,资产阶级同样数次将到手的权力放弃,转交给了波拿巴。尽管马克思试图将一种目的论式的时间注入到个人的生活之中,使之与事件性的时间、个人主观的时间进行调和,构成一种统一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却预先要求了参与者的「自觉」。
世界历史并非自在,而是必须等待着一些人的发现。在《雾月十八日》中,将确定性赋予未来的马克思更进一步允诺,这一发现必须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因为四八年以来的经验正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不具备推动历史前进所必须的超越性,反而是懦弱的、保守的,因而无法承担历史的重量。然而未来只存在于主观时间之中,抽象性时间虽然告知了一个未来,但这一未来并没有切实的意义;只有在主观时间之中,未来才是值得想望的,而只有那些被想望的未来,才有可能构成某种特定的符号,被人们从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唤醒为事件,转而进入历史。
然而四八年的经验同时也证明了,无产阶级尚不具备这种自觉,它们的脑海里只有梦魇而没有未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在《雾月十八日》所调和的种种时间性中,最后还存在着一种「外在的时间性」,其作用正是对文本内部所揭示出的历史进行招魂。这一时间性从属性上来看与上文所提及的行动历程中的主观时间一致,只不过由于身处文本之外,便呈现出了不同的层次,得以在「元叙事」的角度上关涉到马克思对于历史的感知及历史书写与历史分期的问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外在的时间性大大拓展了文本的复杂性,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内外多层交错的时间、因果关系。
事实上,从写作目的与具体的行文风格来看,马克思行文之时便设计好了《雾月十八日》文本外部的时间性问题。正如那些将这一文本称作「宣传手册」与「战斗檄文」的研究者所感受到的那样,《雾月十八日》正是在对辞藻的强调中嘲讽了四八年以来「辞藻胜过内容」的状况[14],而这种悖反恰恰暗示了一种外部时间的存在。如果辞藻在《雾月十八日》中是某种必要,那么其存在只能解释为对阅读者的召唤。这一召唤既在陈述四八年以来的个体行动历程、事件在历史之中的意义,同时也就将自己放置在了世界历史之中,使自身从写作者一人的行动历程拓展到诸多阅读者的行动历程,再蔓延成一个个事件,直到达成自己所允诺的那个未来。
归根结底,如果说「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行者」[15],那么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或许正尝试着签下那张错落在不同时间之中的委任状,以便透过它看见齐一的未来。